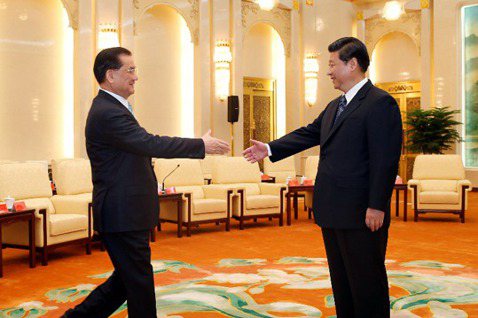在慾望的高牆前——波多野結衣與文萌樓

日本AV女優與台灣悠遊卡公司合作,造成的爭議,可以從太多面向切入,光是「在公關行銷上究為成功失敗?」,每個人的定見即有所不同。但這都不是我關心的(也不擅長),我好奇的是,平素我們喊著不應歧視性工作者,但見到AV女優躍然悠遊卡上,卻又壓不住心中陣陣湧上的古怪感受。二來,對著性慾,我們竟可以彆扭至如斯地步,我們只允許性慾在看不見的角落大肆伏行,在公開場合卻絕口不提,遵守非禮勿視的好寶寶規矩。
先分享兩件有趣的現實。
1.美國每年出產約13000部的成人片,創造130億美金的利潤,相較之下,好萊塢每年上映507部電影,利潤是88億美金(Bridges and Wosnitzer,2007)。
2.有七成的色情網站堵塞發生在上班時間,也就是白日九點至五點(Sex Tracker,2012)。
色情從來不是發生在三更半夜與謹慎幽微,色情很大,他卻大得我們看不見,當一個龐然大物站在你的生活中,我們卻看不見它的存在,理由何在?為什麼我們視若無睹?
Erika Lust,在她的《Good Porn》(中譯為《好色》,大塊出版)中指出,在色情產業中,我們必須現身說法,「我們的社會向來不把色情片當一回事,認為這些影片不可能對生活其他層面造成影響。事實上,他會。色情片不僅僅是色情,色情片是一種論述,是一種討論『性』的方式,是一種觀看、理解陽性與陰性氣質的方式。」
但現身說法總是很難,對於性慾的存在,有時我們以擁有性慾而感到不安,甚至是羞恥,但性慾的缺乏,在部分時刻卻又隱隱有種疾病的連結,君不見,女性的威爾剛上市啦。
現代婦女基金會說,此舉是「運用納稅人的錢在販賣性想像」,這發言有兩個疑問:
1.販賣性想像,有哪裏不對?
先不計較「運用納稅人的錢」這段,因著在台灣,納稅人的錢被花到哪裡去了,要認真細究可能一個不小心就被做成護國消波塊。不妨先聚焦在「販賣性的想像,不好嗎?」
轎車廣告中我們販賣的是對速度、對安全、對自在移動的想像,信用卡廣告中我們販賣的是自己可以擁有富裕生活的想像,在補品廣告中我們販賣的是對於健康、對於免於衰敗的想像,保養品廣告販賣的是對於青春永駐的想像。而我們很少(幾乎是不曾)關注這些想像給生活帶來的負擔與困擾,何以,對於性的想像,竟如此反射性地做出差別待遇?
性的想像,哪裏不好?
何況,既稱想像,想像存在人心,而人心又是多麼善變。恍惚間想到魯迅曾言,「一見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胳膊,立刻想到全裸體,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雜交,立刻想到私生子。中國人的想像唯在這一層能夠如此躍進。」
有人說魯迅此言,是再次演繹了蘇東坡與佛印的故事,「心中有佛者,見眾生是佛。」,故依此理,若我們始終割捨不下對性的譴責與追打,也許是那些念頭時常纏繞在心中。不過,與其坐在瀑布下吟詠清心訣,不如滑鼠往上滑,回到現實吧,色情很大,吾道不孤也。
2. 不該耽溺於「看看誰是好女孩」的遊戲了
統治的定律是分而治之(divide and rule)甚至是分而征服(divide and conquer),意指分裂既存的權力結構並且避免弱勢權力的結盟。但不妨以簡單一點的例子理解,日本前東京大學社會系教授上野千鶴子在近期《厭女:日本的女性嫌惡》一書中指明,「男人對女人的統治除了把女人區分為『聖女』與『妓女』,還利用了階級與人種的分歧。」。
上野舉的例子是,在二次大戰中,日本不僅將慰安婦依國籍區分待遇。在戰場上,軍護士很排斥讓慰安婦照慰受傷的士兵,因她們害怕這會模糊了聖與妓的分野。
當我們選擇作為一個群體組織倡議時,對外名義的使用上,不能貪心,若我們並不打算與這個框架內的不同成員「休戚與共」,最後的溫柔就是限縮這樣的框架,限縮至,我們可以承擔的範圍,我們願意承擔的範圍。
最後,來一次真心話大冒險吧!
若這次出現在悠遊卡上的並非來自日本的波多野結衣,而是台灣本土的性工作者呢?
在欠缺「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慈父手中片,波多野結衣」的情感下,此際的慷慨激昂是不是有可能隨即失所附麗?決定性工作者的歧視與不歧視,背後也包藏著我們對於外表年紀、對於與娛樂的結合成敗的觀點。
甚至,我也想問一問台北市政府,波多野結衣與文萌樓,何以有著截然不同的榮辱?
幾年前就讀大學時,在教授的穿針引線之下,請來日日春協會的鍾君竺分享,她也帶著一位性工作者。介紹了性工作的大致日常後,鍾小姐說,歡迎我們提問。學生們你看我看,確實有著幾分鐘的不自在,因著我們未曾那麼近地,凝視,凝視那始終被性慾凝視的女人。我們對她展現的好奇,有部分是對於自身性慾好奇的投射。
提問時小心翼翼地,好像怕一個使勁什麼東西就會被我們碰壞似的,斟酌著每一個問題,「在工作時,妳的心情是什麼?」(這樣問好嗎?)「若客人提出讓妳感到不舒服的要求,會怎麼反應呢?」(這問題應該可以吧?)、「該如何跟親人解釋自己的職業?」(會太白目嗎?)
我始終忘不了那一堂課,我離性這麼近,離性慾這麼近,離性的各種執著這麼近。當我可以站得這麼近,我也更能坦率地面對自己的性慾,與理解他人實現自身性慾的方式。而當我理解的當下,我也察覺到,自己終究得從道德(虛偽的)制高點走下來。
房慧真曾寫了這樣一篇文章〈欲望很痛〉,裡頭有個迷離絢爛的片段,也是講述她與日日春的因緣,「今年才剛過世的前公娼阿姨麗君,有一籮筐這樣的故事。有不要做愛,提著一卡皮箱來的男人,打開裏頭是一件白紗禮服,她穿上後,男人抱著她痛哭。這背後的故事是,男人有個初戀女友,琵琶別抱。也有男人專門要找她這種上了年紀的性工作者,同樣不要做愛,只抱著她哭,叫她阿母。」
但更讓人激賞的是房慧真在下一段的鋪陳,輕盈且柔軟,「這些男人們,俗稱嫖客,在我們社會的主流眼光中,像是變態。反而是底層性工作者如麗君,承接了他,收拾了他,撫慰了他。麗君阿姨是無牌的心理諮商師,也同樣被主流社會唾棄、排斥,但唯有在她陰暗的小房間內,才真正療癒了這些病體、傷痕,這些無處可去的男人。」
欲望確實很痛,而對於選擇將那些沉痛納進生命的工作者而言,我們可以靜靜欣賞他們的展演,但也可以輕輕一聲感謝,謝謝你們帶來的奇幻旅程。
趁亂告白時間:親愛的吉澤明步,我的性啓蒙前輩,跟妳共度的時光總是特別開心,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