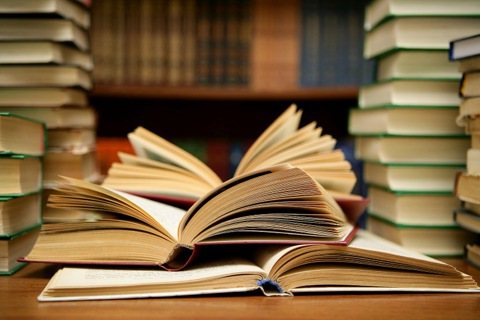古文教育和文學教育的雙重失敗——從「古代廢文大賽」到「桃機賦」

上週有兩件跟古文沾上關係的事件。一是網友發起了「古代廢文大賽」,發現許多古詩直翻成白話文之後,簡直讓人廢到笑,於是開啟了一小波把古詩通通挖出來翻譯的熱潮。二是作家張大春經過桃園機場,讀到林彥助〈桃機賦〉後,批評此賦文理不通;並有網友撰文,逐字解釋何以不通。
這兩件事情的討論不少,但我認為有趣的不是這些「古文」本身,而是這些古文材料引起的反應。這些反應,顯現出台灣中學文學教育的某些癥候:我們在中學六年的國文科當中大量置入古文教材,但普遍受過中學教育的人們,對「文言文」依然充滿著疏離和誤解,教學成果十分失敗。而這樣失敗的教學結果,卻讓我們的公民花費大量的時間去學習,排擠了真正的閱讀能力、文學品味的養成。這才是最可怕的事情。
▎文學教育沒教好的三個文學常識
先從「古代廢文大賽」談起。在這波熱潮中,最經典的一篇翻譯就是陳子昂〈登幽州台歌〉。此詩原文是:「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而鄉民版的翻譯是:「前面沒有人,後面沒有人,這世界好大啊,於是我就哭了。」由於翻譯出來的文章有一種直白的滑稽,部分網友形成了一種氛圍:「原來翻譯出來這麼北七,那原詩也沒什麼了不起啦!」
從這種反應,我們可以看到過去數十年來,中學國文教育現場最大的問題。我們在教材裡面塞了一堆文言文,可是師生實際進行的教學活動,多半就是「翻譯」而已,而且是一字一義,有單一標準答案的翻譯。長久下來,學生就會習慣用白話翻譯去理解文言語意,也就容易忽略以下三件事:
一、文學作品的文字操作,非常重視「歧義性」。
亦即一個字有多個意思,或者多個字有多種排列組合的意義。文學作品並不是純粹「傳達資訊的文章」而已,它有時會刻意營造出一種「你說是A可以,你說是B也可以」的狀態,這是一種文字上的特技表演,也是作品好看之所在。而當我們解讀作品的時候,必須盡可能找出所有的歧義,才能看出它的精妙之處。
以陳子昂的這首詩來說,他詩中的「前後」就至少有兩個意思,一是空間上的(因為站在高台上,當然前面也看不到人、後面也看不到人,又不是鬧鬼),一是時間上的(這裡當然不會有古人、也不會有未來人,又不是涼宮春日)。而表面上說的是空間和時間上都前後無人,搭配後兩句來看,我們又可以知道,他要講的包括但不只是「都沒人」,「都沒人」可以是「都沒賞識我的人」,也可以是「都沒理解我志向的人」,或甚至更霸氣的「都沒可以跟得上我的人」。
回去對照鄉民版的翻譯,你會發現那翻譯之所以好笑,其中的原因之一是,原詩歧義的解釋空間都被縮減成單一解釋了。原詩時空並存,譯文僅存空間;既然僅存空間,後續的解釋也同時被限縮,你自然會覺得他不知道在哭三小。
但這不能怪鄉民翻譯不佳,真正的問題是:「歧義性」這個在任何文學教育體系,都應該是入門款概念的東西,為什麼我們花了六年的中學教育還是教不會?當我們不斷在考試制度、教材教法上強調單一答案、官方詮釋的時候,學生自然習慣去找「最佳解」而不是「更多可能的解」。別說鄉民翻得鳥了,我們的許多教科書解釋這首詩的時候,直接告訴學生「古人」等於「禮賢下士的明君」,這種粗暴的單一連結,是有高明到哪裡去?
二、文學作品的形式和內容必須同時評估。
如前所述,文學作品不是純粹的資訊傳達,所以只要換一個表達形式,就會在內容上產生細微的差異,而讓學生知道如何分辨這種細微之處,也是文學教育所的本分。這種差異,從字數、聲音、節奏、選字、構詞、句型到運鏡、敘述邏輯、先後順序、描寫的詳略選擇等,都會產生影響。
所以,當你把〈登幽州台歌〉「翻譯」成鄉民版之後,基本上就應該視作兩篇不一樣的作品來解讀。比如第三行,「念天地之悠悠」和「這世界好大啊」,前者的「念」強調的是「想到」天地悠悠,後者是直接告訴讀者「世界好大」,側重之處就有微妙的差別。(如果你覺得這差別很抽象,你可以想像「我做了一個告白的動作」和「我告白了」的差別——當然這例子比較誇張一點)而「天地悠悠」與「世界好大」,從聲音、節奏和語氣來看,也都完全不同。「悠悠」讓速度慢下來了,有種緩慢流動之感;「這世界好大啊」拉鏡頭的速度快多了。
如果要對文學作品進行評價,你必須至少對上述的差別有感覺。是的,有感覺就好,不必像文學研究者一樣,把每件事情說清楚,但至少要能感覺形式改變之後,對整篇作品造成的影響。而我們的文學教育有沒有讓學生練習感覺過?我想答案會有點悲傷。這次「古代廢文大賽」對於參與者的啟發,恐怕還高過正規課堂不知多少倍,至少它讓很多人看到形式被抽換掉,只剩下單一資訊的文學作品是什麼樣子。
三、最後一件學校應該教,但沒有教的東西是:在翻譯的過程中,原文和譯文不可能百分之百等同。
原文和譯文應該要被視為兩個部分交疊的圓圈,有些東西是兩者兼有的,這就是「翻譯」的可能性和極限;但有些東西是只有原文才有,譯文沒辦法傳達的、有些東西則是譯文意外跑出來,原文沒有的。比如英文說:“My name is Chuck.”,而我們翻譯成「我的名字是Chuck。」的時候,兩句話並不是完全全等的。在英文的說法,這就是一個正常的自我介紹,但在中文的翻譯版本中,這句話顯得比較生硬、拘謹、疏離,因為我們的習慣用法是:「我是Chuck。」或「我叫Chuck。」我們不會把「名字」(name)標示出來,當標出來之後,就會有一種硬硬的說明感,我彷彿不是要跟你介紹自己,而是要跟你介紹「我的名字」,這種感覺就是多出來的。
所以,理論上,就算是面對與現代中文頗類似的古代中文,我們還是不可能找出全等的翻譯。唯一全等於某句話的,就是那句話本身。這又多了一個不能以鄉民版陳子昂來評估陳子昂的理由。對照兩個版本,你會發現原文有不少東西都沒出現在譯文當中,除了前述的時間脈絡、「念」這個動作以外,還有「獨」這個強調狀態的詞,以及「愴然」這個描述他哭成什麼樣子的概念。而當我們讀到譯文中出現的「世界」一詞,你會立刻想到以整個地球為範圍的這個「世界」,但陳子昂寫下「天地」二字的時候不可能有你腦袋裡面的那些東西,這兩字指涉的,也就是從原文當中增生出來的。
但我們的中學文學教育很少強調這個概念。為什麼?因為要出單選題啊,如果讓學生知道單選題的選項和原文不全等,那要怎麼辦才好。
當然,上述的討論不是要指責網友,而是從網友的反應當中,看出文學教育所帶來的思維限制。還是有非常多的網友其實非常清醒,他們反而利用了這個「古代廢文大賽」來反諷古文教育的僵化,把原本神聖的還原為人——這一還原的過程,本身就有參差對照的趣味。而就算不是那麼有意識的網友,在原文與譯文的來回對照中,也多能隱隱感到上述的文學概念。就此而言,參與這股風潮的網友們,其實從學校給定的框架裡,自行摸索出一種享受文學作品的方式來了。
▎什麼場合該寫什麼
如果「古代廢文大賽」呈現的是中學文學教育走偏方向,因而忽略了若干基本的文學概念的話,林彥助的〈桃機賦〉呈現的則是我們文學教育脫離現實的傾向,沒有引導學生去思考「什麼場合該寫什麼」的問題。
我基本上同意張大春和前引網友對〈桃機賦〉文詞不通之處的批評,從文學的觀點來說,那就是一篇文字表現欠佳的文章,毫無疑義。你如果拿前節的標準,去尋找文章中的「歧義性」或形式特別之處,也將一無所得,因為它基本上沒有什麼耐得住推敲的設計。但我更好奇的是:為什麼桃機的主事者,會將這樣一篇文章懸掛在桃園機場裡?
不同的寫作者,程度和才氣高下有別,但文章能不能出現在那個地方,主事者才有最大的決定權。因此,這裡真正的問題是:主事者有沒有想過,放在那裡的文章要符合哪些需求?決定放什麼文章的「問題意識」是什麼?是給我國出境的旅客看的?還是給外國入境的旅客看的?無論前後者,你為什麼希望他看這個?
從〈桃機賦〉的口吻來看,此文應該是設定給外國旅客看的。姑且不論外國旅客能否讀懂中文的問題(因為這可以用翻譯解決),純粹看文章的內容,更糟糕的部分恐怕是:你為什麼要跟外國人講這些東西呢?手續簡便、路上車很多、科技進步、有很多農產品……所以勒。如果以推廣觀光論,整篇文章唯一有意義的,大概只有:「物美價廉之免稅店,烏龍包種阿里山之茶香,金門高粱之醇烈,包爾試飲三碗而不過崗。」至少提點了烏龍、包種、金門高粱、阿里山這幾個關鍵字。但幾百字當中,只有這幾個關鍵字有意義,這樣的「績效」也未免太低了一點。而如果不是為了觀光,是為了呈現某種「文化氣息」,那你選擇去呈現:「服飾玲瓏而端雅,名牌華貴之仕女化妝。」之類的畫面,這也就怨不得被批評文化水準低了。
如此貧乏的內容,就算文字都修整得很完美,這篇文章也是好不起來的。
然而,「績效」這麼低的文章,終究是放上去了。這意味著,桃機的主事者本身並沒有設定任何問題意識,他就只是想找篇文章放上去而已。而此一高懸「國門」的作品,想像中就要代表「我國文化」,所以就選擇了非常標準的官方想像:來幅書法、寫點古文吧。所以只要有古文就夠了,內容不重要;事實上是不是古文也沒多大關係,只要寫得成一幅書法就可以了。
真正沒sense的不是文章作者,而是這些主事者。而這些主事者,想必有不少也是高普考及格,狠狠K過幾年「國文」的,更別說他們也經歷了六年充滿古文的國文教育。這些經驗,顯然都沒能拉高他們面對文學或古文的「下限」。他們無能審度文字的好壞,這也就罷了;連內容這麼淺白的狀態,都看不出內容不適合,不曉得該看場合來佈置合適的符號,這也真的是文學教育的巨大失敗。
或者,也可以說是巨大的勝利吧。從桃機的主事者、〈桃機賦〉的作者,一直到參加「古文廢文大賽」的年輕網友們,無分世代,他們對文學的理解,都被限制在一個怪異的框框裡了。過去數十年來,我們浪費每個世代中學生的時間和精力,讓他們研讀與自身生活極端疏離的古文,最後卻是古文沒學好、文學的基本概念也沒學到,兩頭都空了。但如果教育的主事者從一開始就不在乎文學、也不在乎古文的話,或者,這個國家的主事者根本希望這個國家的人民根本就不要有自己的文學、也只是把古文當作壓制文學創作的工具的話,那確實可以把這一切看作是某方面的勝利。
一個被壓抑,另外一個則只是工具。這或許才是我們在文學教育上,爭執多年的「文白之爭」真正的輪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