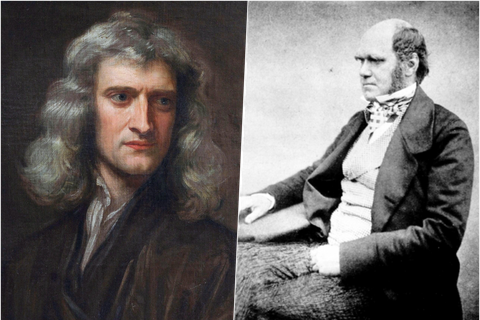走進龍發堂:信徒、家屬與院民的生活世界

(※ 文:湯家碩,國立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碩士,荷蘭阿姆斯特丹大學博士生)
關於台灣精神醫療相關制度的發展,許多研究都曾經提及位於高雄市的「龍發堂」,並指出該堂在1980至1990年精神醫療照護建制化過程所扮演的關鍵角色(何健民 2008;陳小慈 1993;林曉卿 2006)。這間以創堂主持釋開豐為信仰核心的廟宇,一度是台灣最為著名的精神病患收容機構之一,1980年代收容的院民人數達兩百餘人。1
當時的龍發堂,承諾終生收容送入堂中的病人,標榜不使用現代精神藥物,而是讓院民誦經禮佛,透過宗教活動改善病情,並且讓病人進行成衣製作與養雞等生產勞動,甚至組成樂隊或陣頭四處演出。然而,龍發堂也因為拒絕現代精神醫學的介入,引發社會輿論與衛生部門對於龍發堂機構的合法性和療法適當性等關切。
有些精神醫療專業人員認為,龍發堂的收治模式缺乏現代醫學知識與專業人員照護,因此該機構的收容機能形同「笑話」,也嚴重侵害病人的基本健康權。2然而,也有許多同情或支持的論述指出,相對於精神藥物治療,龍發堂以耐心、愛心來感化「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難治精神病人,正是這樣的道德色彩才能吸引家屬將病人送入堂中長居。3這兩種不同的聲音,使龍發堂長期處於爭議之中,也讓龍發堂更加「聲名遠播」,成為台灣精神病院的代名詞。4
龍發堂雖然普遍被認為是促成台灣精神衛生法治化的重要因素之一,但到目前為止,直接以龍發堂作為研究對象的報告並不多見。本文考量既有研究的不足,試圖以精神療養機構的社會史為主要框架,探討1980年代龍發堂在精神病人治療與照護上的實踐,如何被不同社會背景的行動者(例如,精神科醫師、家屬、信徒等)置入不同的議題脈絡中?

龍發堂信仰與宗教奇蹟的建構
在精神醫學的觀點中,由於龍發堂主要被視為精神病人收治機構,因此會將宗教信仰與慈悲為懷、耐心愛心等信念畫上等號,認為這些道德情操促成龍發堂獨立收容病患與照護病患的能力,5卻因此忽略龍發堂收治活動的形式,與其宗教特徵之間彼此鑲嵌的關係。6
龍發堂的信仰形式在1980年代以佛教為主,由於堂內對於住持釋開豐個人神蹟的強烈崇拜,文榮光在研究中將龍發堂形容為新興宗教。不過就筆者的觀察,龍發堂信徒所呈現的信仰觀念,其實與大部分民間信仰的實踐態度十分接近:行善、勸善、做功德,這種對於助人與慈善活動的提倡,幾乎就是龍發堂信仰中最主要的核心內容。
至於釋開豐被特別崇拜的原因,除了高超的德性,也是因為他在救治病患過程中所展現的治癒神蹟。這樣的神蹟在敘事上最為典型的範例,即是精神病人的照護與康復。在筆者的田野觀察中,無論是信徒或是龍發堂的師父,都津津樂道於釋開豐如何親自接受家屬百般請託,將無人敢靠近、時常會作亂傷人的「瘋子」,從長期禁錮的鐵籠或土角厝中解救出來,帶回龍發堂與其他師父一齊悉心照料。
那些被釋開豐善待的病患,也奇蹟似地安靜下來,不僅適應機構中的團體生活,也逐漸能進行勞動或吹奏樂器等活動。這樣的成效不僅讓龍發堂的名聲廣為流傳,也吸引更多外地的家屬帶著無法治癒的精神病人前去投靠。7
信徒為何相信龍發堂裡的「奇蹟」?
除了超自然的奇蹟本身,這些奇蹟也往往以十分戲劇化的方式被反覆傳頌,而傳頌的動機則與釋開豐老師父的崇高德性有密切的關聯。以龍發堂的宗教觀念來說,救治不癒病人的能力,證明了釋開豐在超驗的神佛世界所具有的靈驗力量,也是釋開豐慈悲為懷的道德價值的體現。
龍發堂的信仰中超驗力量的發生邏輯,因此乃是奠基於「無私奉獻的崇高德性」與「靈驗的奇蹟事件」之間的相互證成關係,而信徒對於釋開豐神力的信仰與投入慈善行動的動機,則是一種同時提倡無私助人,也期待獲得宗教領袖神蹟庇佑的「功德福報」價值觀。這種在信仰目的上同時具有利己與利他特質的雙重性,在丁仁傑(1999)對慈濟功德會成員的研究中也有類似的發現。
發生在龍發堂中的奇蹟,如何因為社會信任而成為被信徒接受的事實?筆者在田野觀察的過程中,曾訪問一位資深信徒「阿蔡」,她會與龍發堂「結緣」,一開始是因為母親有無以名狀的病痛,四處求醫求神無果,在公公做生意認識的朋友介紹下,最終才求助於龍發堂。
另一位筆者在田野中遇到的信徒「阿華」,同樣因為兒子得了不明重病求醫無果,經由在同一市場賣菜的阿蔡引介,接觸龍發堂並成為信徒。從這兩個案例中,可以發現龍發堂的奇蹟事實,傳播的過程十分仰賴親屬或者地緣關係所構成的社會網絡。面臨無解難題、亟待某種救治機遇的「受苦者」,因為社會關係而偶然地接觸龍發堂奇蹟故事。8
人際網絡的連帶不只使龍發堂的奇蹟得以擴散,也讓關於奇蹟的敘事有了親近的社會關係人為之代言。這些代言人不僅負責傳遞事實,同時更進一步扮演積極鼓吹、策動其他行動者進入龍發堂的角色。9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即使信徒接受龍發堂的奇蹟作為一種「事實」,這樣的事實仍然可能因為社會當時對於精神疾病的污名化,以及家屬對於口傳奇蹟缺乏信心,而處於「半信半疑」的不穩固狀態。

精神疾病的污名鞏固了龍發堂的「奇蹟治療」
一間充滿「瘋子」的廟宇要在信眾與病患親屬之間成為可被接受的事實,必然要跨越精神病患的社會污名所形成的障礙,而其成功關鍵奠基於一套環繞著「眼見為憑」作為事實,打破污名的機構實作特徵。此一眼見為憑的實作,讓傳聞從不穩固、去脈絡的知識,轉化為被親自驗證的事實,是除了社會關係,另一個使龍發堂的治癒奇蹟成為可信的重要因。
精神疾病與精神病人在社會上的污名,既是使外人不敢接近龍發堂的阻力,也是龍發堂可以穩固釋開豐奇蹟治療神話、吸收信徒的關鍵。當外人懷著對精神疾病的恐懼心理踏進龍發堂的時候,院民列隊念經、出家人悉心照料就映入眼簾。
親眼看見的「秩序」「乖乖的」「可以做工養雞」,正好與典型瘋狂者「亂」「抓狂」「不受控制」的刻板印象產生強烈的對比。精神病人社會污名的嚴重程度,正好反襯出龍發堂的善行與慈悲是如何高明,能使這些原本讓人避之唯恐不及的「瘋子」被徹底收服成溫順的修行人。
因應宗教信仰的結構中既利他也利己的「做功德」觀念,龍發堂中的精神病患收治療效,構成了龍發堂中信仰靈驗的展現,也讓龍發堂信仰中的各種宗教奇蹟能被「眼見為憑」的事實所鞏固,使神蹟不再只是虛無縹緲的口傳言說,而能在親身見證的歷程中被穩固下來。
透過社會連帶關係者作為奇蹟事實的中介代言人,再加上(受到污名的)機構中收治活動景觀作為直接見證的機制,讓龍發堂能串聯起在地機構和機構外的行動者,形成跨越地理空間的信仰網絡,將外在的行動者從機構外逐漸往機構內移動,形成信仰中社會網絡的「再地域化」(丁仁傑,2005)。

病人家屬對現實的折衷妥協
龍發堂以宗教奇蹟與慈善照料,提供精神病人終生庇護場所的論述,除了被信徒視為可信的事實之外,是否亦為院民的家屬所採納?他們是否也相信釋開豐具有治癒精神疾病的靈驗力量?
在文榮光的資料中,對比於龍發堂的信徒對於治癒神蹟深信不疑,114個家屬個案雖然大多數肯定釋開豐的德性與慈悲,感謝他願意照料家庭無法負擔的精神病患,但其中僅有少數家屬相信釋開豐具有法力,或者能以神蹟治療精神疾病。10
大部分家屬對於龍發堂的療效宣稱,其實採取務實的折衷態度:有的家屬不信鬼神,因此並不認為是佛法治病,但相信有社交活動的龍發堂比獨自關在家中好,或者認為誦經並無靈驗力量,但能達到鎮靜效果。
關於家屬選擇龍發堂的動機,文榮光、張苙雲(1984, 1985)研究中指出,龍發堂家屬四處求醫的歷程往往長達數年,直到無法負荷家庭經濟或生活照護等壓力後,才放棄治癒病人的可能性,將病患「放生」到機構內,讓病患接受長期收容。因此,龍發堂的存在標誌著病患求醫途徑和治癒希望的雙重終點。
然而,就如許多關於十九世紀歐美精神療養機構的歷史研究所顯示,家屬與機構之間並非全然對立或斷絕關係的兩個世界,療養機構也可能是暫時緩解照護負擔的場所(Tomes 1988)。在文榮光的個案報告中,也有家屬明確表示,如果家人病情好轉,希望能將人帶回家,並且透露對於將病患「棄置」在龍發堂的舉動感到相當自責;也有家屬維持定時去龍發堂探望病患的習慣。
因此,筆者認為「治療」與「收容」在家屬世界中往往並非全然二分,「長期收容」也不一定是在「放棄治療」後才有的選擇。

大多家屬並非不信任精神醫學
從精神病人的家屬多年的求醫歷程來看,他們並非一開始就不信任精神醫學,也不是直接選擇龍發堂作為收治場所。相反地,精神醫學在家屬的觀念中,依然是最普遍的醫療途徑,其中有不少家庭為了籌措西醫治療的費用,不得不抵押房產、出賣土地、讓售謀生用的市場攤位、變賣嫁妝或借貸。除了在住院治療上幾乎傾家蕩產之外,許多家屬更反覆周旋於不同精神醫療機構之間,往往在一間醫院治療無效後,再轉至其他醫院求助。
除此之外,個案紀錄當中也有家屬認為西醫治療有助於讓病情好轉。但從「有吃藥時比較好,沒吃藥時就比較不好」「住院治療期間病情改善,回家後又惡化」等說法來看,無法穩定使用西醫療法,或許是家屬最終轉向龍發堂求助的主因。
由於住院費用驚人,家屬往往只能斷斷續續地讓病患接受西醫治療,或是因為無法負擔支出而被醫療機構要求出院;藥物使用方面也有家屬反映有發抖、流口水等副作用等問題,或者家屬可能根本不熟悉藥物的使用方式,因此導致治療難以獲得效果。
經濟困境與無法穩定使用抗精神藥物,一方面呼應1980年代精神醫療資源不足,以及機構異質性高等困境,也反映並非所有精神疾病都能康復的現實,亦即西方醫療的有限性。這樣的情況同時也是筆者所訪問的精神科醫師,對於當時台灣精神醫療生態的共同回憶。雖然他們泰半不認可龍發堂拒絕藥物治療的模式,對於龍發堂的存在,以及家屬的選擇,卻抱持包容的立場。
有醫師對於龍發堂模式的評價僅有「笑話」兩字,但也承認並非所有精神病人都會康復;加上當時的精神病床缺乏,導致病患有可能被要求提前出院,都促成家屬轉而選擇龍發堂的收治服務。11
另外也有醫師表示,在1980年代走訪鄉野,所看到的病人收容環境實際上往往並不比龍發堂好上多少,更為悲慘的也所在多有,「至少龍發堂還算是個可以遮風避雨的違章建築」。12甚至有醫師更進一步反思台灣精神醫療系統缺乏對於慢性病患家屬需求的理解,而龍發堂可說是讓精神醫學思考「自己能為病患做些什麼、做到什麼程度」的契機。13

病人家屬唯一可走的路
在王文基(2017)對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中期中國精神療養院的研究中,強調當時由於相關機構數量極少,由家庭與社會負擔主要的病人照顧責任,精神病人的處理乃是家庭問題的一環,因此家屬的能力與社會關係決定了病人如何被安置的行動軌跡。類似的現象,也同樣反映於1980年代台灣精神病患家屬的求醫軌跡之中。
或許就如一位家屬所言:「在此度日,不得不來。」龍發堂關於精神醫學無效、不使用抗精神藥物的宣言,以及終生收容的承諾,或許是少數能呼應家屬處理精神疾病的挫敗經驗的醫療論述,顧及了家庭經濟能力與解決家庭照護負擔等需求。不論是否認同其收治模式,在選擇有限的情形下,這些家屬只能暫且在龍發堂繼續棲身。
如此有限的能動性反映出1980年代精神醫療選擇和安置機構缺乏的時代背景脈絡,同時也是家庭經濟資源匱乏後無法尋覓更理想機構的結果。大環境與個人處境共同構成的泥淖,讓這些家屬深陷其中,最終使龍發堂成為唯一一條可走的路。
※ 本文摘自《不正常的人?台灣精神醫學與現代性的治理》第五單元,更多內容請參本書。
《不正常的人?台灣精神醫學與現代性的治理》作者:吳建昌、李舒中、林桂卉等出版社:聯經出版出版日期:2018/07/05

- 1980年代龍發堂院民人數主要參考文榮光(1984)的研究記載。
- 語出筆者訪問的精神科醫師陳一行(2014年5月13日)。
- 例如,聯合報(1984)在〈龍發堂已屬於社會的龍發堂各界人士均認為有存在必要〉報導中寫道:「與會的專家學者、病患家屬、法界人士、社會工作者等人,均認為龍發堂有存在的必要,而且比一般私人的精神病醫院對待病人更人道。」
- 例如,ETtoday新聞網,〈老師譏自閉症學生「龍發堂出來的」法院判國賠6千6〉報導中提到:「法官審理認為,『龍發堂』是頗具盛名及規模的收容精神病患者機構,因此指某人是『龍發堂出來的』,已有暗示或影射其精神狀態異於常人的含意。
- 參考筆者對精神科醫師李偉強(2013年3月14日)、文榮光(2012年9月16日)的訪談紀錄。
- 本節中關於龍發堂信仰內容與活動的描述,為筆者2013年在龍發堂進行田野調查的過程中,訪問資歷超過30年的資深信徒或出家師父所彙整得到的結果。
- 在此筆者對於釋開豐是否真有佛力/神力,暫且採取存而不論的態度,畢竟以社會科學的立場來說,筆者更傾向探尋各種言說、論述背後所反映的社會與文化意涵,所涉及的行動者之間的互動關係,以及在特定社會建置中所扮演的角色,而不是追問論述或言說的絕對真偽。
- 無論如何,一套釋開豐神蹟治癒的世界觀的傳播,以及某種科學所建立的自然世界觀,同樣都與「誰是值得信任的真理述說者」之間存在共生關係,並且要符合某些既有的社會文化脈絡。因此,筆者認為科學知識的傳布和宗教奇蹟的傳播,在模式上其實並沒有本質上的差別。
- 有趣的是,相對於Shapin(1994)討論現代早期英格蘭科學文化的建立研究中所描繪的,因為作為公共賢達的聲望,而獲得公正不偏代言者身分的紳士,龍發堂中的代言人反而更因為與神蹟密切的利益、社會連帶關係的親暱性而受到信任。
- 這個小節的家屬個案,取自文榮光1984年研究原始資料中對於病患家屬的家庭訪談紀錄大綱。
- 參考筆者對精神科醫師林冠宏的訪談紀錄(2013年3月20日)。林冠宏除了正文所述的觀點之外,也提及自己在2000年後到龍發堂進行巡迴醫療時,在堂中看到自己曾在醫院精神病房照顧過的病患,因此感嘆當時精神醫療資源之有限。
- 參考筆者對王志方的訪談紀錄(2013年3月29日)。
- 參考筆者對陳一行的訪談紀錄(2014年5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