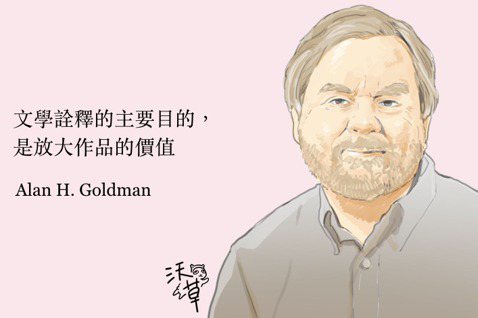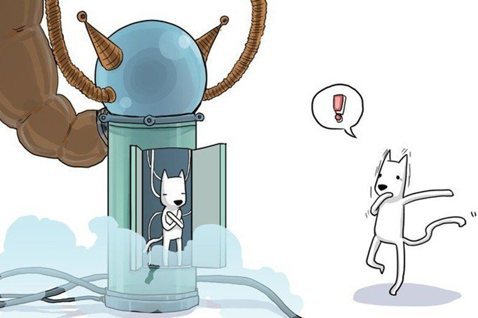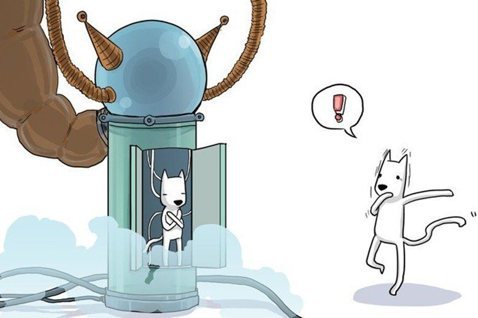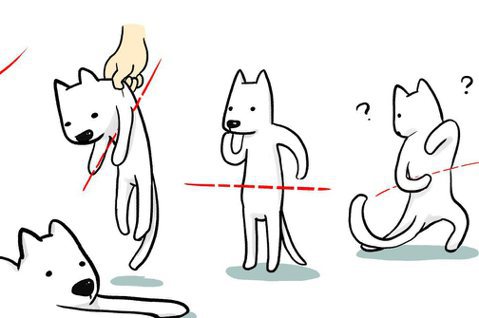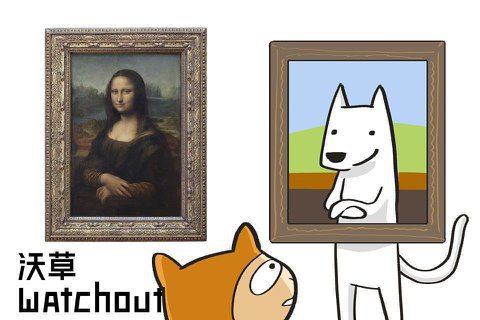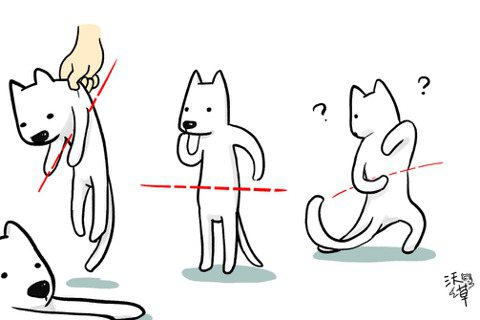林斯諺/猴子或機器人,都可以是百萬暢銷小說家?

小說家是一個成功就賺到翻、失敗就餓到死的神奇職業。我們耳熟能詳的小說家通常屬於前者,例如阿嘉莎・克莉絲蒂(Agatha Christie)、丹・布朗(Dan Brown)或東野圭吾。這些暢銷小說家除了書賣得好之外,還具備一個發人深省的共通點:他們都是人類。
等下等下先不要關視窗,這個共通點真的值得深思,因為我接著要告訴你,有哲學家主張這根本不是共通點。按照這位哲學家的主張,猴子或機器人也可以是百萬暢銷小說家。一定有人會說,天啊,哲學家腦袋是不是有問題?讓我們先來看看哲學家怎麼說,再下判斷也未遲。
出香蕉能請到猴子寫小說嗎?
考慮這個案例:
猴子案例
科學家讓一隻叫做「蒙奇」的猴子敲打電腦鍵盤。蒙奇敲出來的多半是散亂的文字,無法理解。然而,有一天,科學家們檢視蒙奇的鍵盤記錄,發現竟然是一部精采萬分的懸疑推理小說!科學家們仔細檢查過蒙奇的狀況與電腦後,確認這並不是誰惡作劇,而是真的湊巧——機率極低,但並非不可能發生。實驗室決定把小說出版,問題是,作者欄位該寫誰的名字呢? 1
美國哲學家古德曼(Nelson Goodman)會說,作者名字當然是寫「蒙奇」。爾後如果這本書得獎了,該上台領獎的也是蒙奇。古德曼是如何得出這個結論的?我們必須先從他的基本主張開始討論,這個主張是,文學作品等於文本(text)。 2
上述這個主張並不是說,《東方快車謀殺案》(Murder on the Orient Express)等於你手上的那本實體紙本書;這樣的實體書有成千上萬,而《東方快車謀殺案》這部作品並不等於這些書的任何一本。然而,這些實體書顯然與《東方快車謀殺案》有某種關聯:它們都是某個文本類型(text-type)的個例(token)。
類型和個例是什麼?讓我用一個簡單的例子來說明。李清照的〈聲聲慢〉第一句是:「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淒淒慘慘戚戚。」想想看,這句話裡面有幾個中文字?如果你的答案是「7個」,那你講的就是字的「類型」;如果你的答案是「14個」,那你講的就是字的「個例」。在《東方快車謀殺案》的例子中,我們就可以說印出來的實體書共享某個文本類型,但每一本實體書都是這個類型的個例。
掌握了類型和個例,我們可以這樣描述古德曼對文學作品的看法:
每個文學作品,都是一個文本類型。
這說法乍看之下還滿合理的。你不能說《東方快車謀殺案》這部作品等於我手上這本小說,也不能說它等於你手上這本小說,最合理的說法,似乎是說這部作品是一個抽象文本類型,而你我手上的紙本書,都屬於此類型,因此它們「搭載」了同一個作品。
「每個文學作品都是一個文本類型」也可以用來說明文學作品之間的差別。《東方快車謀殺案》這部作品之所以會與《尼羅河謀殺案》(Death on the Nile)是不同的作品,就是因為它們具備不同的文本。
一個作品只會有一個文本嗎?
古德曼必須證明下面兩件事才能讓他的主張成立:
文本唯一:一個作品只會有一個文本,不會同時有兩個或三個彼此不同的文本類型。
作品唯一:一個文本只會有一個作品,不會同時有兩個或三個彼此不同的作品。
一個作品只會有一個文本嗎?有些人會想到,那翻譯怎麼辦?《東方快車謀殺案》以很多語言出版過,每個語言版本都是一個不同的文本類型。直覺上,不管是英文、中文還是日文版的《東方快車謀殺案》,都是《東方快車謀殺案》,因此我們好像必須說,這部作品不只有一個文本。
古德曼的回應很簡單:這些譯本是對作品的詮釋,但不是作品本身。這說法有道理可循,我們常說翻譯是「二次創作」,也會比較不同譯本的細節,品味不同表達和意涵。當譯者斟酌選字與用詞,其實已經在進行某種詮釋。這種二次創作的狀況在模糊性比較高的文本尤其常見,例如詩或純文學小說。
對譯者來說,這類作品想要做到完全的「字面上的翻譯」幾乎不太可能。一部對《哈姆雷特》(Prince Hamlet)進行詮釋的文學評論,本身就是一個獨立的作品,不是《哈姆雷特》;同理,《哈姆雷特》的譯文——若視為是對《哈姆雷特》的詮釋——也是一個獨立的作品,不是《哈姆雷特》。《哈姆雷特》這部作品只會有一個文本,就是原本用古英文所書寫的那個文本。
一個文本只會有一個作品嗎?
不同作品能共享同一個文本嗎?古德曼提供了一些相關案例:
雙胞胎案例
麥特與麥遜是雙胞胎,從小一起長大,接受一樣的教育,連講話方式都很像。有一年暑假他們去參加夏令營。這個營隊由同一個單位在兩個不同的地點舉辦,麥特與麥遜分開參加不同梯次。由於是同一個單位所舉辦,因此營隊內容很類似。活動結束之後兩人各自寫了一篇散文來抒發對這次活動的感想。讓人意外(或者說讓人不意外)的是,兩人所寫出來的文字內容竟然一模一樣,一字不差。
直覺上,我們應該會很想要說,這兩個人寫的文字,分別形成了不同的心得作品,縱使文字內容一模一樣。
但古德曼不認為如此。要說明古德曼的想法,我們必須先說明他如何定義所謂的「文本同一性」(identity of text)。古德曼認為,當兩個文本的語法性質(syntactic property)完全相同,這兩個文本就是同一個文本。什麼是語法性質?這包括文字排列的順序、空格以及標點符號。例如,《東方快車謀殺案》一刷的實體書與二刷的實體書呈現了同一文本,因為這兩者在語法性質上完全相同。3
語法性質還包括文字在該語言的文法中扮演的角色。古德曼舉了chat這個單字為例。這個單字可以理解成一個(迷你)文本,英文有這個單字,法文也有這個單字。按照古德曼的看法,如果美國人與法國人在各自與家人的聊天場合說出了chat這個字,我們不能說他們產出了同樣文本的個例,因為chat在英文文法中扮演的語法角色與在法文中不同。
然而,考慮英文中的cape這個字有「披肩」的意思,也有「岬角」的意思。這是否代表風景區指示牌的cape,以及服飾店標籤上的cape為兩個不同的文本?古德曼認為不是。不管是「披肩」還是「岬角」,都涉及cape這個字的語意,而非語法。在這個情況中,我們最多只能說cape這個字有兩種不同的詮釋。
上面提到的雙胞胎案例正是這種情況。古德曼主張,我們之所以直覺上會認為雙胞胎產出了兩部而不是一部作品,是因為我們把「一部作品,兩種詮釋」跟「兩部作品」搞混了。就如同對cape這個英文單字可以有兩種理解,我們也能對雙胞胎的文本進行兩種解讀(反應兩種相似但不同的夏令營狀況)。
再看看這個案例:
唐吉軻德案例
20世紀的小說家米納寫了一本小說,與塞萬提斯的《唐吉軻德》(Don Quixote)一字不差。書評家認為,米納創作出了一部全新的作品,因為從20世紀的觀點來看,米納的文本不但古意盎然(用古西班牙文寫的),而且某些段落還能嗅到實用主義的味道(實用主義是20世紀重要的哲學思潮之一)。
上述案例出自阿根廷作家波赫士(Jorge Luis Borges)的短篇小說。4不少哲學家認為,波赫士設想的狀況顯示不同的作品可以有同一文本,因此證明了作品與文本並非等同。
古德曼當然不支持這種說法。如同雙胞胎案例,唐吉軻德案例中自始至終都只有一部作品。我們頂多只能說米納做了兩件事:首先,米納產出了《唐吉軻德》這個文本的另一個例;第二,他為這個文本提供了另一種詮釋。然而,米納並沒有創作出一部新的《唐吉軻德》。
猴子靠「文本主義」上台領獎
古德曼這種「文學作品等於文本」的說法,被稱為「文本主義」(textualism)。若文本主義正確,只要不同的文本個例屬於相同的文本類型,它們就都是同一個作品。在此情況下,我們該如何決定誰是文本的作者?顯然把作者這個頭銜歸給第一個產出文本個例的人,會是最合理的,也符合一般人的直覺;就如同在唐吉軻德的案例中,我們會說塞萬提斯是《唐吉軻德》的作者,因為他比米納更先產出《唐吉軻德》這個文本的個例。
依照這樣的看法,猴子案例中的蒙奇當然可以是作者,因為牠是第一個產出文本個例的「人」,即使蒙奇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既然作品的概念只涉及文本的語法性質,並且與文本之外的事物無關(例如文本製造者的身分以及心理狀態),那只要是第一個產出文本個例的「人」都可以算是作者,包括(明顯沒有心靈狀態的)機器人。
你可能會覺得奇怪,機器人或猴子根本無法理解文本內容,為什麼可以稱得上是作者?古德曼認為這並不奇怪,能夠詮釋或理解自己書寫的內容,本來就不是成為作者的必要條件。例如,有些意識流的小說家或詩人可能根本不明白自己在寫什麼,但我們不會因此說他們不是作者。
又如,很多電腦能夠被用來證明數學定理,但我們不會因為這些電腦無法理解證明出來的結果,而說它們無法做證明。也許你會認為,更合理的說法是把電腦背後的程式設計者視為作者,但古德曼指出,設計者其實也不會做證明,就如同蒙奇背後的科學家不會寫小說一樣。那麼幕後團隊對於產品的「無知」狀態跟機器人或猴子有何不同?
假設丹・布朗不曾寫出《達文西密碼》(The Da Vinci Code)這本暢銷書,而猴子或電腦率先產出了《達文西密碼》這個文本,那說猴子或電腦是作者有何不可?畢竟,如果我們承認《達文西密碼》等於某個特定的文本,那麼這個文本是由人、猴子還是電腦所寫出來的,根本就無所謂了。
- 這個案例改編自數學中的「無限猴子定理」(infinite monkey theorem)。歷來對於這個定理有許多不同理解,其中一種對該定理的理解如下:只要給定無限長的時間,機率再小的事件都有可能發生。
- Nelson Goodman and Catherine Z. Elgin, “Interpretation and Identity: Can the Work Survive the World?” Critical Inquiry, 12(1986), pp.567-574. 由於古德曼是第一作者,方便起見本文只提古德曼。
- 書籍的刷次通常內容都會一樣,若有不同會以版次區別。
- Jorge Luis Borges, “Pierre Menard, Author of the Quixote,” in Labyrinths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1), pp.62-71. 在這篇小說中,米納所寫出的其實只是塞萬提斯作品的一部分而非全文。方便起見此處省略這個細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