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寫改變過什麼?——中國新聞業的凍地絕境

冬日的北京,有著難得的藍天,胡同口是賣饅頭與維修機械的小販,一排大叔在路邊人行磚地就著板凳坐下,圍起布巾,在白楊樹下理起髮來。日子若想過得尋常,在這天子腳下討生活倒也舒服快意。
友人Z將車開出巷弄,送我去車站,途中問起我台灣媒體情況,我說:「慘啊。」
他笑了笑,說大陸也慘。
「你們可是投入很多資源做深度報導的。」我對此疑惑。
我總認為,政治發展已經穩定的國家,不太容易見到歷史轉折,但在中國跑新聞,簡直就是在歷史線上奔跑,一個不注意,便成了歷史的見證者。更別說,中國幅員廣大,什麼故事都有,若能認真去跑,隨手一抓就是夠份量的報導。作為記者,怎不對這等新聞寶地興奮?
但我也知,這興奮與緊張,也伴隨著諸多限制與監督;這正也表示,若得到一手好報導,是無可比擬的成就。
有那麼兩年,我時常往返兩岸,於是結識一幫中國記者,看他們神采奕奕,高談闊論,雖對時局不滿,仍能大展拳腳,大有可為的。比起台灣記者對不重要小事窮追煽火、被動等待新聞,甚至對責任怠惰,在報導上馬虎,在呈現上隨便,沒有格局少了氣度,號稱擁有自由却濫用自由,這些中國記者擁有強烈企圖心、雄辯滔滔,對世界局勢有立場、對港台好奇且羨慕,隨時都在練筆,隨時都在研究國外媒體報導,精益窮精。
當我批評台灣媒體的安逸懈怠時,他們都會說:「可是你們曾有過豐富精采、突破戒嚴限制的新聞時代,你們有過豐富的環境、人權報導,然後你們才有今天的隨心所欲。」
是的,他們再積極,都還是處在一條艱難的邊界線上,既知自己眼前豐富待挖的題材,也明白稍一不慎連自己都從社會上消失的困局。
約莫四、五年前的秋天,我在上海遇見了揭露三聚氰胺毒奶粉的簡光洲。在毒奶粉事件爆發當時,媒體記者多半知道真相,就是沒有人敢告訴讀者禍首是誰。某一天,簡光洲糊里糊塗地,不知道哪個筋不對,在部落格上點明是三鹿集團,竟因此而爆紅,成為全國知名記者。
飯局上,眾人七嘴八舌討論這件事時,簡光洲還沒到,便像說笑話一般議論這事,大談所謂「名記」的由來與意外。
一位女記者正色對我:「在台灣,每個記者都想搶獨家,對吧?但我們這裡,沒有人敢當第一個,因為那會付出很大的代價。」不論是得罪企業,或是得罪政府,都會丟掉工作,而工作一丟,如同全面離開新聞界,不可能再當記者了。中國記者因此萬分保守,若遇重要新聞,會互相告知,一起去「聯訪」,好分散風險。
「那簡光洲為什麼沒事,還變成了名記?」我不解。
眾人又吱吱喳喳了起來:「機遇啊機遇啊,在中國當名記是要靠機遇的。」正因為所有媒體都曉得三鹿集團賣毒奶粉而不敢指名,所以傻子簡光洲一失手,全國媒體追湧上來報導,越報越兇,資料越足,簡記者便被沖上新聞歷史浪頭,記者這職因此穩固。
台灣記者得獨家是「三分天註定,七分靠打拼」,中國的記者想當「名記」,除了自身努力還有勇氣,還要拿捏那麼一點點「時機」,但那顯然困難許多。
不過兩年時間,那席間笑談荒謬事的眾自由派記者們,竟都已不在線上,辭職的辭職,返鄉的返鄉,不問事,不拿筆,過自己的日子或換個跑道管社區的事,就像餐桌上熱騰的菜就這麼冷了,那盛宴是如夢幻泡影一場。
簡光洲也卸下記者職務了。2012年,他在微博上貼文宣告離職:「東早十年,是我人生中最寶貴的青春,所有的悲歡,所有的夢想,所有的忍受都是因為那份純真的理想。好吧,理想已死,我先撤了,兄弟們珍重!」沒有說明原因,於是引發揣測。
那一年,許多新聞事件的主角都是新聞人,如《南方周末》的年末的新年祝詞,只因出現「憲政」二字就被刪改、《人民日報》副刊主編徐懷謙自殺、南方報業集團諸多調查記者受到壓力被迫辭職……。簡光洲不過就是其中一個反應中國記者境況的人而已。
當時,一位媒體主管便說,輿論監督不能依賴於某位有良知的記者個體:「我們尋求的是一種良心、是一種正義、是一種公平,而我們所得到的卻是經常被打壓、是眼淚。」
但因為見過那些記者的意氣風發,我樂觀以為,他們在鋼索上跑新聞仍能有這成績,有這麼精采的報導,那麼假以時日,終究能等到媒體管控日漸寬鬆、春暖花開之時。

秋涼了,冬的腳步正在逼近
時間又過了兩年的現在,媒體環境有改善嗎?顯然沒有,而且更為嚴苛。
一到北京,在媒體任職的朋友們紛紛感嘆著大批時政與調查記者離開新聞界,有的去做生意,有的去搞網路。Z在車途中大嘆現在中國媒體狀況的慘狀,「流動率太高。」越是有理想,越是無法待,特別是以自由派著稱的南方報業集團,被政府壓制得更為嚴重。
「過往,給你時間給你錢作調查報導,如今,時間還是給你,但錢少了。」Z說再也沒有過去的空間之外,審查特別嚴格,對大部分記者來說,調查還是去調查,採訪還是去採訪,但不一定能刊得出來,「政治風險變得很高。」
與簡光洲幾乎同時辭職的資深調查記者Y,目前在鄉下經營民宿。他曾寫過幾篇經典的調查採訪,卻不敵政治壓力而離開新聞界。
在北京城內的一個咖啡店,他翻著數本筆記本找尋我要的資料。據說,他每次採訪都可寫完一整本筆記,這些筆記仔仔細細收藏進幾個箱子裡,像是理想青春就這麼封存著。
見他撫摸筆記本如見初戀般深情,我不免問:「既然對新聞這麼熱情,為何辭職呢?」
「寫這麼多字,又改變了什麼呢?」說這話時他牽動一下嘴角,我也不知是睥睨,或是苦笑。
我曾在《學運世代》中讀到同樣的句子,現任蘋果日報社長的陳裕鑫在書中便自問:「寫了上千萬字,到底改變過什麼?」他是學運世代第一位媒體總編輯,是見證台灣解嚴與重要歷史的媒體工作者,他竟然也說了這句話。
在我還沒來得及思考陳裕鑫與Y說同樣的話,卻有哪些差異時,Y又繼續說:「我的記者朋友們,被抓的被抓,被關的被關。我至少還好好的在這裡呢。」這話,是慶幸或是自嘲,我也分不清了。
Y離職後,一名資深調查記者在微博感嘆他與簡光洲的離去時,意有所指:「秋涼了,冬的腳步正在逼近。」
北京的聖誕氣氛並不濃厚,天氣也不太冷,暖陽壟罩著冬日,但對媒體人來說,冷的並非體感而是心理。
開車行過上班堵車潮的北京城,H也與我討論起媒體困境。他曾是Y的上司,看著新聞報導的強度下滑,只說這時局真不好,還想做新聞的,都轉往網路了:「如果網路公司能上市會好些。政府雖然會管,但比較難管,畢竟,網路這麼龐大的資訊量,都淹沒了。」
儘管仍然飽受控制,但損失卻小:「當局有意見,刪就是了,不費力。但對紙媒來說,卻是上萬成本付之一炬,都排版,都印了,要重做或下架。這損失非常大。」總走言論前方的《南方周末》就屢屢遭殃。
局勢越來越嚴峻了,H說這氣氛大家都感覺得出來,也越來越感窒息,日前,一個在公益組織做事的朋友才被放了出來,理由呢?我問,「做公益,能得罪政府嗎?」H笑著搖頭,表明不知理由,也沒有理由,但是,「據說他去複印了佔中的資料,才被抓。」
這樣的風聲鶴唳,已在網路上傳遍,幾個大學教授與媒體記者陸續被開除,習近平政府簡直是全面與自由派為敵。
根據紐約時報中文版轉述去年秋天遭降職處理的新聞學教授喬木的說法:「習近平上台之后,對自由思想人士的壓力和控制確實變緊了。」喬木本人的降職,一部份歸因於公開支持多黨制選舉與言論自由。他說,越來越多的朋友和同事在經歷恐懼和騷擾。
去年,十月,許多網站都出現了習近平的指示:「絕不允許與黨中央唱反調。絕不允許吃共產黨的飯、砸共產黨的鍋。」在內部規定中,他更直白地抨擊自由派思想是毒害黨員的不利威脅,呼籲各級官員清除與當代中國馬列主義思想基礎相悖的理念。
人們可以大可不管什麼言論自由、新聞正義或普世價值,但總會娛樂總會看戲,當所有文創作品都必須要受到檢視,給他一刀,武媚娘無法嬌媚,對創作限制的種種規定陸續上路,而這個網站關,那個網站撤,連上個谷歌都失去自由,封閉在城牆內,過著平凡無奇平穩的胡同口好日子,是否還是好日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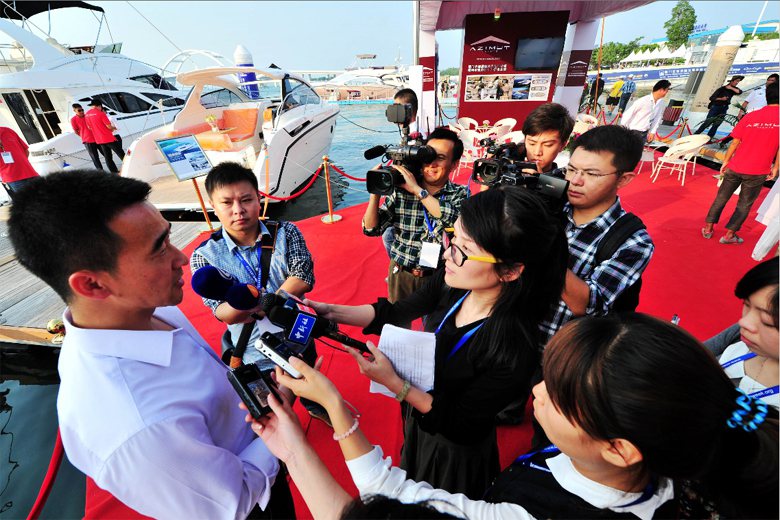
天子腳下討生活,是否真是值得的生活?
當我閱讀李承鵬在北大演講稿時,見他提及某個時代:「整個國家失去了說話的能力,你不可以說出你的本能——我餓了;你不可以說出你的情感,我愛你;你也不可以批評領袖的話——屠殺同類是不對的;你不可以說出科學的話,得承認畝產確實兩萬斤;你甚至不可以描述大自然——比如太陽很毒,那是影射領袖。說話,作為上天給動物的一個本能,一種思考方式,一種權利……統統被切去了。我們比司馬遷還要慘,人家切去了后,寫出偉大的史記,我們卻出現很多垃圾作品。」
他在演講中強調:「我不是一個有政治追求的人,我只是追求自己應得的權利,說話和寫作的權利。可是這個國家的民眾正在失去說話的能力,彼此代以各種假話謊話鬼話。」
讀此文時,我正巧在北京大學旁,在五道口,想起那兒曾有一棟高聳氣派的谷歌大樓,北大友人還特別指給我看,語氣驕傲。
我想起了海協會會長陳德銘在台灣參訪時說,是谷歌排斥了中國。這話說來令人吃驚又發笑,真想問他你說真的還假的?
H說:「他當然知道這是謊話,但中共的問題是,他知道自己在說謊,也知道我們知道他們在說謊,我們也知道他們知道我們知道他們在說謊。但他們已經安於這謊言之下。」
就是索忍尼辛說的:謊言成為這個國家的支柱產業。
然新聞記者的存在,不就是要戳破這些謊言?
當我想起了Y對我說「寫了這麼多字,改變了什麼」時,我只想說,能書寫,就已是改變嗎?至少,有種聲音在縫隙中透出,有一天,他會驗證這個時代的虛假。
出版被禁、言論被封的李承鵬,恐怕也是支持我的,他在《全世界人民都知道》一書中,便說:「比起思維的結果,思維本身就是一種尊嚴。只是總有人放棄了這過程,放棄去想,為什麼世界上最快的動車可以被一記閃電穿,世界上最幸福的孩子們的校舍,倒塌之後竟沒發現什麼鋼筋。」
「我的寫作不是為了真理,真理離我太遠,我只不過為了尊嚴。智力的尊嚴,記憶的尊嚴,親情的尊嚴,表達的尊嚴,生育的尊嚴……這些事,不是什麼大事,這些道理,卻不該被埋沒。尊嚴如此奇怪,它並不值錢,可是我們僅有。尊嚴本身不是作品,卻能讓你通體放光,兩眼澄明,自己是自己最好的作品。」
他說這道理全世界人民都知道。
我說恐怕只有自絕於外政治人物不明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