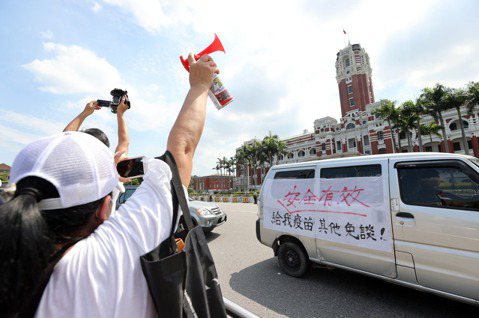大學生存之道:「研究精算師」還是「教學傳教士」?

日前在科技部的一場會議中,一位學術領域上德高望重的前輩,透過具體研究數據的佐證,指出一個驚人的事實:近年來台灣學生科學素養表現趨勢成對數函數下降,科學教育的研究論文發表趨勢卻成指數函數上升。換成白話講,就是科學教育研究的論文發表越來越多,但是學生科學素養的表現卻越來越糟。
這項觀察其實是台灣學術研究的縮影,以論文產出掛帥的結果,表面上看起來似乎是研究卓然有成,但是實際上這些成果竟然無力解決相應的真實世界問題。高等教育原本應該是社會創新的火車頭,但這幾年卻似乎變成了拖垮產業轉型的拖車,造成學用落差的始作俑者。看看目前大學裡的概況,或許就不難瞭解這些問題的緣起。
「研究」與「教學」是現代大學最主要的兩項工作,其中一種類型的老師我稱之為「研究精算師」,他們專攻一些輕薄短小的研究主題,因為它可以短時間量產,所以容易累加、衝量。這類學者就像是房地產的投資客,非常會觀察學術議題的風向球,投資眼光之精準總是讓他們可以在勢頭上賺個幾筆。在「研究量」需求恐急的時代中(為了擠上各種排名),這類炒短線的學術價值經常可以被主流的學術價值買單,在現今的學術規則中,這樣的做法最是一本萬利的投資。只是這類研究雖然可以在大學的計價標準中不斷地集點換現金,但是「多一篇不多,少一篇不少」的宿命注定了它們終究只是在學術殿堂上妝點樑柱的小飾花,「平庸」是他們揮之不去的陰影。
相較於「研究精算師」的左右逢源,另一種極端對比的教師類型就是「教學傳教士」。這類教師用一種幾乎是義無反顧的執念在捍衛教學的價值,尤其在華人的社會中,「教學」隱涵了一種「無私」及「奉獻」的默會形象,不問收穫、不求回報常常是我們對於許多經師、人師,甚至是至聖先師的描繪。這種投資在大學的計價標準上,幾乎是血本無歸,因為「教學」的效果很難被準確地計量或評估,例如,你總不能說學生未來在社會上的驚人成就是來自於你某一次課堂上發人深省的勉勵吧?
即便如此,大學裡面也仍然存在這一群對於「教學」念茲在茲的教師,願意將自己的生涯奉獻於教學工作,為了捍衛教師的尊嚴而奮力一搏。即便在這個過程中,他可能因為拿不出具體業績而升等受阻、前途黯淡。但這種類型的教師仍存在風險,由於長期荒廢對於知識的細緻考察,可能深度讀書的機會少了,連帶地課堂上講的笑話開始重複了,心態也憤世嫉俗了。
這兩種類型的教師常常在學院裡面彼此看不順眼,久而久之形成了教學與研究之間的對立,學術與實踐之間的分離。其實「研究精算師」助長學用落差的加劇,績效導向,往往自溺在學術點數的收集;「教學傳教士」把教學當成奉獻,也因此在精神上承載過多的道德光環,卻缺乏與時俱進的觀念深化,兩者最終都可能同樣成為守舊與倒退的代表,進步與創新的拖油瓶。
教學與研究果真如此互斥嗎?著名的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理查費曼博士(Richard Feynman)曾經提過,他為什麼不願意接受許多研究者所嚮往的「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邀約,而執意留在大學中教書,主要原因是因為透過與年輕學生的互動,可以激發他去思考許多最原始的問題,哪怕再基本的疑問,都是他自己重新再思索問題的動力及契機。
他曾說過,在課堂中,你可以思考一些已經很清楚的基本概念,這些知識很有趣、令人愉快的,重溫一遍又何妨?另一方面,有沒有更好的介紹方式?有什麼相關的新問題?你能不能賦予這些舊知識新生命?他因為這樣獲得學術研究的最高桂冠。
在新時代的教育浪潮下,如果可以有更好的大學生存之道的話,我想那應該是精算師與傳教士的混合體,要有前者的敏銳及效率,更要有後者的誠懇及執著,或許這樣的話,那兩條負相關的指數與對數曲線才有交會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