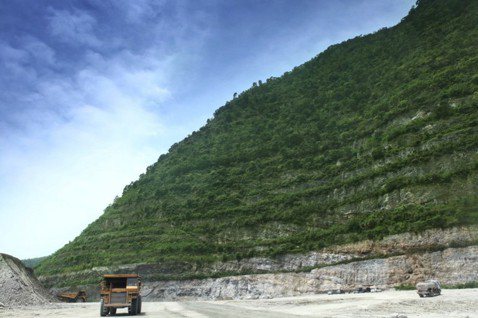野生動物保育與動物保護在台灣的衝突有沒有解套的可能?

這一年來有關「流浪犬救援」與「野生動物保育」議題之間的衝突事件大幅增加。除了媒體上最常見的「忠犬救主咬死保育類的蛇」最容易引起部分動保團體和野生動物保育團體的互相叫罵之外,「是否應該讓山上與高灘地的浪犬離開且不可繼續隨意餵食」是部分動保團體與保育團體之間互相攻防的主要議題。
大家一聽到「野生動物保育」和「動物保護」時,大概都會覺得「聽起來好像喔」,「好像都在愛動物啊」。事實上野生動物保育和動物保護之間本來就不應該存在任何衝突,因為野生動物保育針對的重點是「無論對象為野生或圈養個體,應維護野生動物在棲息地的生存與多樣性,並避免不永續的利用方式」,而動物保護的重點乃是「無論其為野生或馴化動物,在理解許多非人動物亦具有近似人類的感知能力的基礎上,維護動物福利,確保動物在任何狀況下受到良好的照顧與接受最少的痛苦」。
但是為什麼源自西方社會的動物福利理念一到了台灣就會產生衝突?
一、不同社群在其生命經驗中對「動物」認知的出發點完全不同:
野生動物保育團體通常主張野生動物不應該被圈養,就算被圈養也只能是為了教育、研究與復育的需求。在利用方面,保育團體通常認為最好只限於少數有發展歷史的經濟性動物,而在寵物選擇也最好只限於長期被人類馴化的物種,包含狗。也就是說,保育團體的關切重點在於整個生態體系的完整與生物多樣性,因此野地物種的生存權永遠會高於被人類棄養而野化的動物(包含各個外來入侵物種)。而流浪貓犬這類的生物被認為不應該出現在野地中,而應該好好地被人類養在家中照顧。但是部分動保團體與「有力人士」的生命經驗並非來自整個生態體系的多樣性,而是對貓狗的執著與熱情。貓狗的確在人類歷史上佔有相當大的比重,貓狗與人類的互動方式、貓狗的知能、人類對貓狗的理解也遠高於其他動物。所以有人會把貓狗稱為「毛孩子」或「家人」,甚至主張貓狗在法律上應該要能夠行使「權利」也就能夠被理解。但是我們不會在其他寵物社群(例如大型鸚鵡或是寵物蛇)看到這些動物被當成小孩或是人。
二、對動物行為意涵在解讀上的差異:
保育團體或野生動物團體,基於行為科學的基本原則,傾向於不以人類的觀點與文化習慣來解讀動物行為,除非解讀通常趨於保守。那麼貓狗呢?事實上有關貓狗的嚴謹科學研究相當多,但是在台灣社會中,深入地談動物行為不會有什麼言論市場,所以在媒體上就只剩下「過度簡化的教戰守則」或是「假鬼假怪的心靈溝通」。然而深入地瞭解貓狗的行為,和使用人類主觀解讀來誤判貓狗行為的意涵,常常只有一線之隔,也難怪台灣媒體上到處都是「動物報恩」或是「忠犬護主或守靈」的鄉野奇談。這些訊息對於某些對貓狗行為不夠了解的動保團體來說很暖心,但對於保育團體來說簡直就是不可思議,因為過度腦補動物行為的意義,反而有害動物福利。
三、對動物的可操控性上的認知差異:
白話一點的說,可操控性就是「我要你做甚麼就做甚麼」。保育團體因為不主張圈養大多數野生動物,所以自然會認為野生動物是不應該受到管控與約束的。但是馴化動物因為是被人馴養的,所以人類對其行為應該有比較高的可預測性。動保團體花比較多的時間近距離照顧動物,與動物朝夕相處,因此對於個別動物的行為具有較多的理解,這也就是為什麼要保育團體去處理浪犬是很難的,因為只有愛心爸媽會花時間和這些高智能的動物搏感情,讓牠們願意接近人。
四、對「野生動物」一詞的認知差異:
我在過去的文章中提過,「野生動物」(wildlife)、「馴化動物」(domestic animals),與「野化動物」(naturalized animals)之間的差異。貓狗是被人類馴化至少一萬年的人擇(artificial selection)產物,因此就算牠們都還有狩獵的野性,或是可在野地中存活,都不會被認為是「野生動物」。有些因為南島民族的播遷歷史與狩獵需求而出現的早期犬種(例如台灣犬與澳洲野犬)雖然跟隨著原住民長期生活在山區野地,但如同其他馴化動物一樣,牠們仍然不會被視為野生動物,也因此需要受到人類的照顧與看管。如果明瞭了定義上的差異,就能了解「為何不能讓浪犬留在淺山、保護區與國家公園」,因為牠們並不是野生動物。
五、相關法律之間的模糊地帶與漏洞:
若觀察所謂的先進國家在動物福利議題上的論述發展、法律內容與政策執行,應該不難發現,先進國家並未將動物福利概念與施作限用於「指犬、貓及其他人為飼養或管領之脊椎動物,包括經濟動物、實驗動物、寵物及其他動物。」而是廣及野生動物。所以無論是在外來入侵種的移除、人道處理、救援、野放、收容、運輸、展示、飼養、繁殖,都具有最基本的動物福利要求。然而在台灣,動保法雖在母法中明確地規範管理適用範圍為「人為飼養或管領之脊椎動物」,然而因為待解決問題的輕重緩急、中央與地方主管單位人力與專業的短缺、輿論關注的方向與資源挹注的多寡,絕大多數的施行細則與規範卻僅為「貓狗」量身打造(例如「特定寵物」的定義)。也就是說,我們有一部以動物福利為出發點的動物保護法,但在實際的執行上卻難以顧及母法中的精神,也就是「尊重動物生命及保護動物」,更別說野生動物的動物福利了。
野生動物保育法的主旨乃為「保育野生動物,維護物種多樣性,與自然生態之平衡」,其母法的精神上本來就不積極鼓勵「利用與圈養」,因此過去在動物福利議題上,為了維護不同事務之間主管單位的權責區分,野保法僅能在「原則禁止例外開放」的保育類動物的輸入與圈養上稍微加強管理,但無法發展上述動物福利事務的「標準」與「技術」。
至於國家公園法則依據第十三條第八款規定,明文禁止餵食遊蕩動物。只是若單看這個條款的文字,則限縮了「以細緻的餵食協助野化犬捕捉與收容作業」的操作空間。

六、相關單位在政策與施作品質上的落差:
動物保護法是一個相對來說比較新的法律,然而動物保護論述在台灣的學院中的發展卻很緩慢,或受限於由貓狗兔子、部分經濟動物與少數實驗動物案例所發展出來的作業流程與見解。也就是說,在實務上,動保法的執行面無論在關照物種多樣性、人類利用需求的多樣性、或文化需求的多樣性都是非常缺乏的。正因為本土論述與辯證的缺乏,或多半來自情感性的呼籲而非科學證據(無論是自然科學或社會科學),對主管單位來說就會陷入「若依法執行會缺乏諸多配套措施與專業知識」與「當下只要不得罪強悍的民間團體就好」的施政兩難。
目前全台灣各縣市只有台北市與新北市把「野生動物保育」與「動物保護」業務合併在一個處室中執行,因此兩造的需求與取捨至少能夠在一個處室內協調溝通。然而其他各縣市若沒有新北市與台北市的編制與資源,保育與動保事務則會四散在傳統的農業、防疫、與環保單位中。而與這兩個議題亦有相關的「漁業」單位(指水產動物與寵物繁養殖),則一向不被納入討論。如果地方行政單位人員的業務龐雜,業務主辦人之間缺乏很好的溝通協調,主管也缺乏執行面的中心思想,那麼中央與地方,以及地方主管單位之間的施政品質落差,就永遠讓NGO有抗議不完也很難自圓其說的題材。
七、媒體報導的素質落差:
近年來隨著民間團體與網路社群的迅速成立,以及媒體關注的力度增加,我們幾乎每天都能見到「動物保護」或「野生動物保育」的相關報導。雖然前者「被製造」出來的資訊量(例如「某隻狗睡相如何然後萌翻多少人」)遠遠高於後者,但是較為深刻的動物保護概念、政策制定與科學議題卻很少在媒體上有完整的呈現與討論。也就是說,多數媒體不願意去碰觸需要辨證反思的部份,而使用萌照與溫情來賺取點擊。不過一旦出現衝突或抗爭場面,在「有畫面可拍而且新聞稿好寫」的基礎下,真正的議題與癥結便很容易被激情與片面之詞所掩蓋。無論是傳統電子或平面媒體,對野生動物保育與動物保護議題的來龍去脈相當清楚的媒體記者也相對少,當新聞稿中出現「動保團體」、「保育團體」或「地方人士」這類過度簡化立場與論述的標籤、再加上媒體社群編輯下標時主觀立場的引導,有些細緻的議題就難以浮出水面,而媒體新聞的留言區就會只剩下不同陣營人馬的叫罵。
八、不同社群之間因為不瞭解所以互貼標籤:
經常關切動保訊息的人應該對「毛保」與「狗保」這些標籤不陌生。而「野保」則是近年某些動保團體對野生動物保育團體的新稱謂。在互貼標籤的情況下,我發現除了鞏固己方陣營的向心力之外,對議題的完整理解與解決衝突是沒有幫助的。
舉例來說,野保團體經常指責愛心爸媽餵養流浪狗是不當的行為,然而愛心爸媽也分很多種,有些細心的愛爸愛媽餵養流浪狗的最終目的是能夠達成捕捉、絕育與收容的目標,因為山區與高灘地之類的野化犬並不像一般沒有野外生活能力的品系犬容易捕捉 ; 在強行捕捉的情況下也容易造成人員與動物的傷害,而違反動物福利的原則。因此比較細緻的餵養手段會採用限定食材、定點、定量、固定容器與馬上清理的方式進行。然而也有不少的民眾採用隨意傾倒廚餘、給予浪犬不當食物、製造髒亂且不處理的態度引人垢病,污名化了整體動保團體,使得許多尋求以細緻方式解決流浪動物的團體蒙受不白之冤。
然而野保團體必然因為「不愛狗」所以才要讓浪犬離開淺山、保護區、國家公園與高灘地嗎?事實上並非如此。許多野生動物保育人士也養狗,但是基於對大自然的尊重,所以認為狗這種寵物就應該待在家中,被照顧,而不應該放任其接觸野生動物,製造跨物種傳染病的散播,並造成無謂的傷亡。
所以動保與野保團體在「好好照顧狗」一事上並非沒有共識,但這些共識卻經常被歧見所抹滅。
九、對動物照顧品質評估上的差異:
許多野保與動保衝突事件中的癥結其實不在於「要不要讓浪犬下山或能不能繼續餵食」,因為「使用符合動物福利的方式讓浪犬下山或離開高灘地」大概已經是一個共識,然而問題在於收容所的品質與超低的領養率。如果收容問題無法被解決,無法讓動保團體放心,那麼就算浪犬能夠被捕捉與絕育,若原地施放,那麼野生動物一樣受害,週圍居民的安全一樣受到威脅。
此外因為「零安樂死」的政策壓力,所有的公立收容所都需要在帳面上呈現「零安樂死」的狀態,所以「把狗搬來搬去」或是「領養率都是我們愛媽去把狗救出來才有」的說法才會甚囂塵上。
但是收容品質要好到什麼程度才算是好?要比照台北市動物園養灰狼(所有狗的祖先)的方式嗎?還是只要有食物、一隻一籠、成犬幼犬大小狗分開、環境通風乾淨才是可被接受的最低標準?無論是野生動物或流浪動物的收容都是相關主管單位的痛處。
以野生動物來說,全台灣的野生動物收容中心只有少數幾個,造成最大空間壓力的是無法再回到野外的個體,尤其是台灣彌猴,以及原產國無法配合接收的走私野生動物。而且野生動物的處境比起流浪動物來說,社會的關注、政府與民間所投入的資源相對來說更少。我們聽過任何「民間的野生動物收容中心」嗎?或是有「野保志工定期去幫忙清理收容中心的欄舍」嗎?在社會資源的投入上,動保界或許可以試著理解野保社群的不解跟不平。
就浪犬的收容品質來說,有多少準則是公立與民間團體都能接受的?現行的法規除了規範公立收容所之外,是否能夠規範良莠不齊的民間收容所?一旦有些團體與個人宣稱自己散盡家產的情況下承擔社會責任,但其收容管理品質不佳時,公權力與其他民間團體又應該要如何介入處理?在這個時候,如果野保團體試著把「浪犬」當成「一種犬科動物」來看待時,或許也更能理解動保團體的憂慮。

十、在面對不同動物時道德底線的差異:
野保團體經常提出部分動保團體「只把貓狗當寶,其他都不重要」的質疑,然而動保團體也經常以為野保團體支持「為了解決流浪動物問題而支持安樂死」的主張。
在多年觀察部分野保與動保團體之間的攻防之後,我認為動保團體在主張上的多樣性其實被忽視了。有些動保團體是支持安樂死的,但是實施安樂死的前提在於「該動物的身體情況若勉力維持生命,反而讓生命品質更差,還不如執行安樂死讓他走個痛快」。但也有不少動保團體認為,應該陪伴動物到最後,因此無論是甚麼情況都不宜執行安樂死。如果人類的安樂死能不能法制化在台灣社會都沒有共識,那麼不管把動物當成「能或不能夠行使權利的主體」,安樂死或人道處理的道德爭議都會一直存在。而能不能執行必要且合理的安樂死,也直接衝擊到收容管理的品質與空間運用。
野保團體經常舉出幾個例子來說明特定情況之下安樂死的必要性,例如日本之所以能夠讓狂犬病絕跡,所仰賴的就是強勢處理遊蕩犬隻。而澳洲為了保護獨特的生態而撲殺因為白人移民而帶入的野化家貓,雖然也受到澳洲動保團體的抗議,但卻受到大多數保育團體的支持。在台灣,處理外來入侵的野化寵物(例如綠鬣蜥、綠水龍)以及動保法禁止持有的動物時,也都採取人道處理。因此野保團體無法理解「為何一遇到狗就出現雙重標準?」、「和人類歷史發生長久關係的動物並不只有狗,為何在政策上要獨厚狗?」,還有「狗是人類最好的朋友真的是放諸四海皆準的看法嗎?那麼其他動物怎麼辦?」
十一、除動保與野保團體之外的社群聲音
除了動保與野保團體之外,其實還有一種聲音,就是「社區居民」。從北到南,從西到東,許多社區居民經常抱怨野狗成群追咬路人,造成幼童與長者傷亡,當然也順便抱怨猴子搶劫。這些民意經常成為縣市政府、動保與保育主管單位一定要面對的壓力。這些社區民意還有幾個特色,就是人口老化。平常就被排除在動保與野保的資訊傳播體系之外,對社會的快速動態掌握緩慢,因此只要一開座談會,多數里民代表就會義憤填膺地認為「為什麼要餵狗製造髒亂?」或是「為什麼要保護猴子?」。
這些居民平常甚少接觸相關資訊,所以也很難理解動保團體和野保團體平常做了甚麼努力,連甚麼是「動物福利」都沒聽過。比起動保與野保團體之間的衝突,「如何說服當地居民管好自己的狗,做好絕育與寵物登記,並區分不同的團體」,似乎是另一個困難的議題。
如果這些教育與資訊一直沒有進入社區,社區居民一直以停留在幾十年前的概念向主管單位陳情,那麼相關主管單位就只好自己承擔責任,讓不同社群的需求在單位內產生衝撞與拉鋸。

所以,動保與野保之間的衝突有可能改善嗎?
其實不是沒有,但需要一些層面的配合。
首先,我建議雙方應該要能看見共識,而不要只看到歧見。在「大家都認為應該對動物好」的基礎上,動保團體(還有相關的學者、專家與獸醫)在援引國外案例與作為時,應該要瞭解到台灣的地理環境與歐美國家差異甚大:我們的聚落與山區完全鑲嵌,使得馴化動物和野生動物的接觸變得相當頻繁。為了兩造動物的健康與福利,應該要積極地避免馴化動物進入野地。此外,依據動物福利的精神,把關切的層面擴及貓狗以外的動物,還有野生動物,是幫助動保論述與政策施行更完整的一步。在這方面,或許野保團體能夠提供協助。
而野保團體在積極維護生態環境時,也應該要瞭解到動保團體主張的多樣性,試著了解部分動保團體對貓狗的情感,並與細緻的動保團體合作,讓浪犬的收容與領養作業能夠更加順暢,而非「只要讓狗離開山區與高灘地就好」。
在學者方面,我認為台灣的動保論述已經有相當充足的社會學、公共行政、法律、獸醫、公衛、與文化論述。然而最缺乏的部分就是「如何面對人對不同動物的大小眼」所衍生的道德不一致性或道德底線,以及許許多多「能夠支持行政作為的科學研究與論述」。在Hal Herzog所著的《為什麼狗是寵物?豬是食物》(Some we love, some we hate, some we eat: why It’s so hard to think straight about animals)提到人對不同動物態度不一時陷入的道德泥淖,雖然Herzog的論述中引用了幾個非貓狗動物的案例,但是那些案例仍然無法涵蓋我們在台灣所面臨的處境。「結紮以後的浪犬是不是就會喪失對野生動物的攻擊性?」、「愛媽愛爸的餵食能誘集多大範圍內的浪犬?」、「犬這種在食性上屬於機會主義者的動物真的會因為不去餵食而死亡嗎?」,還有「如何估計浪犬數量?」等這類的議題,都是動物行為與群聚生態學的範疇 ; 也就是說,想要解決浪犬問題,需要多方學者的合作努力,而不能只固守在個人對特定動物的情感面發牢騷。
在法律與行政層次上,也還有難題需要被解決。如果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自然保護區之類的管理單位需要救援浪犬,降低浪犬與野生動物的衝突時,通常需要地方的動保主管單位協助,才能讓捕捉到收容都能合乎規範。但只要地方主管單位認為自己的收容所不堪負荷,無法承接這些「大家都知道不會被領養的狗」,那問題就無解。但如果要編列經費來處理這類浪犬的收容問題,是要動保單位自己主動編列嗎?還是要由國家公園與林務局編列?如果這些單位編列了預算,到立法院去又被不明究理的承辦人員與委員以「不符業務職掌」為由而退回,那就會回到原點。就算編列了預算,預算能執行多久?會不會因此而排擠到其他業務?或是因為招標金額太低或缺乏評鑑機制而使得民間團體不願投標?也就是說,法律操作的靈活性、單位內與單位間的協調配合、以及經費編列與稽核這樣的細節,才會影響到相關主管單位的行政力度。
最後,龐大的民間善心要用到哪裡去?我們不要預設行政單位都是冷血無情,不顧動物死活的。事實上很多行政單位共同面臨的問題就是「狗沒有地方可去」,所以「只要有民間收容所願意收我們就給他」。收容動物需要土地、人力與管理,更重要的是稽核與評鑑。如果那些宗教放生團體能把每一次法會花掉的,拿來折磨無數動物的錢拿來支援浪犬的收容與安置(前提是不准叫狗聽佛經吃素),主管單位也能協助訂定管理辦法,相信事情也會往好的方向走。而且,「期待宗教團體能夠對動物多一點關切而非買來亂放」一事上,野保與動保團體其實也算是站在同一條陣線上。
「讓野保與動保團體不要吵架」在浪犬管理議題上只是枝節末端,如何落實源頭管理、飼養登記,與飼主責任才是治本之道。此外,如何加強社會大眾對狗這種動物的了解,以免將之視為飼養門檻低,可輕易獲得與丟棄與耗材,乃是生命教育的重要一環。
最重要的是,大家都需要多一點耐性,但我們也知道時間有限,因為拖得越久,收容所中的狗的生命品質更低,而野生動物的處境也更為艱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