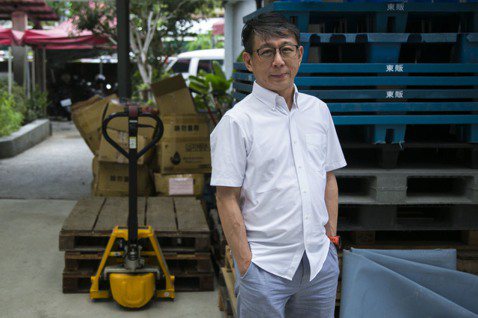將傷害說出口,為什麼要這麼久?性創傷如何侵蝕人的自我認同與思考

(※ 口述:諮商心理師郝柏瑋;採訪、整理:林宜蘭,鳴人堂編輯)
編按:台灣的#MeToo風暴延燒至今,許多性暴力傷害的受害者、倖存者們透過社群平台的自我發聲,得以讓私領域受侵害的過程進入到大眾的視野。然而,聲音進入廣袤的公眾領域時,也折射出許多質疑與不解。本系列針對「性創傷」、「男同志受害者」兩個子題出發,訪問了荷光成人性諮商中心諮商心理師郝柏瑋,以及同志諮詢熱線秘書長杜思誠、副秘書長彭治鏐,以各自專業與經驗,呈現更多元族群的性傷害及其複雜面貌。
本篇系列第一篇,荷光成人性諮商中心諮商心理師郝柏瑋以其心理諮商專業,並分享他在臨床個案看到的狀況,來闡述複雜的性傷害情境。
性傷害,如何侵蝕你的自我認同與日常思考?
當某一個人侵犯另一個人的界線,特別是在性上面,無論是騷擾或是侵害,受害者因為有很多顧忌沒有講出來,外界也不知道;因為各種因素而選擇繼續維持這個關係,可是久而久之,會開始影響日常生活的某些部分,譬如會開始懷疑自己:「我為什麼要?」有些人會形容:「為什麼要一直給人家糟蹋?」「我是自願的嗎?」這類的自我質疑,長期影響自我認同以及跟自己之間的關係。
平時性騷擾或是性侵害的人,如果在隔壁辦公室,或者不是很常見的主管,或許還算可以忍受,但某一時刻,譬如他的某個計畫成功了,你的心情就很複雜。如果你又剛好參與這個計畫,他感謝的人是隔壁同事,你會不會想說,「他是不是刻意把我除名?」、「是不是因為他覺得我很好欺負?」心裡會有很多這種「小劇場」運轉。相反地,如果他稱讚我,我又會開始懷疑,「是我的功勞嗎?」「因為他貪戀我的肉體?我其實沒有憑著實力?」陷入各種想像,讓人沒有辦法真正肯定自己。
因為處在關係中,我們可以觀察到對方,無論他的反應如何,都可能會牽動我們。假設你是受害人,你看到加害人有什麼成就,一方面可能也會某種程度替他開心,可是又會因為「替他開心」,認為「我怎麼會對加害自己的人還有這種感覺?」同時也有可能會生氣,「不公平,為什麼他可以,他明明就是一個暴力施暴者,卻可以有好的人生。」所以久了之後,受害人的整個世界觀,會感覺有裂縫,也就是俗話說的「三觀毀壞」。「到底是好還是壞?」這些許許多多細碎的念頭會長期侵蝕自我,人會很難相信自己,很多人的痛苦來自於這是一個慢性的、三不五時、不預期被引發的自我質疑。
性傷害為何特殊?是否有程度之別?
性暴力大概是所有暴力中,傷害程度靠近金字塔頂端的前幾名。許多政權之間的戰爭,在軍隊一到佔領地的第一件事,就是強暴當地婦女、小孩,或甚至男性——因為性是一個人很隱私、很脆弱,很貼近自己的事情。當這條界線被破壞,就是讓一個「我不想要」的感覺發生在我身體上,然後我無法控制。這會影響一個人對自己的控制感,使當事人產生「我對身體失去主導權」的感受,這對很多人來說是很大的打擊。
如果是外在的東西,它可以被切掉,會遺憾或難過;可是牽涉到性,就是牽涉到身體,人沒有辦法把身體切割掉,所以性傷害帶來的羞恥、罪惡或者是懷疑,常常會被引發,如影隨形。我個人覺得性暴力算是所有暴力形式中,蠻強烈的一種。

然而性傷害的程度之別,在我的經驗裡面,其實沒有辦法百分之百地說,直接性器插入,就一定比摸摸手來得強烈,因為它牽涉到「關係」、毀壞你三觀的程度,還有很多時候搭配上「情境」。
如果我們是伴侶,某一次喝醉了,我一直跟他揮手說「不要不要」,可是他還是做了,那這個情況是性器進入我的身體,可是性行為是我們平常也會做的,但是我那天沒有這個意願,可是我們又是伴侶,我理解成喝醉了,我只會說「你真的很煩,你就是聽不懂」,當事人可能會解釋成這樣子。
而換到另一個情境,如果對方是你很敬重的人,他在摸你的手,譬如他說,「其實我選你進來團隊,就是看你漂亮!」這個打擊會很大,除了能力沒有被肯定,每天也都會想到:我原本尊敬你的樣子、猥褻的表情、在我手上留下的感覺。雖然說創傷不能比較,但是我的意思是說,其實很多傷害的程度是與「關係」,「情境」、「角色」,還有「性接觸身體的感覺」,全部融合在一起的。事實上不太能夠完全就說這個摸摸手應該就還好,然後侵入就最嚴重,當然客觀上可以這樣說,但每個人經驗起來會滿不一樣。
受傷的人們,為何選擇繼續保持關係或討好?
我們最近對創傷的了解會發現,創傷大概有四種典型反應:戰,攻擊回去,比如打回去、罵回去,或是砸東西;再來就是逃跑。戰或逃其實都是一般想像受害人會做的事情,不過戰或逃其實都是急性狀態,我們遇到立即威脅時會採取的手段,可是如果有種狀況是你戰不贏他,又逃不掉,那就會出現第三種生存策略——「凍結」。
「凍結」有點像是我把自己靈魂抽離,暫時把感官封鎖,這樣子比較不痛苦。反正都要經過這一遭,我讓我的身體跟我切斷關係,至少保有活命。其實所有動物可能都會在戰不贏、逃不走時凍結。
另外一種很特別的,就是在長期關係中,不可能一天到晚凍結,你還是需要跟這個人互動的話,就會出現「討好」。討好這個形式其實也是為了生存,就是每天還是要活,所以必須要某個程度去想出的一種新解方,來理解彼此的關係。不能只用這個「加害/受害」的感覺去跟對方互動,因為這樣會每天都很痛苦,所以很多受害者會發展出一種,可能說是要合理化,但對我來說就是一個生存策略去解釋。
譬如有些人會說「這是我的小犧牲,是為了顧全大局」,或者是說,「其實我對他也是有欣賞的,所以某個程度我也同意吧」、「他有這個不好的部分,但他也有很好的部分啊」,就是會用一些思想去合理化傷害,不然的話每天都很痛苦。每天我只要想到他騷擾我、他侵害我,我要跟他同辦公室,我可能待不下去,但假設我必須待下去,那我就要有一些新的策略去解釋這一切。

討好還有一個狀態,可以從受害年齡來展現。我們會發現16歲以下的受害者,跟18歲以上的成年受害者,他們要能夠講出自己受害經驗的時間,差異非常大。16歲以下的受害者平均來說講出自己經驗大概是16到25年,而18歲以上大概平均是二到十年,會看到這個數據幾乎是兩倍差距,原因就是因為年齡或權勢之間的差距。
年紀小的受害人,可能某程度需要依賴所謂加害者的照顧(或教導),當中的權勢差距會讓當事人很難講出來,因為某個程度還需要依賴加害者。他們其中會思考的包括是「有沒有人會相信我?」所以兒童會用很多想法去合理傷害,讓自己的生活可以繼續。
在我們的文化裡隱含權力位階高、知識背景高、重要地位的人,或是有錢人,好像他們說的話比較能夠聽,這也是很荒謬。在台灣文化很特別的就是,其實你不知道為什麼要聽有錢人說話,有錢人好像什麼地方都可以說上一兩句,我們都會聽,這真的很奇怪。
另外還要提一個創傷的反應——迴避(avoidance)。
任何跟加害者或是創傷事件發生當下有關的感官記憶片刻,譬如說味道、他的呼吸、他的衣服、房間的氛圍,發生當時是下雨天,就會很討厭下雨;還有另一種:對於憤怒對象的迴避。
原本應該對加害人生氣,但卻因為各種因素無法直接對加害人生氣,因而轉而迴避,成為對自己或其他地方生氣,這使得受害者非常辛苦,就是很多受害人最後檢討到自己,而非理論上應該要檢討的加害者。

難以被他人釐清的傷害——創傷記憶碎片化
人們常常有誤解,以為事情發生,創傷就在那。假設我小時候被叔叔性侵,但是那個情境可能在你還是小孩子的時候理解起來是:「叔叔很開心,我也很開心他送我東西」,其實我不知道那叫做性侵害。我只知道「叔叔每次這樣做,他就會買禮物給我」,直到可能是青春期,或者是上了性教育,有人告訴你、你學到之後,才恍然大悟「這叫做性侵害!」理解自己被傷害,這是第二時間才搞清楚的事。
有些時候即使成人,可能模模糊糊不太清楚,可是看了MeToo運動,有人在描述,就覺得跟自己的遭遇很像,講他人的症狀、身心痛苦等等,才可能標示「對,我也有」。那這不是只有發生在被害者,加害方也可能是,他本來可能以為「大家不都這樣?」看了之後才發現「原來我對人家做了一件這麼不好的事。」所以事實上很多時候是後面遭遇到的事,新學到的,或是被標記的事物,才讓人們重新回過來想經驗為何。
剛剛說的這是一種情況,另外一種就是剛剛我們講的──凍結。有些經驗真的很太痛苦,或無法理解,它會被解離開來,被凍住,所以很多人其實在被侵害的那一段時間,可能他都不記得,不是他刻意的,是他的身體保護機制。
曾經有個案跟我說,他一開始是先夢到一個情境,嚇到,然後他開始會懷疑,「這是記憶還是我想像出來的?」接下來「夢境」越來越明顯。譬如說我的個案是十幾年來,從來沒有想過,也沒講到過這件事,然後他一開始覺得自己瘋了,為什麼這個東西會如此歷歷在目,可是慢慢才發現這件事是真實發生,他自己很驚嚇,就是創傷記憶像是異物一般,突然產生出來,那個經驗會令人很慌張。
上述所說的對傷害當下的失憶,或是記憶碎片化,這個其實蠻常見的,就是因為性傷害實在超乎我們的理解,所以當事人沒辦法用現有的解釋系統去理解,留下的都是一些片片段段的東西。騷擾也會有如此的狀況,就是前述我所說的,經驗本身有很多因素夾雜,所以這個騷擾可能對他的程度很大,也會變成是一些碎片記憶。
被害者在追求自身公平正義的時候,往往會訴諸法律途徑。但遺憾的是,因為法庭就是講求具體證據的地方,而上述的創傷症狀,是目前學界、實務界都一直在討論的。法庭的設計某個程度蘊含「人是一個理性人」,是可以陳述自己經驗的主體這樣的遇上,但是事實上會發現,無論是心智障礙、創傷,或是這一類遭受性暴力對待的人,他都沒有辦法符合這個設計,因為受害本身就是一個不合理、非理性的事情,我要如何陳述這個對我來說非理性的經驗呢?其實是蠻難的,所以我覺得所有的司法人員,可能都需要有相關訓練,同時在程序上,可能會需要比較柔性的部分,譬如說陪伴,或者是先做一些準備。
對我而言,我的個案他們最受傷的都是法庭上某些質問,但是這個質問其實是可以調整的,應該可以不用用「你怎麼會不記得發生在你身上的事?」「你有沒有隱瞞什麼?」對於受害者來說,很在意的是歷程,但當司法官要求他們「講重點」,或對卷宗搖頭,都會讓受害者非常受傷。
※ 本文與《德國之聲》共同合作,延伸閱讀請見〈性騷、權勢、民運光環?燒向王丹的MeToo控訴〉、〈MeToo的代價:王丹事件折射的同志困境〉系列報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