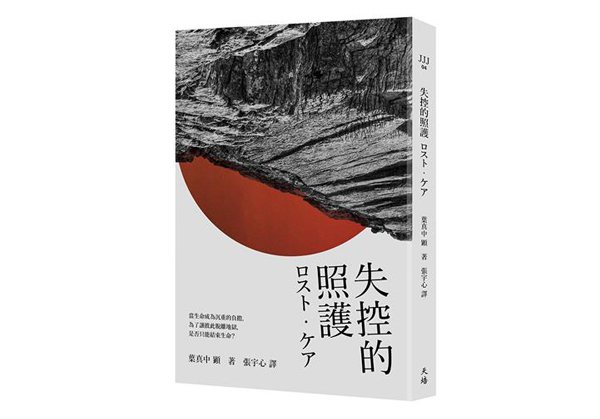別管養生了,先想想送死吧——讀《失控的照護》

2010年,台灣總生育率跌破1%。
2016年,台灣老人數達311萬,將第一次超越小孩數。
家庭照護者當中,每五個就有一個罹患憂鬱症,65%有憂鬱傾向。
文玲從小住台北信義區,23歲的時候,大學剛畢業進入公司不到一年,這時候她母親罹患癌症末期,她就辭職專心看護癌末的母親一年,「那時候我真正體驗到久病無孝子」。後來印尼的阿姨來台幫忙看護一兩個月,文玲也還年輕,撐過了一年,將母親入土為安。沒過幾年,她高齡90歲的父親需要洗腎,三天兩頭要跑醫院,工作忙碌讓她擠不出時間,也無法像以前那樣隨侍在旁,半夜為親人換尿布。最後文玲請了印尼看護到家,文玲的母親是印尼華僑,從小教文玲印尼語,所以可以跟移工講講簡單會話。可是她現在還是不知道,移工為什麼要拋下了他們不告而別?申請「合法移工」要花費幾個月時間,台灣本地的看護一個月要價七八萬元,比她上班的工資還高,逼不得已她決定僱用逃跑移工。
小文玲一歲的陳先生看起來像是個中年人,白頭髮長了不少,住在新竹湖口鄉。他大學剛畢業,就在家照護失智的父親五年。陳先生的母親也是印尼華僑,因為住在加里曼丹客家村內,不懂印尼話,從小就看見華人和印尼人之間的衝突,對印尼人有根深柢固的厭惡,這種情況到了台灣依舊。後來印尼看護來照顧她先生,但雙方相處狀況甚至比單純的語言不通還差。無論是城市還是鄉村,文玲和陳先生這樣的年輕人,二十歲就在做別人五十歲才做的事。
這樣的生活,究竟什麼時候才會結束?
「這個世界上,是否存在死亡才能得救的事情?」
《失控的照護》以推理小說形式,帶出這類照護者處境的艱難。小說甫開場,是日本戰後受害人數最多的連續殺人案,下達唯一死刑判決,但受害者家屬不恨這個兇手,反而有「得救」的感覺,因為犯人殺害的是他們久臥病床的父母。犯人很年輕,而且不後悔,甚至認為這種做法也是一種「消失看護」——將尼古丁注射到老人身體,將其毒殺。犯人從事照護工作,對於受害者及其家屬的處境有充分理解,他自己也曾辭掉工作,拚死拚活照顧父親,但父親因為失智,連一聲感謝都沒有,甚至口出惡言。最後連他是唯一的兒子這件事都忘了。然而父親清醒的時候,曾對他表達「我想要結束,殺了我吧」。他自己也認為,作為一個人應該保有尊嚴,殺害父親就是報答他,也是自己獲得的回報。他決定了,「不要再怨嘆自己的時代。不管在什麼時代,怎樣的立場,都有自己該做的事」。
雖然做好了落網的準備,但警察及醫護人員都認為他父親是自然死亡,並未多做調查,這促使他決定「幫助」跟自己一樣的家庭,他利用職務之便,以「消失照護」來拯救照護對象,以及那些背負重擔而痛苦的家人。書中眾多角色雖然沒有犯案,但都有充分動機,可以說是精神上的共犯。
小說中檢察官的父親投入上億日圓,入住高級的老人之家,檢察官自己也知道:「雖然父親可以入住,但他自己大概沒有機會」。即使在同一個家庭裡面,不止是階級的差異,世代之間也存在差異。書中最後提及:
日本戰前與戰爭期間,不乏同樣規模或超過此紀錄的大量殺人事件,在當時被稱為「養子殺人」。因為彼時墮胎違法,而雙親無力照料的小孩過多,因此就出現收受金錢酬庸,然後帶走父母照料不來的小孩,再加以殺害的事件。
只是同樣的事,過去發生在小孩身上,如今則是老人。
這類加工自殺不只發生在小說,現實生活中,2011年曾報導美國一位高齡91歲的老奶奶,在ebay網站販售要價60美元由塑膠袋和管子所組成的自殺包,估計已賣出十萬美元,成交1600組以上。雖然不知道真正實施的人有多少,但老奶奶比任何人都知道人有這方面的需求。老奶奶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嗎?她很清楚,就跟《失控的照護》一樣,她說:「我做的事是改善這個社會。」(延伸:為父親做的最後一件事──讀《天堂計劃》)
完善的照護保險能否解決這個問題?小說中,在高級老人院工作的佐久間說:「根據照護保險,人被分成兩類,可以獲得協助跟無法獲得的人。」書中提到遊民沒有居住的地方,因此無法使用照護保險,所以他寧可犯罪入獄,換得有人協助上廁所和洗澡的尊嚴。
回頭來看,文玲和陳先生這兩家的父親都是榮民,但兩人都沒有資格入住榮民之家,除非沒有子女或子女無扶養能力。但那邊才有跟他語言相通的老兵,否則一般的安養院,住了進去,因為不會講台語,也無法跟大家看同一台電視。而子女的經濟負擔,幸好有家中固定有幾千至上萬元的就養金,成了家中的防護網,而且兩人已成年有工作能力,更令人擔心的是,下一代孩子若在國中、國小的求學階段,就面臨父母其中一方倒下的狀況,處境會不會更危急?
當父母老了,子女陷入工作貧窮,或同樣步入老年,天經地義的事變成無邊詛咒。照料孩子,期待孩子日後長大獨立。但長期照護的家屬只能期待不退步就是最好的情況,24小時的照護工作,讓人在休息的時候,不敢完全放鬆,就怕忽略被照護者的需求,更何況不養就是不孝的觀念,以及接受補助就是無能者的印象,當事人很可能拒絕申請服務,使得社會福利資源並未幫助到最需要幫助的人。萬一他們無法回應父母和社會雙重的「養兒防老」期待,發展到最後,很可能走投無路,發生孝子弒親的社會新聞。
有位年近五十歲的公司老闆告訴我,他已經物色好一家瑞士安樂死機構,沒有意外的話,預定和妻子活到八十八歲。其實要做到這點並不容易,因為這個機構會評估你是否有犯罪紀錄、精神疾病(包括失智)而企圖安樂死,評估期間約三四個月,你就在環境優美的村莊中,享受健康有機的食物,最後以注射的方式結束自己的生命,感受據說是二三十倍的性高潮,然後器官快速衰竭。這樣一連串的評估及服務,要價台幣五百多萬。這不是我第一次聽見關於瑞士的討論,若是不買房不生子,許多中產階級說不定真有能力和意願負擔這趟旅程。
死亡在未來的台灣說不定可能變成一件奢侈的事,有錢人得以好死,窮人沒有機會也沒有權利。有人能夠不依靠下一代,以自己的能力和意願決定生命終點,但更多的人或許像小說家張怡微說的:「人生都是事到臨頭的妥協,現實總不及想起來那樣迫人」,明天的事明天再想吧,不然就交給下一代來抉擇——如果我們還有下一代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