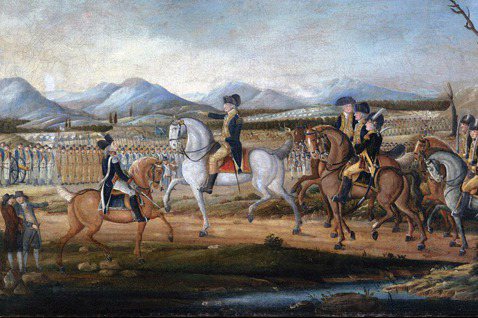真正想要的花朵

yo,brother,聽過這個故事嗎?
有一位旅人,獨自一人在雪地裡踱步。
他走到一座村莊,那裡的屋子是用茅草搭成的,上頭的白雪已結成霜,人們打著哆嗦從房屋裡走出來,他們的衣服也是用茅草做成的。
「可以給我你身上的衣服嗎?」
他們瞧見了旅人厚實的外衣,顫抖的伸出了手。
旅人將外衣脫給他了,那個人套上暖和的衣服,又叫又跳的回到茅草屋裡,然後,和他同樣穿著草衣的人,一個接著一個走了過來,他們抱著雙肩,搖搖擺擺,等到旅人回過神來的時候,他已經一絲不掛站在寒風中。
「哈啾!」
他打了個噴嚏,那些人,像是喪屍一樣,把玩著他的衣服,被撕成碎片,他們一人一片,貼在臉上,露出滿足的表情。
「這樣會暖和嗎?」
旅人心裡發出了疑問,但他也無暇管這件事情了,他們什麼也沒留給他,於是旅人走入了森林裡。
這次,他遇到了一個魔鬼,他乾癟癟的,好像很久沒吃東西了,他是被村人趕到這裡。他聞到了旅人身上,殘留的村民味道。
「可以給我你的手指頭嗎?」
魔鬼說,
「阿,不,這有點……」
「見到有困難的人,難道你不願意幫助嗎?」
魔鬼低頭坐在地上,露出憂傷的表情。
「只要一根手指頭就好。」
旅人嘆了一口氣,
「如果只是一根手指頭的話……」
魔鬼很高興,走過去咬下他的手指頭,旅人忍耐著,看著魔鬼咀嚼。
「吃不飽阿。」
「可以給我你的眼睛嗎?」
魔鬼說完,摘下了他的眼睛。
卡滋卡滋。
最後,旅人被吃的只剩下一顆頭,他覺得無所謂了,他走不動,也看不到,彷彿自己,並不屬於自己的一部分。
「謝謝你阿,雖然我還是吃不飽。」
魔鬼噘著嘴巴,肚子咕嚕咕嚕叫著,一股腦兒的,將剛吃的東西全部吐了出來。
「我看你應該是草食動物。」
旅人說。
yo,brother,這真是有點血腥的故事,我們換一點比較溫柔的。
在一座老舊的火車站裡,擺放了一座鋼琴。
不知道是誰擺放在那裡的,也許是要給路過的人彈的吧,但那琴鍵已泛黃,琴蓋上布滿灰塵。
人們都在等著下一班的火車,他們的腳步並不停歇,鋼琴安靜的等待著彈奏他的人。
有一個留著鬍子的年輕人停下了,他觀察著這台鋼琴,有點猶豫它是否還能發出聲音,但是他把琴蓋打開了,就像開了塵封許久的寶物一樣。
他撫著琴,嘗試每一個音階,鋼琴溫柔的回應他,核桃木輕輕括著琴線,就像索吻不成的貓咪。
年輕人的手像是爪子,但陶瓷做的地板沒有老鼠,只括出了一朵朵的旋花,華爾茲在他手中跳躍,既頑皮,又高雅。
有一個小女孩在他背後聽著出神。
她不同於其他的旅客,她並不忙,她的媽媽正在打電話,如果這裡有架攝影機,那她有足夠的時間可以對鏡頭做鬼臉。
但她只是站在這裡,靜靜的聽著。
年輕人沒有發現她的存在,他沉浸在他的華爾茲,直到她將小手伸入了他的詩篇,按下了鍵形的門鈴。
他瞅了她一眼,面無表情的回過頭去,小女孩只會彈單個音節,年輕人放慢了速度,讓這簡單的鸚鵡式語言得到了回應。
小女孩聽了很高興,大膽的將五根手指頭放上去,她彈了簡單的旋律,看起來似乎學過一些。
但是這個旋律並不是年輕人想要的,它太快了,年輕人騰出了一隻手,示意她彈的簡單些,小女孩換了一個,用眼神告訴他「這樣可以嗎?」可惜兩種旋律沒有和在一起。
所以小女孩乾脆停了下來,再仔細的聽著不間斷的琴聲,一步一步的,試著接在他後頭,想聽明白他說的話。
年輕人也盯著她的手指,一字一句的,傾訴心裡所想的,他們倆就像呀呀學語的嬰兒,沒有交集,但都不願放棄,直到了12月,終於找到了共同的單字。
「tomoyo!」
然後他們的語彙開始爆炸,有意義的,沒意義的,滿天亂飛,他們摘下幾個音符,做成了自己的文法,她負責主旋律,他負責副旋律,然後大手覆蓋過小手,只彈一種旋律的她,顯得有些沉悶寂寥。
他的旋律越來越高亢,一不小心,碰到了她的小拇指,這才發現,他已經佔了太多女孩的位置,雖然說,這裡原本全部都是他的位置。
於是他跳了過去,手肘來到小女孩的胸前,她嚇了一跳,彈錯了幾個音,但是較低音的地方,她有把握的多了,不知不覺,慢慢的往他的方向靠了過去,此時年輕人已經起身,放開了雙手,來到她的另一邊。
於是稚嫩的手指注入蒼老的靈魂,而蒼老的靈魂,他已經換了羽,小女孩終於把雙手擺在琴鍵上,彈出站在他背後時,沉思的種種,年輕人用高音為她助興,一會兒在遠處用單手搖鈴,一會兒又靠近,雙手灑下綿密的絨羽。
他們的旋律終於找到了,飛了起來。
他們很高興,搖擺著身子,不時對看了幾眼,他們成為了一個站,所有下車的旅客,都來到這台老舊的鋼琴前,靜靜的聽他們說話,一大一小的兩個陌生人,送給每個陌生人,最美妙的伴手禮。
yo,brother,我們的世界,往往需要的是旅人,而不是鋼琴師。
我們擅於拿走別人的東西,也習慣被拿走身上的一切,這個規則很奇怪,建立在「沒有人想被拿走自己的東西」的情況上,但是拿到的又不是自己想要的,也許你會說,那就是我想要的呀!
但事實上,那不是你真正想要的,而是你覺得缺少的。
比如說,你真正想要的是,種一朵花,那麼你應該灑播,應該澆水,應該去查詢植物的圖鑑,但是大多數的人,選擇去踩死別人的花,或拔走別人的,當成自己的。
那是因為自己的花也被其他人拔走的關係,所以你覺得是對的。
你想要的是「被缺少的感覺」,所以拿來的花就算已經死了,也無所謂了。
所以旅人的作用,是提供你所有看起來你覺得像是花的東西,你並不知道真正要的是啥,你永遠無法滿足。
真正想要種一朵花,必定是自然的,而且出自於自願。
就像小女孩佔了鋼琴師的琴鍵,或者鋼琴師擅自掀開鋼琴的蓋子,沒有人允許他們這麼做,在眾人聚集的車站大肆撥放旋律。
沒有目的,就是他們的目的,這麼做,並不是為了要得到獎賞,而是「有也不壞」的心,鋼琴不屬於鋼琴師,鋼琴師並不屬於小女孩,這個車站也不屬於每一個旅客,他們都是自由的,只是在這個時候,偶然的相遇,恰巧的聚集,然後他們發生。
而美好旋律的秘密是,他們不會在乎對方誰彈的比較多,誰應該得到主要的旋律,他們明白誰也不屬於誰,誰應該負責什麼樣的工作,應該彈出什麼樣的旋律,誰應該先退讓。
誰應該獲得什麼樣的掌聲,為誕生的歌曲命名。
所以他們就不用咬對方的手指頭。
如果你要追求公平的話,brother,你得想想你要追求什麼。
如果你追求的是一種表情,那得靠掠奪,掠奪那個人的表情,變成和你一樣的表情,搶他多出來的,補滿自己缺少的,被拿走多出來的部分的那個人,就會焦急的去撕碎別人,塞在自己的空洞裡。
如果你追求的是一首歌,那麼就彈奏吧,在心中空出一片地,讓她奔跑,把心變成柔軟的泥,容許他奔跑時留下的腳印。
阿尼瑪拿走了阿尼馬斯的陰莖,裝在自己的頭上。
波西米亞人典當了所有,為咪咪冰冷的手套上溫暖的手套。
你必須知道那是不一樣的事,然後才能得到心中真正想要的花,
tomoy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