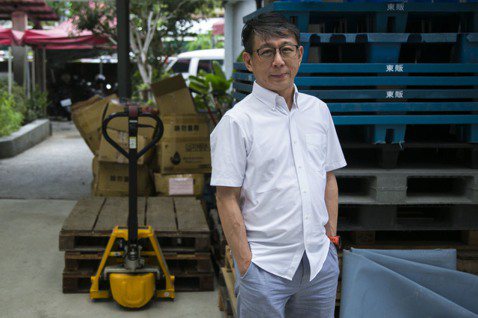【鳴人現場】我將生命交託祢:乩童與濟世文化

在新聞報導以及影視媒體所再現的乩童,往往以一種片段及負面的形象呈現在閱聽眾面前,例如怪力亂神、騙財又騙色,這些對乩童粗野蠻陌與落後迷信的成見,某種程度上來自傳統士大夫的視野,另方面則來自社會型態的轉變(從傳統農村社會進入當代都會生活),而學校也逐漸導入科學化的教育。這些來自階層的、社會型態的以及教育模式的移轉,皆使臺灣的乩童以及乩文化面臨人力承續的斷層。
2016這一年,臺灣的影視文化圈吹起一股臺灣宮廟風,特別是《通靈少女》與《花甲男孩轉大人》劇中更有對靈乩的描繪。民間社會對「此岸」到「彼岸」的溝通需求不減,更可上溯至漢時期,這淵源流長的儀式文化正反映出常民對「神鬼溝通」的殷切需求。
「社會上經常將乩童或是通靈人視為不入流的文化,甚至不認為是文化」,民俗亂彈執行編輯,也是民俗文化研究者溫宗翰指出,儘管如《通靈少女》帶出通靈的討論,但劇中並未呈現有別於通靈以外的另一體系——乩文化——的系統,乩童與靈乩無論在信仰的結構、訓練的過程皆有不同,對社會發展而言也意義也迥然相異。
溫宗翰說,當臺灣社會邁入工商社會且越來越民主化後,靈乩的發展才逐漸蓬勃,當前社會靈乩甚至比乩童還要來的多。靈乩講求的是個人內在的修行,「他們強調每個人身上都有一個『靈』,透過修行讓我們可以與神靈接觸,並藉此獲得更多的靈力」,強調個人的靈驗,溫宗翰認為這與民間信仰走向個人化有關。那靈乩與乩童主要的差異在哪?靈乩講靈語、重視靈異經驗,強調靈動特徵,「例如靈乩會跟你說你現在身後有幾個人跟你這樣」,溫宗翰表示,絕大多數的傳統乩童是看不到所謂「無形」的存在的。
話鋒一轉,溫宗翰有感而發地指出,乩文化在臺灣社會承受了諸多污名,新聞報導如果有乩童,不是騙財,就是約人「雙修」的騙色,卻忽略傳統乩童是地方社會的重要精神寄託與儀式專家,是信仰中心的代表與領導者。他以松柏嶺受天宮為例,指出受天宮除了是臺灣知名的進香中心,也是具傳統歷史的乩童訓練中心,早期臺灣各地公廟還會將乩童送至該地接受訓練,從受天宮出來的乩童數量不勝枚舉,這點也可從受天宮設有乩童專屬的盥洗室可以看出對乩文化的敬重。
|


乩童訓練手冊
「乩童不只是神明的『代言人』,神靈降下來的時候,他就代表神。」其一言一行皆為傳達神明的旨意,不得閃失,因此其訓練的過程就十分重要。要成為一名乩童,溫宗翰指出須由「神明採乩」指定,接著也需經祖先、父母同意,通過後還需進行「坐禁」、「訓乩」,若要獲得公眾信任,還要有各種顯聖神蹟,任一階段未通過,都無法成為合格的乩童,為神明服務,因此傳統乩童不僅是神明的代言人,更是地方社會的重要儀式專家。
以受天宮帝爺公採乩為例,通常是在一段「特定時間」(比如謝平安遶境活動),且在特定區域(轄內六區七村)內。溫宗翰特別指出,神明會在遶境、眾目睽睽下採乩,為的是讓庄裡明白此人將為神明服事,獲得庄裡的認可。
其次,採乩後,神明會附身在老乩童身上到新乩家,詢問祖先與父母的同意,必須連續三個聖杯方能採用此人。最後,等獲祖先與父母的同意後,新乩需進行「坐禁」,在坐禁期間,需進入禁房與外隔絕。禁房內配有一床(過去是草席),一桌(安放神像),其他空空如也,對外窗需以紅紙遮掩,而在坐禁期間需禁食,只能飲水、或是以甘蔗汁充飢,甚至不得大號。此外,禁房內檀香需24小時持續燃燒,以淨化新乩的身心。在渡過這坐禁期間後方能出關,接受老乩童的檢驗、訓練,往後,無論是坐釘床、釘椅或是操持五寶都需自己練習,至此,新乩也才得以稱為一名乩童。
坐禁是任何人想坐就可以坐的嗎?溫宗翰表示不行,如前面所提到的諸多繁複程序,想當一名乩童,甚至是坐禁都有一定的條件,「怎麼可能會有雙修,要修也是筆生跟乩童一起」,溫宗翰說,有時候筆生也會跟乩童一起坐禁,但同樣需擲筊經神明同意。坐禁出來有瘦嗎?現年26歲的受天宮筆生李澍慶說,有,他瘦了三公斤。 人們或許對坐禁期間充滿好奇,像是坐禁時手機也不能帶,可以看書,但對現代人來說不免單調乏味,甚至這樣的「閒到發慌」會讓坐禁前功盡棄。受天宮乩童陳建宇說,在裡面的生活總結下來是「無聊、無聊、無聊」,無事可做便找筆生聊天,當然,只有兩個人,話題不拘,但坐禁就是要讓你放下俗事,靜下心來。李澍慶則分享,曾有乩童在坐禁時「說幹話」,結果半夜遭神明處罰,徹夜雙手騰空筆畫,整晚不得安眠。
|


乩童的濟世文化
乩童的民俗功能最被廣為討論是「醫療」的作用,其所醫治的疾病,往往是具公眾性與展示性的,重要的是在於提供「心靈上的支持力量」,溫宗翰也提及,此可供醫病關係緊張的臺灣當代社會思考。
「現代人即使相信現代醫學,也經常遇到醫病關係緊張的狀態,」溫宗翰說,「許多人生病去看醫生,未必會遵從醫生指示,有時醫生開七天的藥,病人只吃三天,他指出,如果藉助神明的力量,說「帝爺公交代要按時服藥」,你還會不吃嗎?
「當你需要做出人生抉擇時,神明經常是最有信心的選擇」,溫宗翰說,底層民眾因生活經驗傳承,面對重大決定往往交託給神明作主,像是在眾多醫生名單中猶豫不決,但只要神明指派了哪一位醫師,信者便容易死心塌地的相信這位醫師。這看似現代文明與傳統的尷尬,其實另方面來看,也是彼此的互補與互助。
當然乩童的功能不僅在醫療與心靈支持,也在掃蕩妖精、驅逐鬼魅的信仰功能上,提醒我們對生活環境的覺察與尊敬。溫宗翰說,當遶境隊伍到某個車禍熱點進行路祭,整個隊伍停在該路口,乩童一躍而上附身起乩時,這樣的「大陣仗儀式」也會傳遍整個庄頭。在往後庄頭人經過該路口時,都會顯得特別留意、警惕在心,這就是儀式的力量。
此外,乩童的濟世文化還包含社區關懷,溫宗翰回憶起有一回一名黑面元帥的乩身來到一戶男主人剛往生的喪家,安慰喪家年幼的孩童,並交代如果需要協助,請他隨時到宮裡,玄天上帝三兄弟會幫忙他度過難關。這些事例再再呈現濟世文化中關懷鄰里故土的慈悲,也呈現出地方濟世助人的溫暖情誼。
|


乩童的本質是公眾服務的一環
在民間信仰中有種普遍流傳的說法,認為被神明挑上的乩童壽命較短或有生命難關,透過擔任乩童累積功德得以續壽,因此我們常可見到一些老乩童儘管年歲漸大,依然出外為神明服務,因為他們相信一旦退休了,壽命也將盡了。
對乩童陳建宇而言,就有離奇經驗發生在他身上。在他成為乩童前,就曾離奇發生車禍卻大難不死。問道,是騎快車嗎?他說就順順地騎,不知道為什麼總是遇到血光之災,車禍的陰影如影隨形,直到他正式成了乩童,這些情事才不再發生。
問到陳建宇,第一次操持法器「自殘」時會害怕嗎?他說其實當下進入恍惚狀態不會有感覺,而傷口也很快就癒合了,相較於肉體的受傷,令他掛心的反而是「沒把信徒的事情處理好」,就像信徒與神明、神明與乩童、乩童與筆生間,都是彼此相互交託與依存的共生、共存關係,如同人們生活在臺灣這塊土地上,都會與民間信仰間無可避免的產生互動甚至是相互約束。
溫宗翰最後提醒,在當代社會裡,傳統民間信仰不斷地流失,他建議人們盡可能回到地方瞭解地方知識,重新認識地方信仰網絡,乩童與濟世文化其實就在我們的日常生活裡,只是當代的生活讓我們以為它已經離我們遠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