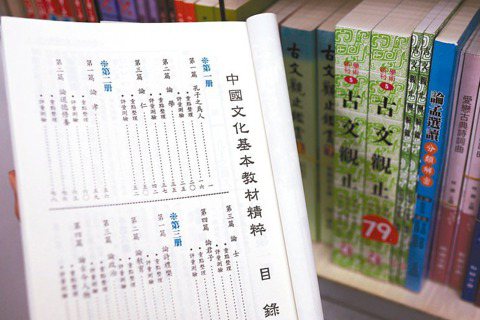回應「批判文言文運動」(上):國文課的文學價值與人文素養

最近,社會上與網路上掀起一股巨大的浪潮,台灣島民長久以來對「國文課」的不滿,一次爆發開來,矛頭首先指向「文言文」,我稱之為「批判文言文運動」。
知名網紅朱家安為此運動開了第一槍。朱家安認為,國文課一直在浪費學生的青春,並提出「文言文應該退出必修課」的主張。接著,小說家朱宥勳則是發文批判那些擁護文言文的國文老師,並主張「設立能力指標,就不必迷信經典」。這幾天,又陸續有作家現身說法,認為大量閱讀文言文無助於寫作,國文老師應該回歸基本面,培養學生的基本語文能力,諸如寫自傳、寫履歷、寫文案以及製作簡報的能力等等。
連日的論戰下,現在網路上的風向已大致底定,主張降低或廢除文言文的呼聲極高,現在站出來為文言文辯護,無論觀點為何,恐怕難以避免地被貼上保守派的標籤,換來網友的一番冷嘲熱諷。但我想,有一些問題確實值得釐清,所以我會將相關議題的脈絡梳理一下,讓問題能夠更清楚的呈現,進而說明吵文白比例實為一個假議題,並簡單回應反對方(特別是朱家安與朱宥勳)的一些論點。
問題的緣起:國文課沒辦法回應時代需求
首先,為什麼偏偏是國文課?「升學主義」與「填鴨式教學」荼毒台灣學子是全面性的,每個科目都應該有僵化、學了也用不到的問題,但為什麼偏偏是國文課被認為最廢,對人生毫無幫助,並引起公憤?
我的理解是,現在是一個所有公共議題都在網路上進行討論的時代,因此,一個閱讀與寫作基礎能力欠佳的人,對社會造成的傷害比起英文、數學不好的人要大太多了。人們往回看,發現國文課跟這些能力最接近,就認為國文課應該要包辦他們覺得最重要的基本語文能力,結果發現國文課本充滿大量文言文,學這些文言文根本就派不上用場,無法回應時代需求。1
針對這一點,我首先要澄清的是:就算今天文言文完全退場,課本全部選白話文,學生的基本語文能力也不見得就會提升。因為「多讀白話文就可以提升基本語文能力」是一個想當然耳的預設,你沒有辦法證明兩者之間的必然關係,就像我們也無法證明學文言文對基本語文能力有幫助一樣。
一般人的邏輯很簡單,我們認為學生不會投籃就應該努力學投籃,表達能力不好就要多讀白話文。但語文能力涉及的是全方位的能力,包含擷取訊息、抓取論點、整理歸納、有邏輯地陳述與表達、該用什麼風格與表情進行溝通等,這涉及的是如何融入對話情境、如何組織思維的問題,不會因為全部改讀白話文,就提升這方面的能力。
因為,在教白話文時,老師會更著重在這篇文章的文學性,以及其中所表達的意義,或情感內涵等等,依然沒時間訓練學生的思考與表達能力;而且考試也有可能繼續考注釋與修辭,或是語意填空及文句排列等等沒意義的題目。就算引進朱宥勳所謂的文本分析與應用技巧,在升學主義的摧殘下,難保不會變成僵化的考試題目,導致學生必須背誦「朱宥勳提出的分析小說的原則是哪五個」,因而失去學習的意義,使學生更憎恨國文課。因此,「白話文取代文言文」對國文教育而言,完全是個治標不治本的藥方——從這個脈絡來看,文白比例是個假議題。

大家真正需要學的,是「應用文」
再者,大家期待國文課應該要包辦的語文能力,若是為了寫自傳、寫履歷、寫文案、討論公共議題等等,這方面的需求應該是屬於「應用文」的範圍才對。「應用文」與「文學」是有交集但基本上完全不同的兩個專業,如果大家真的想精進這方面的能力,應該要呼籲國文課綱減少「文學」的比例、增加「應用文」的比例才對,吵文白比例根本是焦點錯誤。
我們可以歸結國文課很廢的原因是:目前國文課本中的「應用文」仍然停留在老舊的書信、對聯等內容,已經一點都無法「應用」了,國文課就是廢在這裡,大家要攻擊的是這個部分,並爭取加入「寫自傳」、「寫履歷」、「寫文案」等教學內容才對。
在朱家安的構想中,必修的國文課應該以教導學生「討論議題(溝通)」的語文能力為核心,所以國文課本只需選錄條理清晰、文意明白曉暢的白話文即可,完全不必選文言文,因為文言文是無法清楚表意的文體。2
值得注意的是,朱家安徹底搞錯了「文學作品」與「應用文範本」兩個概念,「文學作品」是具有獨立價值的,它無法被取代;「應用文範本」則只是為了學會某個技巧、或討論某個議題而存在的,只要有更好的範本,就隨時可以取代。如果讓朱家安來編國文課本,那我們的國文課本就會變成「應用文範本」,毫無文學價值。說得更清楚一些,朱家安希望從必修課程中拿走的,其實不只是「文言文」,而是「文學」本身,而這個做法是我們國文老師無論如何不能同意的,因為這樣一來,國文課就再也不是國文課了。
能力指標很重要,但人文素養更重要
還有一個主張「文言文可被白話文取代」的論點,是朱宥勳提出來的。他在〈找到能力指標,就不必迷信經典〉一文中認為,只要確定了「能力指標」,就不必迷信經典了,因為白話文也可以培養學生學會所有該具備的能力:
更徹底一點說,當我們確定了能力指標,就不再需要迷信「經典」了。因為任何能夠幫助我們教會能力指標的文本,都是合格的課本範文。從而,我們就可以在這個及格線上,納入更多的考量。
我們還可以參考朱宥勳所提的實際例子:
比如說,我們可能認為「象徵手法」是一項重要的文學知識,所以把它視為能力指標,然後開始去找:我們應該要用什麼文本來教會學生「象徵手法」——是不是要用陳映真的小說〈麵攤〉呢?還是魯迅的小說〈藥〉呢?
國文課本在編排上,確實可以採納朱宥勳的建議,增強「能力指標」的部分,讓每一課的學習目標變得更清楚,這樣會更有助於教學(實際上也已經這麼做了)。然而,若按照他的構想,以各種該學的文學技巧為綱領,下去選擇文章當「範本」,這又是另一回事了。這會使國文課本成為「作文技巧學習大全」,國文課也會被窄化成「寫作練習課」。
當然,朱宥勳還是可以透過陳映真的〈麵攤〉或魯迅的〈藥〉來談文學之美或陶冶學生性情,但在以能力指標為導向的課程設計中,所有與「人文素養」有關的要素都將退居次位——畢竟你讀〈藥〉就只是為了學「象徵手法」,至於其中蘊含的「魯迅對時代的批判與對革命志士的同情」,教師雖然也可以討論,但就不是那麼主要的部分、甚至可有可無,隨時可被其他文章取代。朱宥勳的做法,其實顛倒了「文學教育」的邏輯——「文學」畢竟是「人學」,「人文素養」應該作為最主要的選文導向,而不是「文學技巧」或「文學知識」。(但為了因應時代需求,最好的做法,就是我們建議教學現場的老師在教學時,可以多加強文學技巧的分析,並建制一套完整的教學配套供教師取用。)
討論到這邊,我們可以看到,朱宥勳跟朱家安瓦解文言文價值的手法就是:將國文課本的編排,從以「經典」為導向,扭轉為以「範本」為導向。畢竟,只要將國文課本視為「範本」,就再也沒有什麼文章有非選不可的理由,因為一切選文都是以「目的」為導向,愈能夠有效達到目的的範本,就愈是值得選錄。(所以二朱都很強調「效果」這個關鍵字。)而往往符合他們設立的「學習目的」的,都不是文言文,而是白話文。
他們的主張能夠得到大眾的支持,是因為把文學給工具化,所以能夠符合時代的需求,引發年輕人學習的興趣,但我們這些第一線的教育工作者認為,教育可以包含這個部分,但就整體取向而言,不應該如此短視近利。

- 這個觀點受到李學明的啟發,特此感謝。
- 朱家安的論點散見於他的文章、臉書貼文及回覆中,無法一一列舉。可參考他在〈高中國文必修學分應砍半〉一文中的說法:「去修習以溝通能力為核心的國文課程,是學生的義務」、「在現況下,我們的國文必修課程,並不是以溝通能力為核心的國文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