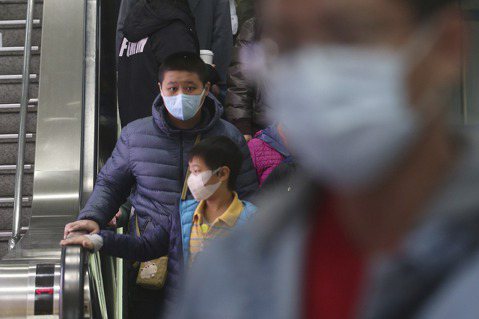正視口罩,放下口罩:如何面對新型冠狀病毒的持續戰?

這兩個月來,台灣新聞幾乎被來自武漢、蔓延中國、播散各地的2019年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以下稱新型冠狀病毒)報導所占據。這個病毒最初被視為SARS的翻版,只是報出時間點提前,讓大家似乎看到病毒「ground zero」的華南海鮮批發市場,追出它早期的爆發途徑。
隨著疫情進展,這個病毒走出自己的傳染模式。以亞洲來說,推手有「地表最大人群移動」的中國春運,有頻繁的國際經貿,甚至觀光郵輪也成為巡行的疫病溫床,提醒各國「檢疫」(quarantine)的原意,正是透過對人群貨物的管控,達到防堵疾病的效果。
檢疫與隔離雖然古老,但絕對有效。當時《美國醫學會雜誌》(JAMA)分析1918年大流感,指出要徹底阻絕流感就要全面停止活動,不跟外界接觸。但如此極端的社會控制會導致商品流通停滯與損失,是敵暗我明狀況下不得已的措施。
以中國來說,不但國際航班陸續停飛,政府更祭出SARS時期曾提出,但未付諸實行的「封城」手段;從武漢到湖北,從二級都市到一級都市,追趕人民在春節歡聚之後,在疾病陰影下恐懼竄流的腳步。這個中央集權的舉措雷厲風行,但效果有限。相較於言論的管控,監視系統與科技對掌握盲從的人流與病毒似乎幫助不大。

防疫作為一種社會控制
到目前為止,台灣在這場防疫戰中成績斐然。當局從SARS防治汲取教訓,在疫情與防疫政策(例如自主管理、居家檢疫與居家隔離)的傳達即時到位,也沒有群聚感染,用不著封城。
與此同時,剪不斷理還亂的兩岸關係與國內政情,也讓這次防疫與SARS相同,糾結在政治考量與防疫專業的權衡裡。政府不但要應變疫情,還得回應各界對參與世衛組織的期待、被無端孤立的憤怒,與澄清社群媒體與評論節目的誤導。如此壓力下,衛生官員的表現有如當年的陳建仁署長與李明亮教授,令人印象深刻。
在此不重複已經討論許久的輿論議題。這裡我想回到公衛,指出防疫是以控制傳染為目的的社會控制,前提是對風險的精準衡量。面對狀況不明的疫情時,社會介入(比方說檢疫)無法避免,也要有付出代價的準備。
本文要談的口罩與「口罩之亂」是最好的例子。病從口入,避免口腔暴露瘴氣古已有之。但戴上口罩後活動並不容易,口罩愈嚴密呼吸愈困難。在那篇1918年大流感的分析裡點出這樣的兩難:要患病者戴上口罩固然辛苦,但對防止流感傳布有幫忙,只是不清楚能幫多少。
研究者大致認為,戴口罩對直接接觸病人者有保護效果,但不確定對其他人是否有用。這樣說,口罩是自我風險衡量的「檢疫」機制,查得鬆沒效果,查得嚴撐不久。口罩不是問題,問題是要用怎樣的口罩,在什麼時機佩戴,防疫才不會淪為紙上談兵。

公共衛生的弔詭
但就像飯前洗手、飯後漱口一樣,這類健康操作說來容易,但往往只停留在學校教育,大多數人被動遵守,畢業後就束之高閣,能正確做到就已經不容易,更不用說要能內化成習慣。集體公衛活動也是如此。
一些朋友或許記得1950與1960年代夏季一起打掃鄰里,撲蚊滅蟑捉老鼠的盛況,但現在這樣的大型演練十分罕見。即使是登革熱這樣年復一年的非地區流行病(non-endemic disease),只要撲殺病媒蚊就有控制效果,衛生查核也從不放鬆,但依舊無法阻絕,每年都有上萬病例,造成數百人死亡。
這是公共衛生的弔詭:有別於衛生不佳地區人人自危,發展出許多自保手段,衛生基礎建設的進步,反而讓大家放下戒心,鬆懈身體,將防疫全部交給醫療,丟給政府。只有SARS或者是H1N1這樣的大流行來臨時大家才會打回原形,體會醫藥固然日新月異,但一百年來防疫的社會手段沒有太多創新,不外乎隔離病患,杜絕接觸,搶時間發展疫苗,遠遠跟不上病毒突變與人群移動的速度。
這是「口罩之亂」的社會根源。口罩並非先進科技,使用也行之有年,但還是有很多人沒有養成適當的佩戴習慣,不但醫療用與非醫療用口罩分不清楚,使用時機也懵懵懂懂。
於是,戴口罩最有效益的病患,往往因為圖呼吸方便而不戴口罩;戴口罩者也不見得是基於防疫,而是其他的風險顧慮(比方說空氣汙染)。只有透過一次次的傳染病威脅,我們才在「勇敢不戴口罩」與「無時不離口罩」之間,蹣跚地學習如何與病毒相處。以下點出三點觀察。

口罩在戴與不戴之間
首先是使用場合。流感病毒到處散布,但並非處處一樣危險。1918大流感的經驗點出「直接接觸」是戴口罩最有效益的場合,其他狀況因為感染風險較低,效益見仁見智。但這樣的思路在SARS期間並未落實。
以醫院來說,最該戴口罩的場合包括候診區與診間,佩戴對象除醫護人員外還有就診者或抵抗力較弱者。但由於疫情不明,許多平時不戴口罩的人高估自己的耐受力,以為可以長時間佩戴口罩,結果反而不需戴口罩時戴口罩,但真的需要的場合反而戴不住,無端暴露在高風險下。
其次是「口罩中心」的思維。新型冠狀病毒感染影響呼吸系統,防疫以戴口罩、勤洗手與酒精消毒為主,實際操作上大家卻以口罩為指標,似乎規格愈高愈好。
以N95口罩來說,它的防堵效果當然好,但配戴者很難呼吸,不利長時間配戴。此外,N95口罩某種程度造成類似17世紀「疫病醫師」(plague doctor)的社會效果。當時醫師身穿長袍大帽,手戴手套,頭上配戴怪異的鳥喙型口罩,全副武裝前往檢視,造成當地恐懼,N95或者高規格防護面具也會產生類似效應。
而口罩中心的迷思是忘記口罩只是工具,重點是如何配合防疫。許多買上N95等級口罩的人不清楚如何正確使用,或因為戴不習慣而放棄,結果防疫效果比佩戴普通非醫療用口罩的還糟。

此外,就跟有藥吃就好像可以不用在意健康一樣,口罩往往讓人忘記其他衛生習慣的重要。許多人將口罩的清潔面(通常是內面)隨意與污染的物品或表面接觸,或者是抓臉摳鼻,將手任意伸入口罩中或挪動口罩,都可能讓它的防疫效果破功。
從口罩中心思維延伸出來的,是對防疫物資的錯誤認知與過度期待。這次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民眾學到教訓,不再搶購N95口罩,但對象改成外科用口罩(surgical mask),變本加厲,助長「口罩代表一切」的論述。
與非醫療口罩(比方活性碳口罩或布口罩)不同,醫藥管理上醫用或外科口罩是第一級的醫療器材(與棉花棒同等級),或者是第二級醫療器材(與隱形眼鏡同等級),其生產與販售通路有特定規範。這是衛生當局第一時間便出手徵集,介入分配的原因。
這裡不討論實名限購政策,僅點出兩個與搶購相關的問題:
第一,許多人將口罩當作一般物資,動輒強調價格波動與供給短缺。但如前所述,口罩是醫療器材,本來就不完全由市場決定,更何況是防疫的非常時期。
第二,許多人高估外科口罩的防護力,忽略它只是防疫的一部分,天天更換固然理想,但不是沒它防疫就無法進行。事實上,作為抗菌手術(antiseptic surgery)一環,外科口罩主要是防止醫療人員的飛沫污染檯面。手術既然不是「無菌」(aseptic),因此口罩也沒有阻擋所有病原,而是簡單輕薄,能夠長久佩戴。
任何醫療資源都有限而可貴,口罩也不例外。從這樣的概念去想,當局的邏輯不難理解。以流感疫苗來說,風險最大的醫療人員優先分配,其次是可能的感染者,如老年人與幼童,再有剩餘才開放其他風險較低者施打。如果有人急著想打疫苗,則需要自費(診療費加藥費並不便宜),以達到資源的最佳使用。
如果有以上認知,便不至於在「口罩之亂」中人云亦云。這幾天看到用鄰里系統免費發放口罩,或者無限制以平價提供口罩的主張,甚或是排隊買口罩時連個非醫療口罩都不戴,跟前後的人近距離談笑。提出者的出發點或許良善,交換意見也是人之常情,但從專業角度來看,這些人可能需要再上一堂公衛課,重新思考防疫的社會意義與自身的責任。

看不到風,但看到被風吹動的樹葉
確實,防疫的基礎是醫療,但更是社會。我們與新型冠狀病毒的遭遇戰打得漂亮,但捫心自問,我們是否就此準備好接下去的持續戰?
我不禁想起前不久,H1N1流感防疫指揮官郭旭崧校長的「驚人之語」,指出戴口罩不必無限上綱,應根據場合決定是否戴口罩,並提出百萬慰問金給遵照這個原則但依然染病的師生。
郭校長的呼籲固然是公衛的老生常談,但此時提出有兩個意義。
首先,陽明大學以生醫起家,找出病原、開發篩檢技術、疫苗與藥物自然當仁不讓,但在各界往醫療傾斜時,郭校長讓我們看到「社會改造」才是防疫的正本清源之道。
第二,面對這波疫情,公共衛生促進會提出社區防疫的重要,但人人以鄰為壑,不易推行。陽明大學有面對高染病風險的見實習生,鼓勵同在校園的師生將用不上的口罩捐給他們,是專業判斷與生活共同體的體現。
最後提這場防疫戰的可能後續。第一,無症狀感染者的出現,代表用體溫與臨床症狀來掌握風險的方式需要重新檢討。第二,大規模感染的可能。目前所知新型病毒傳染性高,致死率則否。如此,在國際交流頻繁的今天,我們是否還能將病毒繼續阻絕境外,不無疑問。
當然,疾病管制署對疫情持續追蹤,或許幾個月後會如同H1N1流感一樣,在台灣發現無法確定感染源,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案例。但我們要的不是無謂的恐慌,而是提早養成正確習慣,減少皮膚的暴露與不做不需要的肢體接觸,勤洗手與酒精消毒,而不是戴口罩就算。對此,任何沒有具體論據的風險評估,用似是而非的方式撥弄防疫方向與力道者,都需要正視與排除。
而疫情如果遲遲未見起色,終究會遇到疫苗的研發與施打。如前所說,檢疫犧牲社會活動,圖的是搶出時間,作出疫苗,全面施打來提升群體免疫力。但相較於口罩,疫苗的管制規格更高,測試手續更加複雜,非一時兩刻可以趕出。
更重要的是,社會長久以來對疫苗安全性多所疑慮,其中訊息真真假假不輸給現在的口罩。因此政府是否要全力投入,預期民眾在推出後會如口罩一樣爭先恐後地搶打,都值得思量。SARS當年橫掃全台,但最終沒有推出疫苗,H1N1當年搶推疫苗,但最終並不普及,都是前車之鑑。
醫學人文先驅黃崑巖教授生前將傳染病比喻成風:我們看不到風,但看到被風吹動的樹葉。黃教授的叡見也適用在這次疫情。
我們雖然沒有辦法看到病毒,但卻從對它的反應,各種徬徨、疑惑,以至於誤解與偏見中看到騷動不安的人群與社會。在疾疫年代我們需要先進醫療,更需要傳統公衛裝備自己,平心靜氣,度過難關,以此與大家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