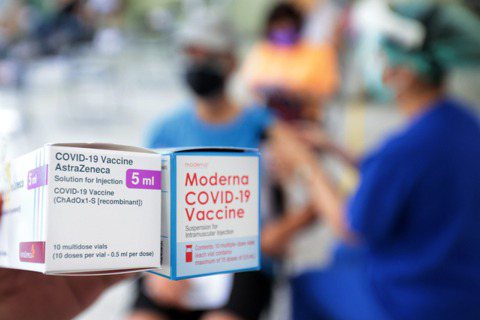葉明叡/抗疫共同體:為什麼大部分台灣人願意配合戴口罩?

疫情自上週開始全面升級,防疫作為進入新的階段。有關一般人防疫的做法,許多專家已經分享了有用的建議。這篇文章想談一個在這波COVID-19大流行之中的大哉問:東亞社會相較於「歐美」社會,似乎更不在意自己的自由受到限制,而願意配合政府的防疫規定,特別是帶口罩政策,原因究竟是什麼?是否是因東亞有特別的文化所致?這對於接下的防疫能有何啟示?
口罩的健康防護意象
請大家回想過去在2003年遭遇SARS大流行時的經驗,以及近年來對於空氣汙染防治的經驗。先簡要說一下SARS,當年台灣是少數幾個遭遇重創的國家,有社區感染、也有院內感染,當時台灣的傳染病防治機制還不是很完備,付出的生命和健康代價極大。事後,整個傳染病政策與法律基礎,以及衛生部門之間的權責區分,做了全面的檢討,此為部分台灣政府能迅速應對COVID-19的原因。
由於SARS主要也是透過飛沫與接觸傳染(傳染機制基本上與這次COVID-19差不多),因此就建立起戴「口罩—防疫」間的關聯性(當時也有相關戴口罩規定,只是不若COVID-19時這麼強硬),我想那次的經驗很重要,傳染病防治也是有學習曲線的。其實不只戴口罩,其他個人防護措施,像是要勤洗手,回家後要將外出衣物與物品,與清潔的家裡內部區開來放置等應對飛沫與接觸類型傳染病的個人行為,也都是有相同效果,此次COVID-19,人們也很快地的自主採取了這些措施。
空氣汙染,則是近十年受到重視的民生議題,空汙造成很多過敏、肺部疾病,也是許多慢性疾病的致病因子。空汙的來源,除了發電方式的爭論,許多空汙來源是源自台灣外部的汙染源,例如隨著鋒面、氣團從國外飄散至台灣的汙染物,這些不是本國政府所能掌控的,人們只好自己想辦法,戴口罩就是一個很直接的個人防護設備,成本低、易取得、易操作、又有效。
因此雖然個人防護設備在公衛原理上通常是最後不得已才考慮的作法(其他如移除、置換汙染源、或在製程中替換汙染性較小的物質,這兩者是較個人防護設備為優的做法),戴口罩也成為民眾自保、對抗空汙的方式。戴口罩的微小不方便或不舒服,可能也就被視為一種日常習慣,而不至於感到特別負擔。
這兩個經驗,都讓「戴口罩行為」和「個人健康的維持、保護」構成直接的因果關係,如此,當COVID-19興起時,甚至不待政府主動強制要求,人們就開始自主採取戴口罩為基本的自我健康保護策略了。

團結抗疫的社會氛圍
如果大家還有印象,台灣的口罩爭論在流行初期,人們主要不是在反對政府要求戴口罩的規定,反而是要求政府應該要好好規劃口罩的配給和流通,因為一時之間到處口罩都被搶購一空了(當時是剛才過完農曆新年後),也才有後來的口罩實名制、兩週一人可買幾片等配給制度。政府也緊急徵召民間工廠和機具來生產和流通口罩等,而這些政策機制都是經過立法授權而建立的,並非專為COVID-19而特別設計,如前述這是SARS的遺產,才讓政府可以快速動員,又不會流於權力的專斷行使。
或許也是因為這樣民主立法的基礎,人們反對的聲音也較小,或比較不認為政府過度限制人民自由(另一方面,在政府收集個人的數位足跡、強制實施的入境隔離管制等方面,比起口罩就受到較多批評與質疑)。
總之,戴口罩除了個人的自我健康保護行為以外,社會中可能也會形成一種互相提醒督促的氛圍,讓戴口罩成為在疫情中生活的一種暫時的、新的社會互動模式(social norm)。從個人的健康,到彼此的健康,到共同體的健康,可能有形成了這樣的公共關懷。我會說,這是一種公共衛生的「公共性」(the “public” of public health)的顯現,它或許平常就存在,但不易察覺,大流行等這種極端時刻,才會被召喚到人們面前吧,我希望我有信心能這樣說。

文化本質VS. 健康實作
至於,這是不是已經是一種「文化」了?我想應該還有很多辯論空間。戴口罩行為不見得就真的會構成某種文化,或必然扣連到某種文化的底蘊才會想戴口罩,甚至說,怎樣才能構成「文化」、又是誰(一個城市?民族?國家?區域?文明?)的文化等爭論。
某些論者會以為,東亞(或台灣)社會是因為(儒教或其他)文化因素上較為順服政府權威,所以人們才會戴口罩,我對此解釋感到相當不以為然,缺乏客觀基礎。從台灣經驗我們已經看到,人們並不是因為順從於政府要求才戴口罩,剛好相反,人們是在面對新興疫情時,主動去尋求、採取健康保護的措施,戴口罩正是其中一個人們易於取得、便宜又有效的措施。撇開以上關於文化的爭論姑且不論,從台灣的案例或許至少可以說,戴口罩防疫是一種基於實用經驗累積而生的健康實作(practice)。
對於歐美國家而言,或許COVID-19對歐美的人們,就像當年SARS對台灣的效應一樣,因為嚴重傳染病大流行已經許久未曾發生,過去世代曾有過的經驗和健康實作已經為人們逐漸淡忘,到了COVID-19時才又被迫重新建立經驗,因此在事過境遷之後(我們都希望此日快點到來),人們會習得應對傳染病大流行的經驗,採取有效的個人防護裝置,在飛沫傳染類型的傳染病而言也就是戴口罩,也有機會成為人們內建的預設知識,在下次遭遇到類似情形時,快速活化起來,成為防疫的個人作為。
除了問為什麼想戴口罩,也可以從「為什麼不想戴」的觀點來切入。有些論者會提出說,這是因為「西方」或「歐美」較為個人主義的文化價值。
我沒辦法說這個解釋絕對是錯的,就跟我也沒辦法說儒教文化對人們的防疫行為絕對沒有影響一樣,這些都是實證問題,也是程度問題,一個社會中,有多少比例的個人主義信仰者?其中又有多少願為了「不戴口罩的自由」而犧牲自己或他人的健康,到什麼程度?這每一個環節都有許多沒有證據的論斷,不然同樣我也可以說,美國也是有共和主義的傳統,社群的價值、共和的健康,不見得比較不重要,但信仰著這傳統的人,比例又是多少?我也可以說,個人主義是基於對於彼此權利的肯認與尊重,即使不認同政府要求強制戴口罩,總也可以自己主動去採取自保或保護尊重他人的戴口罩作為吧?
歷史與文化因素,在某種意義上大到沒法操作,我們當然可以做出很多洞察和猜測,不過我傾向還是回到社會整體應對傳染病大流行的經驗來談。這些經驗產生的預設知識與健康實作是重要的,讓這些知識有系統性的傳遞下來,讓實作或實現實作的條件成為制度的一部分,可能是從公衛角度而言能做的事情。

問題不在政治動員
除了文化,另一個很重要的關鍵點是,應對COVID-19戴口罩與否這件事,在台灣尚未太過度被政治化,成為與支持政黨綁定的立場,進而形成對立的議題。
當然,在台灣COVID-19防疫作為的某些層面,還是有被政治化而產生對立社會意見的,例如去年中,是否進行社區普篩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台灣的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並不打算實施普篩策略,但部分學者以及主要的在野黨則強烈主張應該實施普篩),此議題近日隨疫情升級又再起,但在戴口罩這層面並沒有此對立。
就此而言,不論反對或支持戴口罩者,都不會特別被政治動員,雙方對於科學或衛生專業建議都可較平常看待,也可發揮原有的防疫經驗知識(如前面所提及SARS和空汙的學習經驗),而不會特別相信(並幫助傳播、再製)許多陰謀論。因此就沒有被政治化的結果而言,人們的原有立場就是傾向會戴口罩,或是說,沒有特別的政治動員因素,來動員讓人們不想去戴口罩。
在某些歐美國家,戴口罩行為被連結到特定的政治立場、價值和意向,那麼「不戴口罩」就作為一種政治態度的展現,這種政治動員就會實質造成某些人不想戴口罩了(或是放大戴口罩的不舒適、傾向嚴厲檢視戴口罩可能對自由造成的限制、放大對醫療衛生專業或科學研究的不信任、以及其他更多的政府陰謀等)。
最後必須強調,前面提出的這些解釋也僅是片面的觀察,一種基於經驗的可能推想,嚴格說起來,都還需要進一步實證研究來弄清楚,這也是公衛研究亟需要做的事。

保衛健康的共同體
傳染病大流行必然受到歷史、文化和政治的影響,防疫專業科學知識沒法幫大家做出決定說,怎樣一定比較好,說「戴口罩防疫」一定比「絕對的選擇不戴口罩的自由」重要。防疫知識只能說,在COVID-19大流行中進行必要的人類接觸活動時,除了保持社交距離以外,戴口罩是具有防疫效果的重要作為。
最終的決定仍會是人們的決定,是政治的、也是倫理的決定。而傳染病大流行時代的公衛倫理會要求我們,並避免有心人士就疫情議題進行政治動員,記起過往應對傳染病的經驗,繼續保持我們的健康實作、團結抗疫的社會氛圍,把口罩戴好、搭配其他防疫措施,與COVID-19奮戰,保衛共同體的健康。
(原文授權轉載自「思想坦克Voicettank」,原標題:〈抗疫共同體:戴口罩的健康實作〉)

|延伸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