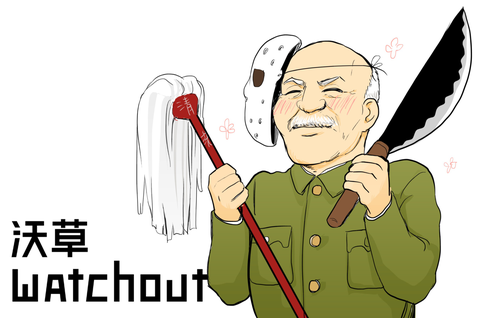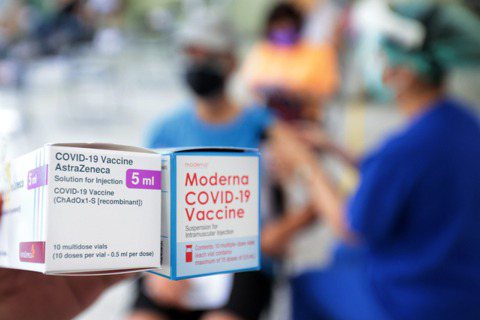謝世民/轉型正義是否「正義」,該由什麼原則來判斷?

轉型正義是台灣各界自民主化之後就持續關注的政治議題,但由於大家對於這個議題的認識有限,政治利益計算又牽涉其中,因此,我們對於國家應該如何處理「威權時期政府系統性侵害人權、奪取國家資源」事宜,一直爭論不休,進展有限。這個局面直到民進黨完全執政之後,才有了巨大的改變。
民進黨在2016年初的立委和總統選舉中,大獲全勝。立法院在國民黨失去優勢的情況下,陸續通過了《不當黨產處理條例》以及《促進轉型正義條例》,行政院並分別於2016年8月、2018年5月,成立了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和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由前者負責「進行政黨、附隨組織及其受託管理人不當取得財產之調查、返還、追徵、權利回復」,後者負責規劃、推動「開放政治檔案」、「清除威權象徵及保存不義遺址」、「平復司法不法、還原歷史真相並促進社會和解」、「處理不當黨產」、「其他轉型正義事項」。不過,這些重大變革並未受到國民黨其及支持者的認同,爭論仍然不斷。
在這場勢必還會持續的爭論中,有一個基本的政治道德問題,我們不能忽視,那就是:國家處理「威權時期政府系統性侵害人權、奪取國家資源」之制度和作為,是否正義,應該依據什麼原則來判斷?
或者,更簡單地說,什麼是我們最有理由接受的轉型正義原則?
這個問題不是在問:我們目前用來處理威權時期諸多不義事宜的制度和作為是否違憲?憲政問題很重要,但除了憲政問題之外,我們還有政治道德層次的正義問題:我們目前用來處理威權時期諸多不義事宜的制度和作為,即使不違憲,是否正義?如何判定是否正義?以我們熟悉的分配正義問題來類比一下,或許有助於我們理解這個問題的基本性。
如何判定是否正義?
要評價社會制度,我們必然訴諸價值,其中最特別的價值是正義。正義的特別之處在於:正義不待我們的選擇就對我們具有不變的規範性,或者說,正義給了我們不可放棄的理由,因為我們無法說「正義不是我們選擇去追求的目標,因此,正義對我們沒有約束力」。相對而言,其他價值的規範性則會隨著我們的選擇而有變化,在不涉及正義的所謂「價值衝突」情境中,我們可以選擇某些價值作為目的來追求,放棄另外一些與之衝突的價值。
當然,在衝突情境中去放棄這些價值,我們會感到遺憾,但是,這些被放棄的價值,一旦被放棄了,對我們就不再具有規範力。對照而言,不論我們選擇什麼價值作為我們的目的,我們在追求這些價值時都必須謹守正義之要求(或不能背離正義之要求)。
我們對「正義」的這種理解,羅爾斯在他的《正義論》用了一句很簡潔的口號來概括:
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德目。
對羅爾斯而言,就內容而言,正義不是來自於神意,也不是一種獨立的而且僅僅依賴理性直觀就可以去發現的道德秩序,而是人彼此在公平情境下的協定。
眾所周知,羅爾斯《正義論》關切的是「分配正義問題」,他倡議我們應該依據「正義二原則」及其「優先規則」去判定一個社會的分配制度(或他所謂的「社會基本結構」)是否正義。
根據羅爾斯的正義論,社會基本結構是正義的,僅當(1)每個人在其中都享有一套適當的、彼此相容又相等的基本自由和權利體系;(2)它所允許的社會經濟不平等,(a)在滿足了所謂的「公平式機會平等原則」之前提下,依附在對所有人開放的職務和工作之中;(b)並對受益最小者最有利;在適用上,(1)優先於(2a),(2a)優先於(2b)。
羅爾斯主張,上述這兩項原則(其及優先規則)是憲政民主社會最有理由去接受的分配正義原則。對羅爾斯而言,一個政治社會的分配制度,即使沒有違反自己的憲法,但若違反了上述的原則,那它就是不義的,而且違反的程度越嚴重,就越不義。
以羅爾斯的分配正義原則為參考點,我們要問的是:什麼是我們最有理由接受的轉型正義原則?國家處理「威權時期政府系統性侵害人權、奪取國家資源」之制度和作為,是否正義,應該依據什麼原則來判斷?
針對這個問題,當代法政哲學家Colleen Murphy在她2017年出版的重要著作The Conceptual Foundations of Transitional Justice中,為我們提出相當具有啟發性的答案。

轉型正義是正義的獨立面向
根據Murphy,轉型正義是一種獨特的正義。轉型正義不是分配正義、不是補償正義、不是應報正義:分配正義原則、補償正義原則、應報正義原則,或其組合,並不是我們去判斷「國家處理威權時期諸多不義事宜的制度和作為是否正義?」之恰當標準。
轉型正義的正義,不僅具有不可化約性,而且也不與其他種類的正義和我們認為重要的其他價值(發展、和平、和諧、民主)彼此妥協之後的一種價值。換言之,轉型正義是正義(諸多面向中)的一個獨立面向。
對Murphy而言,國家處理威權時期諸多不義事宜的制度和作為,是否正義(或在多大程度是正義的),取決於這些制度和作為是否有助於(或在多大程度上有助於)社會轉型。
雖然這些制度和作為必須以適當方式去回應受害者的主張和訴求,以及追究加害者的道德責任,但不必然是以「補償正義」和「應報正義」之名來進行,也不是以犧牲「補償正義」和「應報正義」來進行,而是著眼於「社會轉型」之促進。
她強調,正義不是僵化的價值,而是有彈性、對脈絡「敏感」的價值,就「轉型中的社會」這個脈絡而言,追求正義不是在追求補償正義,也不是追求應報正義,更不是在追求分配正義。
Murphy所謂的「社會轉型」,指的是公民之間關係正常化的轉型,公民與國家之間關係正常化的轉型。Murphy的這個概念與她對於「轉型正義」的適用範圍有關。
對她而言,「轉型中的社會」具有幾個特徵,這些特徵構成了她所謂的「轉型正義之情境」(the circumstances of transitional justice):
- 公民與政府官員之間存在着普遍性的、結構性的不平等互動條件。
- 人權侵犯被常態化,已經成為一般人生活中必須時時面對的事實。
- 對一個政治共同體是否可以存活下來,有極度的不確定感。
- 國家過去在各種犯行中常常扮演了某種角色,人民對於是否要服從權威相當遲疑。
在Murphy的理論中,這樣的社會,是「轉型正義」(作為一種特殊的正義)之適用對象。因此,嚴格而言,她的理論並不適用於台灣,不過,她的分析架構仍然有相當參考價值,有助於我們去回答:對台灣這樣的社會而言,國家處理「威權時期政府系統性侵害人權、奪取國家資源」之制度和作為,是否正義,應該依據什麼原則來判斷?
(原文授權轉載自「思想坦克Voicettank」,原標題:〈如何理解「轉型正義」?〉)

- 文:謝世民,政治哲學工作者,相信抽象問題與具體問題同樣重要,認為具體問題,甚至實踐的策略和變革的方案,要想得透徹,一定會觸及有待釐清的抽象概念和價值,也同意羅爾斯的觀察:沒有人去思考抽象而困難哲學問題的社會,是一個殘缺不全的社會。
- 更多思想坦克Voicettank:Web|FB|Twitter
|延伸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