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柏翰/冷戰再起?國際法規範真空的間諜活動

最近在歐洲鬧得沸沸湯湯、不可開交的新聞,是前俄國特工史克‧里帕(Sergei Skripal)中毒案所導致的英俄外交危機,到底發生了什麼事?里帕早年是俄羅斯聯邦軍上校,後來成為雙面間諜為英國服務,而遭俄國依間諜罪和叛國罪判處13年有期徒刑。2010年,美俄達成交換被捕間諜協議後獲釋,里帕在英國獲得庇護。
今(2018)年3月4日時,里帕和他女兒被發現遭神經毒素謀害,倒在英格蘭索爾茲伯里(Salisbury)一處購物中心的長椅上不省人事。英國政府表示,從他們身上採到的物質是俄羅斯「大量儲存」的神經毒劑諾維喬克(Novichok),因此俄羅斯「極有可能」是這次的襲擊謀殺事件的幕後主使。
在英俄雙方劍拔弩張地控訴對方「違反國際法」的情況下,本文想討論的是,該起「前情報人員毒殺案」和「驅逐外交官」到底涉及了哪些國際法問題?又,整起事件發展迄今都未有國家討論間諜與情報活動的法律問題,突顯了一個各國共同接受的事實——國際社會並不想真的全面禁絕間諜行動。
安理會緊急會議上,英俄雙方代表各執一詞
這起「前情報人員毒殺案」已經演變為西方與俄國之間的外交戰,不僅在媒體和聯合國安理會的緊急會議上互相指控,更開始大規模驅逐彼此的外交人員。根據BBC報導,已有26個國家支持英國,目前西方諸國共驅逐了143名俄羅斯外交人員。當然,現在這個時候,來自各國的各種陰謀論也甚囂塵上。
事件發生後,安理會應英國要求召開了緊急會議,場上雙方各執一詞,都主張對方違反《聯合國憲章》第2條中關於「主權平等」和「政治獨立」等規定。其中備受關注且爭議的點在於「是否真涉及化學武器的使用」;若是,「是哪一國製造、擁有,並容許使用它」,但目前尚未有任何證據被公開。
英方認為,使用與俄國脫不了干係的諾維喬克神經毒劑已經構成了「非法使用武力」,而要求依1993年生效的《禁止化學武器公約》(英文簡稱CWC)中的相關規定啟動調查。在批准後,該公約已於1997年12月對俄國生效,所以若俄國真要為暗殺里帕負責,那它就真的違反了相關的條約義務。

俄方的說詞是,不僅英方指控毫無根據,英國也拒絕俄國提出的種種要求,包括因傷者為俄羅斯公民,因此俄方請求分享「相關物質的資訊」,並進行「聯合調查」。俄國認為英國在情況未明就到處放話、串連各國誣賴俄國,且於3月30日「無故搜索」俄航班機等作法皆不符合國際慣例和外交禮儀。
事實上,在收集了里帕和他女兒身上的神經毒劑樣本後,依《禁止化學武器公約》建立於荷蘭海牙的「禁止化學武器組織」(Organization for the Prohibition of Chemical Weapons)已成立專案小組著手進行試驗。這個國際組織迄今,已監督銷毀了全世界所申報持有近97%的化學武器儲備。
根據《禁止化學武器公約》,所有締約國同意永不(再)製造、儲存或使用化武,也不得協助它國從事類似活動。此外,締約國還須申報它們擁有哪些化學武器,以及相關生產設施。根據利茲大學環境毒理學阿拉斯泰爾‧海(Alastair Hay)教授的說法,大多數國家都遵守了它們的最後申報期限並銷毀化武設備,但俄美兩國並未遵守。
實際上,《禁止化學武器公約》仍然允許各國「基於和平用途」(包括工農業、科學研究和醫藥發展等),可以儲存有毒化學品及該物質的前體,但「儲量」和「保存期限」都須受到管制及監督。
然而,被認為用來謀殺里帕和他女兒的諾維喬克神經毒,從來都沒被申報過。因此阿拉斯泰爾‧海教授表示,「這種化學物質從未進入國際監管機制的法眼,部分原因是因為它們化學結構的不確定性。」易言之,未被查證、分析且命名的化學物質其實很危險,因為它無法被「明文」禁止,也成了化武規範的盲區。

互相驅逐外交官(或關閉使館)的外交意涵
隨著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簡稱「北約」)宣佈驅逐俄國常駐北約代表處7名外交官後,美國也驅逐了60名俄國外交官,甚至還下令關閉俄羅斯駐西雅圖領事館。雖然歐巴馬政府也曾因俄國涉嫌干擾美國大選驅逐35名俄國外交官,但這次顯然是冷戰高峰期以來西方最大規模的「抗俄行動」。
為反擊英國及其他國家的抗俄行動,俄羅斯外交部三月底也表示,俄國將再驅逐50多名英駐俄羅斯外交官、駐俄外交使團工作人員,以確保兩國「互駐」的外交人員數量相等。事實上,三月中時,俄國早已宣佈禁止英國文化教育協會(British Council)繼續在俄國的工作,並關閉英國駐聖彼得堡領館。
在外交的場域中,這些被驅逐的外交官就是所謂的「不受歡迎人物」(慣用的專有名詞是拉丁文:persona non grata),指的是特定外國人被某國政府禁止進入或繼續居留在該國內,但理由經常不是出於「法律原因」(比如非法入境、簽證過期等),而是「政治理由」(比如處於交戰狀態、不當政治言論等)。
通常情況中,外交人員享有不被接受國調查或起訴的豁免權,因此將其列為「不受歡迎人物」可以視為一國針對他國(外交人員)最嚴重的政治決定與待遇。這項例外條款早已是國際慣例,也被寫進了1964年生效的《維也納外交關係公約》(Vienna Convention on Diplomatic Relations)第9條中:
任何國家可以「在任何時候,不附理由」,宣布任何外交人員為「不受歡迎人物」,並否認其繼續參與外交事務的正當性(但並非否定其合法性,這屬派遣國的管轄事項,除非有雙邊條約特殊安排)。
被列為「不受歡迎人物」的人會被拒絕入境或遣返回國,或派遣國識趣地召回該名外交官。若是已經入境的人,則會被下令限時自動出境。不過,還有另一種情況,則是跟法律原因直接相關的——那就是不顧《維也納外交關係公約》規定,嚴重違反接受國當地法規,也可能被直接宣告為不受歡迎人物。
不過在歐美與俄國這次大舉飭回外交官的外交戰中,歐美的理由是「俄國外交官涉及『不符合外交任務』等情資蒐集與間諜行動」,而俄國則是基於互惠原則(不要被中文騙了,reciprocity在國際關係中更多時候是「以牙還牙」的意思,俗稱“tit for tat”),也隨之驅逐英國的外交人員,作為回應。
值得提的是,美國更依據1947年的《聯合國與美國關於聯合國總部協定》第4條第13項第b款,要求俄常駐聯合國代表團的成員離境。與兩國外交不一樣的地方是,會員國駐聯合國(或其他國際組織)的外交人員並不適用維也納公約的規定,但該協定提到,「若居留特權遭濫用,得受到美國法律的干涉」。

間諜行動:國際法中歷史最悠久的規範真空
上面談了禁止化武,針對的是不能使用太過分的「手段」;談了不受歡迎人物,針對的是不務正業的外交「人」員。然而,似乎都沒有真的談到間諜或情報行動這件「事」(espionage)。這是因為國際法並沒有真的禁止或限制一國在他國境內進行這類型的活動,只要不要太過分,或不要被發現。
間諜活動形式多元,但不外乎是透過掩護的人(本國人或外國人)或網路活動,進行情蒐或干預外國內政(比如1970年代,美國透過情報行動擾亂尼加拉瓜政局,得參見國際法院1986年關於《軍事與準軍事活動案》的判決)。因此許多學者認為,經證實的間諜行動,應可直接視為一國政策工具之一。
目前與間諜行動最直接相關的規定,是《聯合國憲章》第2條第1項(主權平等)及第4項(不干預外國內政)了;而這兩者又能衍伸出侵害一國人民整體的「民族自決權利」的可能性。
歷史已不可考的「間諜行動」本身比國際法還悠久,也從來都不一定違反國際法,端視實施行動的手段是否踩到紅線,而所謂「紅線」也依時代脈絡有所不同。比如二戰前,間諜行動被戰爭法(jus in bello)所規範(但甚至不被視為戰俘);戰後,國際社會開始追求和平、法治等價值,紅線區也越劃越大片。
交戰時,各國本來就把彼此視為敵人、涇渭分明,因此間諜行動的正當性似乎不證自明,彷彿本來就該是軍事行動的一部分。然而承平時期,如冷戰後的英俄(不考慮兩國參與的代理戰爭中總是對立的話),間諜的法律性質顯得曖昧不明,既不被明文禁止,也不被承認合法,儼然是刻意保留的規範真空。
按照各家說法的最大公因數來看,當代間諜行動的紅線包括:不要產生侵害他國主權或人民自決的疑慮、不要非法使用武力,用以干預他國內政(遑論使用被禁止的化學武器)。若間諜行動太猖狂,經發現,甚至可能構成聯合國大會第3314號決議(1974年通過)中的「侵略行為」(aggression)。
不過若只是安安靜靜蒐集情資怎麼辦?這引發學界激辯:「外國干預」一定包含武力介入?聯大第2625號決議(1970年通過)認為「所有間接的干涉行為(interference)」都算違法。這解釋起來已太廣泛,沒想到後來的第36/103號決議(1981年通過)更包山包海,諸如外國介入、意圖策反的政治宣傳。
瞎咪!這不就是今天許多國家禁止外國組織支持國內社會運動、壓制資訊自由的藉口嗎?回頭看,或許我們會覺得冷戰時期的聯合國過於偏執,被「主權至上」沖昏頭,完全沒考慮到後遺症。但一直以來,關於俄國透過「假新聞」來影響西方各國選舉的傳聞也越來越多,使得再安靜間諜行動也令人不安。

結論
最後讓人不禁想提一下《冷戰諜夢》(The Americans)這部影集,多數間諜終生都得過著戰戰兢兢、如履薄冰的矛盾人生。冷戰後,雖然有許多學者認為間諜行動對一國主權、領土完整性和國防安全造成極大威脅,建議各國應著手建構相關國際規範,但各國仍傾向將其視為國內法問題(大多是刑事)。
回到里帕毒劑暗殺案,顯然英國政府因為沒有把握找到「兇手」,因此只能利用化武這個把柄,透過條約義務來指控俄國,但若真要成立法律意義上的「國家責任」仍然非常困難(若抓得到人,英國應該已經依國內法起訴了),而這也是為什麼俄國總是揪著「有種就拿出證據」這麼任性的回應方式。
可見國際社會對間諜(及其人生)終究誠惶誠恐,因此得上綱到主權完整、政治獨立、國際和平等討論,而情報機密也理所當然被視為國家資訊主權一部分。弔詭的是,各國卻也沒有意願嚴防這件事發生,原因在於「知彼」也是決策時的重要依據,因此間諜行動仍很大程度存在於「沒有絕對是非」的法律真空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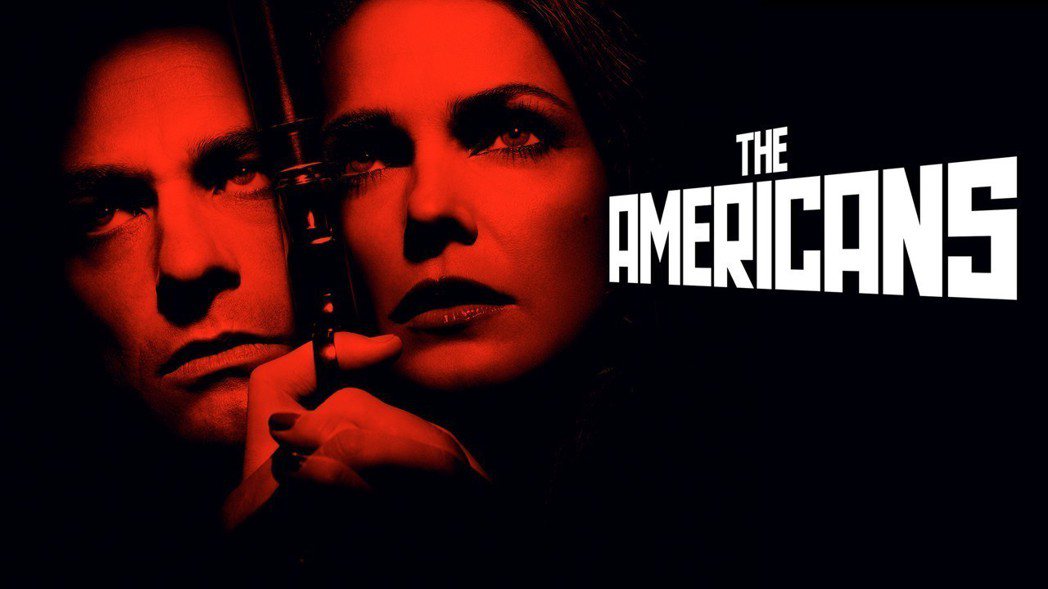
|參考資料|
- Deeks, Ashley (2015) ‘An International Legal Framework for Surveillance’, Virgini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55:2, 291-368.
- Eileen Denza (2008) Diplomatic Law, Commentary on the Vienna Convention on Diplomatic Rela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Forcese, Craig (2011) ‘Spies Without Borders: International Law and Intelligence Collection’, Journal of National Security Law & Policy, 5, 179-210.
- Ohlin, Jens (2017) ‘Did Russian Cyber Interference in the 2016 Election Violate International Law’, Texas Law Review, 95, 1579-1598.
- Radsan, A. John (2007) ‘The Unresolved Equation of Espionage and International Law’,
- Michig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 28:3, 596-623.
- Sulmasy, Glenn & Yoo, John (2007) ‘Counterintuitive: Intelligence Oper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Law’, Michig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8:3, 625-638.
- 文:李柏翰,畢業於東吳法研所國際法組,正在英國University of Sussex從事博士研究,主要關注弱勢群體健康的社會因素及相關國際人權法之議題。目前也是法律白話文的編輯之一。
- 更多:FB|IG|We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