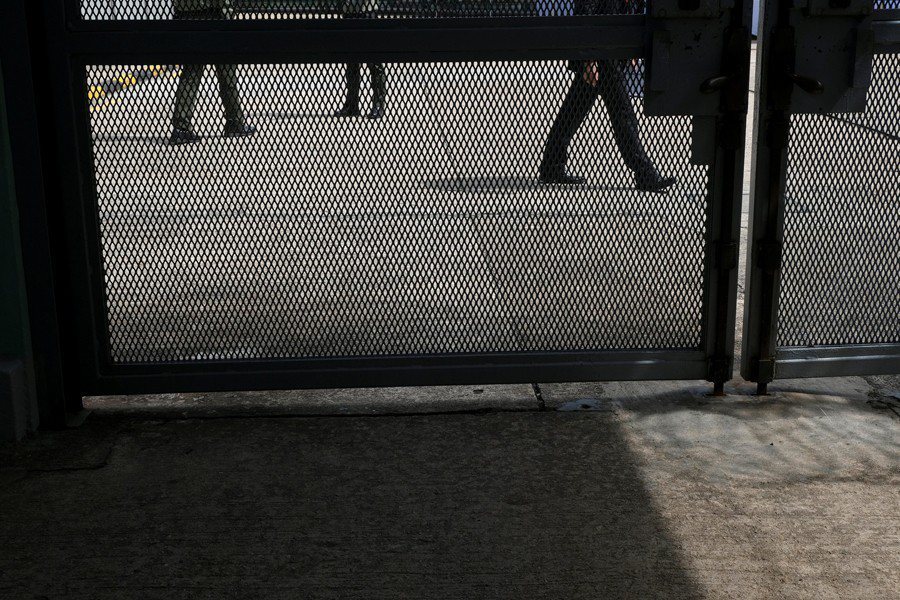林士欽/從法國法省思,台灣版未成年人保護法律體系是否有用?(上)

(※ 文:林士欽,銘傳大學財金法律系助理教授、法國艾克斯馬賽大學法學博士)
立法院本會期截至目前為止,共修正了《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下稱「兒少福法」)、刑法及《少年事件處理法》(下稱「少事法」)等幾部與兒少有關之法律,這些法律再加上《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下稱「兒少性剝削條例」)構成了「台灣版」未成年人保護的法律體系之主要支柱,但這些支柱是否能有效地為進入司法系統的國家下一代提供足夠的保護?是本文想要探索的問題。
本文將從保護對象與保護類型二方面來辨析,並輔以法國法的觀點,試圖從中挖掘修法盲點。但在進入正題之前,必須先說明行政、司法在兒少保護任務上的差異性。
對於未成年人的保護,乃至成年人的保護,都會有預防與治療這兩面。預防是行政的職責,治療則屬司法之權限。也就是說,行政機關應主動積極地預防危險產生在未成年人周圍,至於危險發生後的創傷治療,則適合由消極受理案件的司法機關負責。
基於上述之分工,本文要談論的未成年人保護法律體系,是指司法保護,而非行政保護。
另外,對於先前社會上頻傳的虐兒事件,真正應該強化、或是改善,應是社政主管機關的兒少曝險預防機制(事前),以及兒少被害人之身心治療方式(事後)。
然而立法者卻不思此途,反倒選擇以加重刑事罰則的方式來預防虐兒事件的再度發生,惟重刑是否真能嚇阻失職父母的不當管教行徑,仍有待後續觀察。
保護對象:未成年人
未成年人司法保護的法律體系,是以「未成年人」作為規範保護之對象,所以如何界定未成年人與成年人的年齡界限是幾歲,以及在這個界線以下之人該如何「稱呼」等兩個問題,必須先行釐清。
首先,從法國的法律看來,就界限來說,不論是民法或刑法,都將未成年訂為未滿18歲之人,與國際上的《兒童權利公約》(下稱「兒權公約」)第1條「兒童係指未滿十八歲之人」所規定之界限相同。
反觀我國《民法》將未成年的界限訂為20歲(第12條),刑法(第18條)及兒少福法(第2條)皆訂為18歲,兒少性剝削條例則沒有明文規定。
筆者對於兒少福法竟然沒有與《民法》為相同規定感到納悶,因為兒少福法的某些規定和《民法》親屬篇是有關聯性的,例如該法第3條規定「父母或監護人對兒童及少年應負保護、教養之責任」。
倘若兩部法律在劃定未成年人的年齡界限有不一致的情況下,父母對於18歲以上未滿20歲之子女的保護與教養義務,到底應該適用兒少福法第3條之規定予以排除,還是依據民法第1084條第2項之規定必須承擔,則會產生疑義。
剛剛提到,兒少性剝削條例沒有明文規定年齡界限的情況下,也產生在適用上應當以《民法》、刑法抑或兒少福法為據的問題。更有甚者,兒少性剝削被害人之年齡,應以行為時的年紀,還是檢警機關救援時作為認定依據,相關條文同樣沒有規定,主關機關衛福部也沒有任何相關函釋加以說明。
在法國,法律對於未滿18歲者的稱呼,混用「未成年人」(mineur)與「兒童」(enfant)兩個詞彙。儘管如此,仍有其脈絡可循。
在法國民法的範疇,談論到家庭,尤其是涉及親子關係(filiation)、親權(autorité parentale)之規定時,「兒童」一詞是被偏好使用的,因為兒童一詞的法文詞義帶有直系卑親屬之意涵,使用上比「未成年人」一詞較為洽當;法國刑法則偏好「未成年人」的用語,這是因為「未成年人」的定義明確(18歲以下),較之「兒童」一詞更能合乎構成要件明確性的要求。
我國法使用兒童及少年來稱呼未滿18歲之人,似乎無法從法規中看出特意區分兒童及少年的實益,況且,如果連兒權公約都只使用兒童一詞來稱呼未滿18歲之人,號稱要遵守兒權公約的台灣,為什麼要堅持在內國法規中區分兒童及少年兩個稱呼呢?
|

保護類型:未成年罪犯、曝險未成年人與未成年被害人
筆者在2009年秋天負笈前往法國艾克斯馬賽大學就讀時,原本打算以未成年罪犯「刑事程序」之指導性原則為題攻讀博士,但法國教授卻表示未成年人犯罪之觀察不能只側重在程序面(即如何從程序上處理未成年人及其犯罪),還必須兼顧實體面之刑事回應,才是對未成年罪犯(mineur délinquant)刑事司法全面且完整的觀察,而之所以必須如此,與這個司法範圍的形成歷史有關。
這段形成史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為羅馬法時期,在當時,視未成年人為「小大人」,若有觸犯刑法,則適用與大人相同之刑罰,但得「減輕其刑」;第二個階段是在17、18世紀,視未成年人為「發展中有自己需求」之人,此等人士若有觸法,需要的不是和成人相同的刑罰,而是透過「專業處遇」教育他們。
第三個階段則是進入到20世紀初,由於受到社會防衛理論倡議從人格了解罪犯的影響,便開始有「專業法院」與「適切程序」之立法產生,企圖藉此探究未成年罪犯之人格,以便對其施以最適當之刑事回應。
從減輕其刑到專業處遇,再到「專業法院」與「適切程序」,一步步建構出今日未成年罪犯刑事司法的範圍,不僅止於實體面,也包括程序面,而支配此一司法的法律如我國少事法、法國未成年罪犯條例,都必然會同時規範實體與程序事項。
未成年人之犯罪,在數十年前的法國,往往是一個家庭危機的表徵,因此,當時的未成年罪犯,同時也會構成「曝險未成年人」(mineur en danger)。所以要了解未成年罪犯,就不可能不去觸碰到曝險未成年人這個概念,這是第二種需要司法保護之未成年人類型,也是最重要的類型。
因為一旦國家沒能及時協助曝險未成年人的家庭走出困境,曝險未成年人若不是以犯罪的方式自救,就是淪為父母行為之被害人。而這後者,就是需要司法保護的第三種(也是最後一種)未成年人類型,即未成年被害人(mineur victime)。
嚴格說來,我國法在5月31日少事法修正通過前,並沒有曝險未成年人的概念,而相當於這個概念的規定則散見在兒少福法(第56及62條的緊急安置)、兒少性剝削條例(第2條性剝削態樣)以及少事法(第3條虞犯)之中。
分散立法反映出只著眼表面事實,而忽略兒少背後隱藏家庭危機的治標不治本,因而只對兒少卻忽略家庭的法律回應能收到多少成效,便有待商榷。
又這些規定的內容本身也有疑義。
首先,兒少福法第56條賦予縣市主管機關「應」安置或緊急安置「未受適當養育或照顧」之兒少,同法第62條則允許兒少父母等關係人「申請」縣市主管機關安置或輔助「家庭發生重大變故,致無法正常生活於家庭」中之兒少。
然而,無法正常生活於家庭不就是未受適當養育與照顧嗎?有必要分成兩條規定嗎?又為什麼縣市機關在第56條之情形是主動介入,在第62條卻採被動受理,差別立法的理由為何?
其次,兒少性剝削防制條例第2條第1項第4款規定,「使兒童或少年坐檯陪酒或涉及色情之伴遊、伴唱、伴舞等行為」構成性剝削,故坐檯陪酒的兒少便構成性剝削之被害人,適用上述條例保護之。
然而,若是出於家庭經濟因素而陪酒、伴遊之兒少,不就是在家庭中曝險之未成年人嗎?如果國家不能協助家庭走出困境,只是針對兒少有所作為,一旦處置結束,家庭經濟狀況仍舊沒有解決,這些重返家庭的兒少,將來還是很有可能會重回性產業。
況且,國家從「曝險未成年人」的角度來輔助兒少及其家庭,絕對勝過用「性剝削被害人」來幫他們貼標籤。
此外,同條例第2條第1項第3款也規定性剝削為「拍攝、製造兒童或少年為性交或猥褻行為之圖畫、照片、影片、影帶、光碟、電子訊號或其他物品」。基此,發生在未成年同儕或情侶間的性好奇,例如「單純互相自拍或錄影」,依照前述條文文義,也會構成性剝削。將未成年人對性的好奇,也當成性剝削,這指責(或者說是標籤)難道不會太沉沈重嗎?
特別針對兒少性剝削定立專法,是否確實有其必要?這部法律對於不該進入性產業的兒少真的能提供特別保護嗎?還是只是一種特別指責與沉重?
5月31日剛完成三讀的少事法修正案,引進了法國法上曝險未成年的概念,藉以取代「虞犯」,顯然我們的立法者已經注意到隱藏在少事法第3條第2款(舊法)那七種偏差行為態樣背後所隱藏的家庭危機,惟在法律效果上,如果沒能進一步創設出可以協助家庭走出困境之輔助措施,供有關單位選擇適用,那這樣的更名恐怕只有形式上的意義而已。
又修正通過後的曝險未成年人與兒少福法第56及62條間的競合關係要如何解決,繼續維持分割適用,抑或是等來日全部歸給行政部門,或是全部回歸司法部門處理,本文認為基於兒少基本權(自由及家庭生活權)之保障以及兒權公約之要求,應採司法主導、行政執行的模式為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