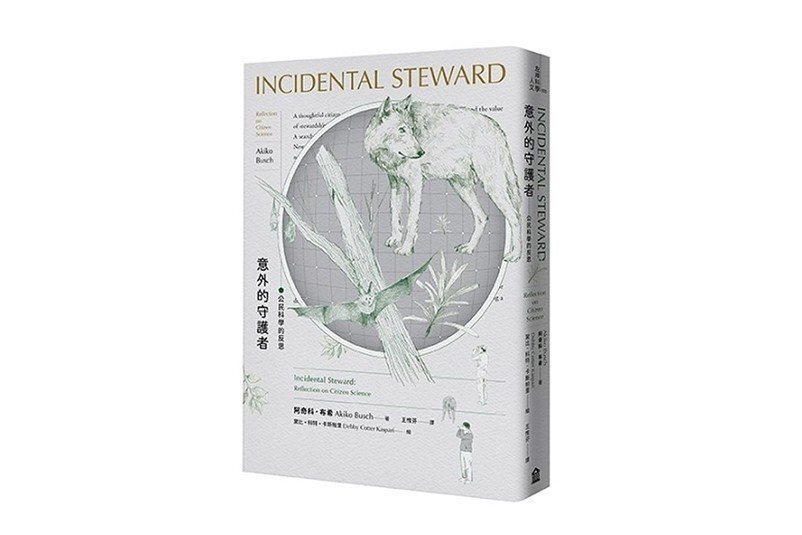陳文琳/生態學的故事沒有結局——讀《意外的守護者》反思公民科學

每年9到10月間,臺灣西部的出海口,會陸續飛來一群被稱作烏面抐桮(黑面琵鷺)的侯鳥準備渡冬。黑面琵鷺覓食、交配以及儲存回返體力的期間,來自四處的鳥友會頻繁躲在某處觀看這些侯鳥的日常。他們或是將其視之為一種休閒,用等待換來一張一張黑面琵鷺照片,或是對看鳥產生某種熱情,有的甚至在重複的觀看中,無形之間建立起一種地方「歸屬感」。
然而無論是何種,因這些「平凡人」長期投入而無意間聚集的訊息,都極有可能是一筆珍貴的自然紀錄,且在參與的諸多過程之中,成了如阿奇科・布希(Akiko Busch)形容的,那個對生物、環境,甚至自己棲居之所「意外的守護者」。
公民科學:自然事件的聚合與發散
《意外的守護者:公民科學的反思》(Incidental Steward: Reflections on Citizen Science)是一本對環境投以深刻凝視,並探索我們與生物、環境關係的反思之作。
布希說,這是一本寫給她曾經生活過的地方的11封長信。從對蝙蝠、菱角、看天池、苦草、郊狼、鯡魚、千屈菜、鰻魚、扛板歸、吉丁蟲與白頭海鵰等這些日常且持續的觀察當中,她除了想弄清楚地形地貌不斷變化的原因,也透過與志工團體及科學家長期合作,試著建立一個個「公民科學」(Citizen Science)的微系統,讓零散的科學數據能夠產生有意義的聚集,累積成自然的資料庫。
書中提及兩個啟發她長期投入哈德遜河谷(Hudson Valley)觀察的重要資料庫。一是丹尼爾・史邁里(Daniel Smiley)約十萬張的「索引卡」,史邁里每日讀取溫度兩次,並觀察住地的周遭,比方太陽黑子週期、春季鳥類的抵達、開花植物初次開花的日期、蠑螈的繁殖行性與游隼的築巢偏好,從而成為物候學(Phenology)的基礎資料。
第二個則是線上自然誌《哈德遜河年鑑》,其編目會收集哈德遜河每週的觀察。這一筆筆資料的匯集,因存在太多變因,也許不太準確,無法在短時間顯現其意義,但從更大尺度的時間看來,卻可能隱含環境變化的重要訊息,就算只有單筆資料亦然。
無論是索引卡或《哈德遜河年鑑》,布希認為,這些紀錄包含了自然事件的「聚合」(convergency)還有「發散」(divergency),以預期當季事件以及意料之外的種種發生,彙整出哈德遜河谷生態的資料庫。簡言之,這些不論聚合、發散抑或偶然的「自然事件」,皆是環境持續變動不居的微小證明。

公民科學凝聚而成的人的交會
至於何謂公民科學,康乃爾鳥類研究室(Cornell Lab of Ornithology)主任里克・邦尼(Rick Bonney)主張,從公眾參與科學論述的理念到社會良知驅動科學家研究,包含整合社區成員,擴大蒐集科學數據,與科學家進行合作皆屬之。
後來,這個定義愈來愈廣泛。美國環保署第二局局長朱迪恩・恩克(Judith Enck)認為「社區總是第一個發現問題的」,她定義公民科學家只要是使用任何工具,著重在科學測量或描寫的人,便屬於公民科學的一環。
布希正是採用最廣泛定義來看待這一個個公民關注環境的行動。她認為即便是志工、科學家與監測組織之間看似鬆散的合作關係,也能夠因為跨區域的連結,促使這些微小社群,以來自四面八方的「個人」資料蒐集為驅力,漸漸打開關注環境的觸角,匯成一股相對穩定而持久的力量。
布希發現,公民科學力量凝聚了人與人的「交會」,這些人有的是科學家、家庭主婦、退休人士或學生,他們來自不同地域,因著不同理由投入。其中,有被IBM裁員的經理,她將管理所學運用在看天池的生態紀錄;911事件的罹難者遺孀南西,每年固定返回哈德遜河拔除菱角;或是10幾歲的女孩參與計數鰻魚產生的驚喜之情與提升自己對社區事務的關注力等等。
她認為上述的種種努力,會使我們重新看待與土地、環境的連結,甚至動用想像力來解釋我們眼前的事物,重建我們對於自身存在與對土地的「歸屬感」。
這份地方歸屬感的建立承繼過往的認知:與萬物共生,卻同時也必須考量到未來的「住戶」。由於全球環境與氣候變遷、棲地喪失、生物逐一滅絕等因素,迫使人們不得不作出回應,部分民眾對環境的責任感也逐漸提升。加上許多量測技術的增進,透過志工收集來的大量資料,我們得以在環境發生問題後,儘可能找出能夠因應的修補措施。


進入私有地,從衝突到協商的可能
公民科學可以發揮作用之處,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區塊:志工團有很大的機會進到私有土地將資料補齊。進入私有土地之所以重要,是因為生物棲地是「跨區域」的,非人類土地劃設所能設限。這個跨域特性往往會產生某種衝突,卻也具有協商的可能。
比方〈看天池〉這章當中,兩棲爬蟲類專家兼政策保育研究者麥克・克萊門斯(Michael Klemens)與幾個組織組成研究團隊,結合科學研究與土地政策,制定相關的土地利用規劃政策。這麼做不僅能與地主建立友好關係,也讓在地志工們,繼續到跨域的「天池」作長期的生態紀錄。
再如〈梣樹裡的蟲〉,兩位實習生布萊恩與艾咪,為了理解梣樹遭受蟲害的程度,到處監測梣樹綠吉丁蟲,經過私人領域時,若有在地人因好奇而發問,兩人會詳細說明緣由,雖然也有可能讓在地居民產生懷疑或不信任,但布希認為這是「轉譯生態學」(translational ecology)的一種,有機會提升利害關係人(在地居民)對所處環境產生關注意識。
但也有些狀況像是〈穿過樹林的藤蔓〉,由於對扛板歸這種蔓延快速的植物沒轍,造成兩方想法上的歧異。一塊私有地主人茱迪思・威爾希就提到,儘管她勤奮除草,確實也發現效果顯著。然而當提到要進行整頓,政府官員與私地地主之間不一致的想法,往往令這項「除草」工作嘎然終止。
布希認為人類對破壞的容忍力似乎完全沒有上限,因此當拿恣意生長的扛板歸沒辦法時,有人亟欲積極處理,有人就會選擇忽略,但這一切仍有「聚合」起來的可能,端看利用何種方式去召喚不同的人。
在布希看來,科學有它令人信服的一面,詩也是看待世界的一種方式,這兩種並不衝突,對每個人有不同程度的影響力,但若能讓這個邊界為相互協商所縫合,就可能喚起更多關注,進一步引發行動。
公民科學不夠嚴謹?
以眾人資料蒐集與觀察的累積來反映自然,或許不夠嚴謹、猜測性質甚至鬆散,但仍然如布希提到的,它能反映出自然事件的狀態,帶給我們一種「自然秩序」(earthly order)的意義。
無論是在年限將至老槐樹樹洞裡求生的蝙蝠;從美西遷徙至美東,經由漫長演化的郊狼;或是遠從大西洋馬尾草海域前來哈德遜流域繁衍的鰻魚;甚至非原生種(nonnative)千屈菜、菱角等,這些生物在漫長的環境演化中適應生存下來,一定有其緣由。因此,這些「居民」的遷徙與定居,也經常透露重要的環境訊息,促使我們以不同的目光再一次省視人與自然的關係。
舉例來說,在〈空地上的郊狼〉一章中,負責管理威斯切特郡郊郊狼棲地地圖的生物學家馬克・偉克爾(Mark Weckel),聚集公民科學力量,以目擊或狼嚎為基準,將之作成一份地圖。這份研究發現,郊狼的活動範圍,儘管也包括都會化地區,但仍屬農村居多,後者對狼存在的適應性較高,不會視之為一個問題;反之,則因對狼不甚熟悉,發生狼闖進私人領域的零星事件時,容易使人恐懼。
然而,無論何者,這份地圖顯現一個「新景觀」的形成:郊狼與人類的生活區域無可避免地重疊。其重要性在於不僅讓科學資料透明化,也給私有地主評估狼在私領域活動的可能性,這個討論需要人們的積極參與,我們與環境的連結程度,將會決定如何回應新景觀。

▲ 民眾以目擊或狼嚎為基準,將資料上傳到共享地圖。
「外來種」的說詞是「文化焦慮」?
又如〈沼澤中的千屈菜〉對於「外來種」(Alien species)生物的諸多反思,亦提供了不同的思索面向。陌生生物來到異地之後,經年累月,因其沒有任何天敵意外長得繁盛,甚至干擾其他原生生物或大幅度改變環境樣貌,我們經常會使用「入侵」「干預」「侵害」等帶有軍事意味的用詞來形容這個生態現象。
但長期研究千屈菜生態的艾里克・基維亞特(Erik Kiviat)認為就算是原生種植物亦可能入侵,重點在於它是否過量。對於此生態現象,他傾向使用中性詞「原生」(native)與「非原生」(nonative)稱之。此外,在他與組織及許多志工組成的研究團隊裡,發現千屈菜的生態多樣性,是許多昆蟲的蜜源、生物的交配產地與棲地,並非所有非原生種都具備負面特質。值得一提的是,非原生生物的異地生長,通常與環境、氣候變遷、伴隨人類需求的引進或植養有關,去脈絡談論非原生種議題,其實亦是一場災難。
當然,布希也提到,非原生種生物對環境的影響,確實也有失控的例子;非原生種生物該移除抑或加以利用,也有分歧的立場與說法;甚至連「外來種」這樣的說詞都可能是「文化焦慮」的呈現,錯置對經濟、社會和文化變遷的焦慮,把自己與外來和異地植物對立起來。但她強調:
就算多數人真的對非原生種抱持偏見,肯定也因為熱愛擁抱陌生事物的意願而平衡回來;我們就是很容易為異國情調所驚嘆與誘騙。穿插在我們自己後院和花園的綠竹或中國芒,或是任何非原生植物,其實都在證明新事物對人類深具吸引力。受到那些不屬於我們的事物所吸引,是我們的天性。在自然界中,我們的歸屬感顯得相當不一致、難以預測而且混亂不穩定。
當我們正視自我在面臨陌生事物立場上的不一致與矛盾,或許我們對非原生種生物就能產生移除、趕走以外的思索路徑,並試圖找出更多的解決之道。
生態學的故事沒有結局
「事實何時獲得意義?」是布希參與幾個漫長的觀察與紀錄時,不斷提出的問題。在氣候、環境變化更為劇烈的此刻,人們該如何看待自然的變動,未來的生態會是什麼結局,布希沒有確切的答案。
但她引用艾瑞克・幾米亞特(Erik Kiviat)的話:「在生態學裡的故事沒有結局,只有可能的結果」,說明了面臨未來的不可測,我們無法只用梭羅式「狂野式的想像力」了解我們的日常,而是得更深層地去找出,能夠因應自然變化的速度與性質的力量。
在布希看來,這份力量不在他方,而是人們將「規律的行動」或稱「重複運動任務」(repetitive motions tasks),實踐在自己所處的地方,無論是聽見一聲郊狼的嚎叫,或是紀錄一對白頭海鵰的生活,數算烏面抐桮在溼地覓食的數量。唯有如此,我們才可能在不可測的未來裡,找到可能安放自身與他者的棲身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