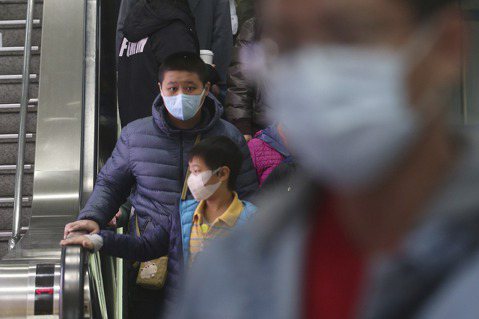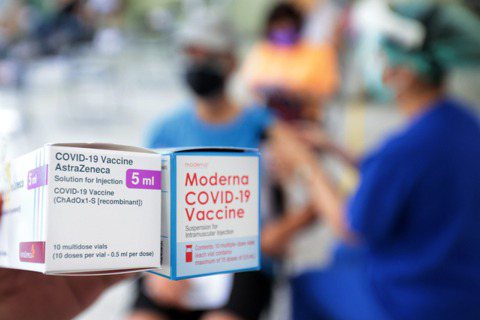陳嘉銘/武漢肺炎政治哲學:搶口罩自保會傷害他人,如何取捨?

我們面對2019新型冠狀病毒(2019-nCoV,俗稱「武漢肺炎」)該採取的基本道德原則是什麼?遇到道德難題時,我們該怎麼取捨?
我先提出看起來很明顯的三個道德原則,看是否符合我們的需要:
- 道德原則一:自保原則。每個人都有追求自我生命保存的權利和義務。
- 道德原則二:不傷害原則。我有義務致力於不造成他人傷害。
- 道德原則三:協助他人原則。如果我可以充分確保我生命的保障,我應該盡可能去幫助這世界上(或者我關懷的社群)每個人的生命保存。
自保原則
從道德原則一來看,每個人都有義務進行健康的自我管理。這包括了,勤洗手、避免高密度聚會和往來、避免出入醫院、公共交通和密閉娛樂場所。即使有必要出入,也必須要正確戴口罩等等。
但是,每個人也都想囤積口罩。這似乎難以被責備。可是如果囤積非常大量,我該被責備嗎?我囤積的限度在哪裡?我不是該囤積愈多愈好嗎?畢竟我們不知道未來會怎麼發展。專家說,現在沒有社區感染,所以沒有症狀的人不需要戴口罩。可是明後天如果發生了社區感染,我還來得及搶口罩嗎?
讓我們假設資源很緊張,集體隔離無法做到單獨隔離,因此集體隔離的人感染機會更高。如果我是被集體隔離的人,例如如果我是關在武漢封城裡的人,我可以逃離嗎?畢竟我有自保的義務和權利?如果我是被封在武漢的人,而且我發燒了,難道我就不能逃離嗎?畢竟其他大城市的醫療資源還很優渥,我生存的機會比較高。畢竟我有自保的義務和權利?
再者,我們有權利基於自保的必要性,把有感染嫌疑的人都集體隔離起來嗎?隔離對象的範圍要擴大到什麼程度,我才能確保自保是充分的?

不傷害原則、協助他人原則
這裡,或許我們會認為道德原則二可以幫助我們解決這些難題:我不應該造成他人傷害。
基於道德原則二,我再一次有自我健康管理的義務,不讓自己成為感染源。而且如果我從疫區回來,我有自我隔離的義務,不去感染其他人。
而大量囤積口罩,等於減少他人取得口罩的機會和數量,相當於某種程度上造成他人的傷害。所以或許我們囤積口罩該因為第二個原則而有限度。但是我囤積的限度在哪裡?我如何得知,在什麼囤積點上停止,我不但保護了自己,也留給其他人充分和一樣好的防護資源?
基於道德原則二,如果我是封城裡、被集體隔離的人,我也不應該逃出來,因為我可能在潛伏期,可能會傳染給別人。我逃出來也可能造成模仿效應,大家都想逃出來,如果大家都逃出來,危害更大。但是至少我逃出來生存機會變大了?
這裡有三個難題。
第一、自保和不傷害他人,這兩個原則如果相衝突,哪個原則優先呢?
追求自保如果是我們的首要的道德權利和義務,即使我們有可能傷害他人,難道我們不該追求自保的最大化嗎?人們似乎無法抵擋懼怕死亡的恐懼,似乎必然會為了這種恐懼,而不管他人受到傷害。
如果「自保原則」的道德優先性遠高於「不傷害原則」,那「強者法則」就會開始出現。身強體壯的人開始可能打劫體弱的人囤積的口罩。他們幾個人可能集結起來,打劫運送肺炎相關醫療資源(口罩)的運輸車。比較聰明、比較富裕、比較有權力、比較有關係的人等等,就會開始各顯其能囤積更多口罩和相關醫療資源。弱者也會集結起來,以集體強者的力量,對抗個人。在「強者法則」運作下,各種強者的生存機率比弱者高出許多。
第二、即使我想要遵守道德原則二,「不傷害他人」,可是我也不知道怎麼做。我不知道不傷害他人的尺度在哪裡。
口罩要囤積多少才算傷害他人?誰需要被集體隔離?所有去過中國的人?來自武漢的人?我不能逃離封城嗎?畢竟我傳染他人的機會即使存在,其他地方的醫療資源也比較充分,不會造成太大傷害?
第三、道德原則三看起來更難遵行。我怎麼知道自己的生命已經充分獲得保障?誰知道明天會怎麼發展?基於對死亡的恐懼,我們對自保機率的追求,只有不斷更大化,沒有所謂的充分這回事。
這三個難題都牽涉到知識的不確定性。我們不知道該做到多少,自保才算足夠。我們不知道該遵循什麼尺度,才不算傷害他人。我不知道我對他人的威脅可能有多大。我們不知道該怎麼做,才能兼顧這些道德原則。

國家的任務
知識的不確定性似乎都來自對死亡的恐懼。在死亡的恐懼面前,我們無法有共同的尺度。
基於這三個難題,或許有人會說,顯然我們需要考慮集體合作。也許集體合作就可以同時兼顧這三個道德原則。好吧,那國家進來吧。讓國家建立尺度,建立知識的確定性。讓國家說有光。這就可以解決問題嗎?
每個人在這種情況下都會贊成國家需要掌控和管制情勢。而且都會贊成國家在這種情況下可以動員所有資源,包括每個人的移動、勞力和財產。國家的任務是幫助國民集體生命保存的最大化。
國家在這裡有三個優勢。
第一、國家有公共定義的權威。國家出面統一定義了什麼是充分的自我保存(需不需要戴口罩、囤積口罩的限度),定義什麼是對他人的不當傷害,定義了我們該隔離誰、不該隔離誰。即使國家背後沒有科學社群背書,國家具有公共定義的權威,對情況有很大幫助。因為它穩定了知識的確定性。每個人似乎有了尺度,不會永無止盡地需要和想要累積更多醫療資源。
第二、國家有懲罰機制。如果我遵守「自我保存」和「不傷害他人」的公共規則,其他人都不遵守,我最倒楣。國家的懲罰機制因為嚇阻了違規的人,也因此幫助我能夠遵守規則。但是嚇阻效果有其限制,在死亡的恐懼下,很多人還是會違規去追求自保機率的最大化。
第三、國家有科學社群的支持。公衛和醫療專家在國家的支持下,統一、及時、透明地對全國公布所有武漢肺炎的相關資訊,提供全民該怎麼做的建議。他們不僅要說,他們知道什麼,也要說他們不知道什麼、以及他們在未來何時能夠知道什麼。好的、壞的都要說。這些公共權威必須擁有公共信任,因為人們是否會聽他們的專業建議,全部依賴於他們是否能贏取信任。
在以上國家管制的狀況下,我們似乎就該接受國家頒布的公共定義、守法、聽從國家的指揮。果真如此嗎?

我們能信任國家嗎?
首先,我們願意讓國家調度所有資源,包括我的移動、勞力和財產,因為我們相信這能夠幫助集體生命保存的最大化。
可是國家一旦有這麼大的權力,我們如何確保國家把每一個國民的生命價值視為平等呢?我們如何確保國家不會濫權、隱藏資訊,只想保護特權階級的利益呢?
再者,民主國家一定會表現得比威權國家好嗎?威權政府的正當性高度依賴經濟成長的表現和人民的安全,所以它對情勢的敏感性一定比民主政府差嗎?民主國家因為講究平等,有細瑣的考試和選用規則,因此政府容易平庸化,人才很難在官僚和政府體系中出頭。民主國家的人民對政府的公共信任感一定比較強嗎?有些民主國家是,有些民主國家似乎不然。民主國家的資訊,因為言論自由,一定比較透明嗎?可是民主國家的誤導資訊和偽訊息似乎也很多。
最後,即使生存在一個對政府和科學社群有相當公共信任感的國家,我們真的能完全信任政府和科學社群嗎?
過度仰賴專業、經驗和官僚體系,可能會導致錯誤的訊息判斷,乃致導致錯誤的組織決策。如果自保是首要的道德義務和權利,我們是否還是要有準備政府是可能犯錯?我們要準備違法呢?
自保作為個人首要的道德義務和權利,在17世紀是現代政治思想的哥白尼大革命。它作為頑強的個人主義,推倒了無數傳統的忠君愛國、君父體制和為國為民的意識形態。我們有準備好要擁抱這樣的自由嗎?
(原文授權轉載自「思想坦克Voicettank」,原標題為〈武漢肺炎的政治哲學〉。)

|延伸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