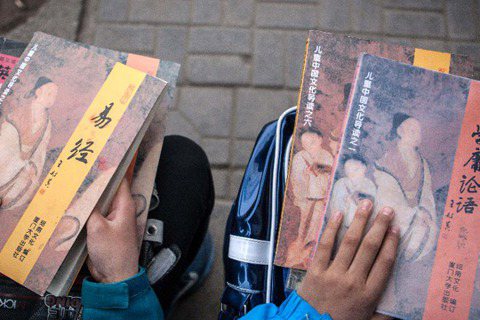給旁觀他人痛苦的我們

不論睡與不睡,過了這一夜,台灣真的不一樣了。
昨晚沒有到現場,坐在電視機前整夜流淚不止。當電視媒體集中報導警民在二樓的攻防戰,我問朋友:魏揚的記者會要去哪裡看呀?最後還是得回到臉書,那些記者來不及拍,或者不願拍也不能拍的畫面,透過網路鋪天蓋地而來。
可是,鋪天蓋地而來,還有過去被我視為朋友,在不同時期認識,曾經愉快相處的朋友,他們在臉書上的種種譏嘲。有人把鎮暴畫面當成好萊塢電影收看,有人指責群眾違法在先,被拖離只是剛好而已,還有人感嘆溫情的學運變質了。真正讓我震撼到無法言說的,是台灣真的有一群人堅定信仰著,不論因果,和平,有禮貌才是唯一真理;法制也永遠排在民主、自由之前。
深夜,電腦前,還是想盡點力,開始轉載群眾頭破血流的照片,希望能以極其微小的力量,或多或少,逼使坐在電視、電腦前無感的朋友們,與暴力真實的面孔相對。然而,習慣遊走在各種災難影像的擬像世代,暴力、痛苦、受害幾成幻覺,一如蘇珊.桑塔格所言:「若我們承認災痛是有觀眾的話,某些人的災痛又會比其他人的災痛更能吸引觀眾」。抗議者的災痛,警察的災痛,官員聲明行政體系被破壞的災痛,甚至只是辦公桌上太陽餅被偷的災痛,更多的人,選擇掉頭不顧,選擇旁觀他人之痛苦。
稍晚,收到學妹的信,問我能不能撤下照片,因為那些畫面,正是她今晚直接經歷的一切。她和哥哥原本在天津街後門靜坐,眼前是配帶方盾和警棍的保四,空氣裡有一股內縮的張力。後來,聽到幹部宣導往立法院撤離,起身,隨著群眾從北平東路往林森北路走。暗夜中,順著人群的方向前進,她有些茫然,還在思考著關於今晚所見的一些問題,擔憂行政院裡的變化。突然,大台灑水車進駐,鎮暴警察和指揮車快速推進,包圍人群,堵死出口。她的茫然感又更深了,發生什麼事了呢?我們正要撤離,應該不是針對我們,會讓我們通行吧。可是,指揮車的喇叭開始怒吼:「退到人行道!」前方群眾鼓譟了起來,不到三十秒,如大壩潰堤,人流如泥往人行道散去,後排的人被擠的紛紛倒下。到底發生什麼事了?矮小的學妹從人縫中望去,只看到鎮暴警察的盾牌,把大家往人行道壓制。她擠在路邊,還未來得及恐懼,就被身旁的男孩拎到人牆後面,並大吼著:「女生不要站在第一線!」

那一刻,恐懼感才從胃部升起,她第一次認識到自己應該恐懼。剩下的時光裡,對她來說都是既遠又近的側景:鎮暴警察拿棍子追打在路上奔逃的,或者已經被驅趕到人行道,卻站在最外圍的人。她的視線混亂,看到鎮暴警察的長棍,就打在哥哥的手臂上,有人則被警棍擊中頭部,卻滿臉疑惑,彷彿還沒有意識到自己已經血流如注,也有人在一旁痛哭:「不要打!不要打!他已經流血了,拜託不要打!」學妹很自然的,伸手摟住她,輕聲說:「不要哭,不要哭。」可是,自己再也抑制不了嘴角的顫抖。
短短的十分鐘,卻像一世紀那麼久,時間在混亂中,把自己狠狠拉長了。她後悔自己之前沒有恐懼,她真的應該恐懼。回家的路上,她問哥哥:「為什麼?」路上的人也在問:「為什麼?」大部份的人,已經帶著覺悟,準備負起自已該負的法律責任。可是,這樣的覺悟後面,是從來沒有設想過,所謂「法律責任」與暴力,以及街頭等於戰場之間的緊密關聯,更多的是對執法手段,至少還留存一絲的信賴與期待。
在臉書的聊天室中,只有文字閃動,看不見學妹的表情,卻能感覺到每回憶一些片段,就更多一些痛苦。我想忍住不問細節,覺得自己殘忍,可是,作為一個不在現場的人,此刻唯一能做的,或許也只是盡力透過見證者拼補真實吧。弔詭的是,什麼是真實?再現等不等於真實?如何能逼真?是永遠辯駁不清的悖論。學妹突然告訴我,喂,學姊,會不會警察也有警察的真實,院長也有院長的真實,而她的真實,只是像「全面啟動」一般,在一個重重的kick之後,就墜入底層的無邊夢境呢?
我不禁想起,「漢娜鄂蘭:真理無懼」電影中,執行希特勒民族屠殺命令的特務頭子阿道夫,在審判時,表情堅定而平靜。他是再普通不過的人,因著信仰,執行自己認為正確的事,和你我都一樣。一旦關乎信仰,正確與否似乎就難以辯駁,只有實現信仰手段的正義與正當,應該被檢視,再檢視。給旁觀他人之痛苦的我們,我還是很悲哀且自然地想到了Martin Niemöller被引用到耳熟能詳的詩:
| 納粹殺共產黨時,我沒有出聲,因為我不是共產黨員;
納粹殺猶太人時,我沒有出聲,因為我不是猶太人;
納粹追殺工會成員時,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工會成員;
納粹殺天主教徒時,我沒有出聲,因為我是新教徒; 最後當納粹開始對付我時,已經沒有人能站起來為我說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