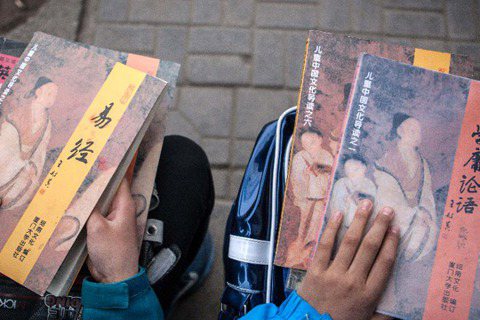斷開魂結之必要:從「國文課 ≠ 課文國」粉專看中文系的焦慮

最近,由政大中文研究生成立的「國文課 ≠ 課文國」粉絲專頁上,有數位國文老師撰文討論國文課困境,雖然改善國文教學的目標相近,但顯然有不同的立場。而關於國文教育,其實過去已經有許多討論指出諸多問題,新課綱也如火如荼調整,現在重新提起的意義會是什麼呢?是針對教學方法?是能力指標?還是教材內容?
國文課與中文系的焦慮症
2015年,唐捐與楊佳嫻在《聯合報》「文學相對論」上重論「讀中文系的人」的在地化與當代化,正逢課綱微調爭議引爆近一年且事態越演越烈,因此有了一系列就中文系如何介入社會、台文系資源分配與國文課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的思考。這一系列的討論最後停在《秘密讀者》「文」與「語」專題,以清理「國語運動」發展史的策略,對本來勢如水火的「國語」、「國文」在台灣戰後如何整併在「國文系」的學術建制進行探討,指出二者攜手重構語言的菁英與庶民階序。
不過,其實此前朱家安就已經質疑中學基礎國文必修為什麼一定要學古文,去年,《相對論》策劃「台灣高中國文課綱應廢除文言文必修」辯題,邀集朱家安與胡又天辯論文言文作為基礎教育的必要性與存廢問題。相關論題沉寂了一陣子,然後,是今年由政大中文所研究生發起,5月13即將在北一女中舉辦的「國文課=課文國?——詮釋的教與學論壇」,從論壇分組討論架構來看,應該是一次由「內部」發起,朝向「內部改革」的嘗試。目前粉絲頁上已經發佈陳茻、黃承達、李珮蓉、厭世哲學家等在教學現場有實戰經驗老師們的文章,作為論壇的前導討論。文章雖各有立場,但目標也都鎖定「國文課與國文老師的任務」以及「體制內國文教學的困難」。
不過,話說到這裡,本來是針對「國文課 ≠ 課文國」粉絲專頁上諸文所引發的問題而寫,究竟為什麼要先叨叨絮絮回頭看2015年至今的討論?
無非也是因為相關的討論進行到現在,其實對於「國文課」的歷史情境與其所擔負的語文教育任務,雖然看似開了很多戰場,但都已經有了頗為明確的願景。那麼,在此刻,我們繼續在這個問題上打轉的意義是什麼?進一步說,如果大方向抵定,國文教育此後應當一帆風順青雲直上,為什麼談起來仍覺情勢複雜而困難?
我想,論壇在現階段重新發起討論的原因,與其說是對著大眾的,不如說前行諸多討論累積對「國文課」的批評,不斷戳刺中文系在這個領域的有效與合法性,因而中文系對當代化與在地化的焦慮仍未紓困,焦慮的輪迴週期越來越短。
當然,這個焦慮一定程度來自於認同。既然名為「國文」,在台灣主體性建構過程中,實在很難避談「這到底是哪一國的文學?」「中國古典文學與台灣文學的關係?」,因為國文課在台灣的建制本來就與文化認同脫不了關係。如果未來國文必修課中國古典文學比例大量下降,或全面廢除,那麼,中文系勢必面臨一個問題:究竟我們在中學教育中的不可取代性在哪裡?從思考自己的專業是什麼,到說明憑甚麼國文課由我們來教?課綱古文比例的爭論,以及新的教學方法是否真能讓國文課回應當代社會,某種程度大概都說明了中文系、國文系與國文教學穩固的連結從戰後到現在,逐漸面臨了一種必須斷開魂結,不再是不證自明的轉型期或許正要開始。
因為這個「不證自明」受到挑戰,意識到自我說明之必要,也才有機會回視、反省自身在這個空間裡取得位置、權力的原因。我們不能總是避免去談課綱、課文內容構成的意識形態與政治,視台灣主體建立造成的文化板塊挪移如洪水猛獸,假裝文化民族主義與國文課本選文及考試題型沒有關係,彷彿中文系在中學國文科的獨佔性就不會被挑戰。

什麼東西失落了?經典與能力指標的車輪戰
不過,自我說明,當然也就有自暴其短的可能,原因是過去那些被視為理所當然的事情,其實並不理所當然。
明白戰後台灣「國文」與「國語」的結盟建立在貶低、清洗台灣本地方言與日語,重構菁英與庶民次序的策略上,今日對「國文」與「國語」的想像,是否仍有以文化階序上的文與雅來排拒生活化俚俗語的意識?如果,我們都同意閱讀能力在國文課中是重要的,那麼,選讀什麼作品似乎就會變成論爭的核心之一。
可是,當我們在討論國文課選材,將「經典」與「實用」對立起來時,是否能重新思考,經典之所以為經典,傳統之所以為傳統,真的必然是因為它夠美好,自然而然在時間的汰洗下披沙揀金的緣故嗎?
「國文課 ≠ 課文國」粉絲專頁上有一篇評論從「審美的失落」談國文課「實用化」與「經典的失落」的趨向,認為教學目標導向「實用」,使得課文選篇的「經典」空間被擠兌,越來越多學生無法從經典中經驗美感。而審美經驗的失落,表現在學生網路論戰的謾罵與著迷於淺薄的流行文化。這篇評論讓我不安的是,這樣的說法當然不會全錯,文學教育本來就有其抒情與溫厚的向度,但是,將「審美性」與「實用性」全然對立,或者將經典視為絕對能陶冶學生成為溫柔敦厚之人的路徑,是否也正好透露了中文系訓練出來的學生將對「什麼是文學?」某些直覺式的習慣,帶到了國文教學中。

三○年代以降,從龍伯純至朱光潛,分別借用康德、席勒以至克羅齊的唯心主義美學,套用在中國文學作品批評上,導致「道德性」、「社會性」與審美經驗截然為二。二分實用審美經驗的觀念在當前的中國文學研究上逐漸獲得改善,卻不能說是完全消失。
例如,我記得在一次研討會上,目睹一位講評人評論一篇通俗小說改編影視之傳播現象的論文之前,就開宗明義的批評發表者:「你的研究沒有價值,因為你研究的小說沒有美學價值可言。」這種批評的發言位置,是將「雅」的審美經驗孤立出來抬上神壇,貶低大眾文化、通俗文學的俚俗,以及文學生產的社會性。而審美、品味的高低,除了象徵你有一顆柔軟抒情體察人情的心,基本上還說明了文化資本的累積程度。並不是每個來到課堂上的學生,手上握有的資本都相同,而國文老師透過品味的訓練,試圖將學生培養成未來的文化菁英,這難道不是一種「實用」嗎?
與現職國中國文老師討論二分法的現象時,他提到,這個觀念除了來自中文系研究傳統之外,也基於國文課綱訂定的諸多語文教育能力指標,在選文與教學概念上,基本就與用「文學經典」想像所選的課文二分。就國中國文而言,「經典」是歷來被選入課本中較為知名的作品(有時候還不一定是文學史上的經典,而是課本一代又一代的沿襲形成的經典),篇目不會有太大異動,老師的教學任務是什麼呢?或許是培養學生審美,通曉人情,又或者因為經典不容質疑,所以沒有不讀的理由。而符合能力指標選擇的課文,則不一定是傳統意義上的「文學」,畢竟寫作者在創作時,並不是為了國文教育的能力指標而寫。二者斷裂勢必造成經典比例重新分配,或許又是將文學視為信仰的老師產生強烈剝奪感的緣故。
那麼,語言訓練與經典欣賞在此又慢慢拉開距離了嗎?「國文」的幽靈為什麼還在上空盤旋?可是,這種斷裂在高中國文又似乎不那麼明顯,老師們還是試圖在文言文課文中找出訓練語文能力與接合當代議題的方法,說服學生讀完這些經典,你們的語文能力就會大增喔。國中與高中國文教育也有了間隙嗎?

放不下的經典信仰?
不過,當之前的討論都指出中文系的專業、國文教育的目標與不可取代性,在於認識、使用語言,因為世界是依賴語言運作的,如此一來,閱讀能力就可以包山包海。但是,落實到教學現場,經典與實用二分,老師的觀念還是一樣的話,是否也容易變成貶低、排拒某些語言的理由?畢竟,世界運作的方式不斷推前滾動,語言與文字又如何作為一種純淨的、永恆的、只能承載美的載體?
物質、傳播技術的轉變與發明,往往影響了使用者的感知與表述方式。如果國文老師一開始就將年輕人在網路上的語言使用(破碎化也好,尖刻也好),直接視為國文教育失敗,且不說許多思想、文學前輩在前網路時代的紙上論戰中,言語如何苛刻,網路使用者在不同形式的網路媒體上發言,本來就有媒介介面、社群交往型態所形成的言說規則,以及為達到傳播效果而不斷調整的語言策略。因此,或許不要那麼快跳入批判的位置,我們總不能告訴學生閱讀與表達多麼重要,卻無視他們正遇上一個閱讀與表達的方式劇烈改變的時代。
所以,在討論國文課是否都要教經典的問題上,我們也許還可以暫時放下對經典有其神聖性的執迷,重新思考,什麼是經典?誰來決定哪些作品是經典?經典形成的方法是什麼?文學史的撰寫、文學獎的汰選、種類繁多的年度選輯與讀本等等,都是文學作品經典化的過程,它們都是由人選出來的,裡頭有個人喜好,也有人際考量,還有各種資源分配的權力關係,不是電腦選花生,好的自然會留下那麼簡單而已。進一步說,全國上下每個中學生都必須念的國文課本選了哪些課文,基本上決定了學生如何想像文學,難道不是一種比任何選本都更具影響力與決定性的經典化過程嗎?如果是這樣的話,為什麼經典是不容質疑,也不容更動?
如此一來,誰來選課文就變得重要,為什麼是這些人選(有教授,也有退休國文老師)?負責替各家出版社編選課文的委員,他們是依據什麼標準來判斷哪些作品中學生非讀不可?而學校老師又是根據什麼理由來選定該用哪家出版社的教材?其實也都是體制有沒有辦法撼動,魂結有沒有辦法斷開的原因之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