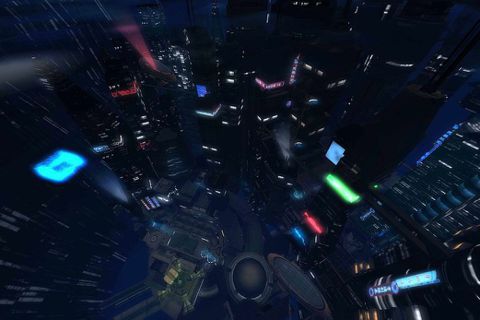機會與陷阱:智慧城市下的特區發展

2008年科技巨擘IBM發布《智慧地球:下一代領導人議程》(A Smarter Planet: The Next Leadership Agenda),報告提出將資訊科技充分運用在各行各業中的概念後,「透過資通訊等技術改善城市服務與管理,以解決都市問題、增進生活福祉」之智慧城市定義便開始成形。
不久,「智慧城市」很快地被各國政府乃至於聯合國等國際組織肯認,成為全球城市發展議程的重要組成部分。
根據地理學家Rob Kitchin等人的研究,智慧城市之所以如此快速地被廣泛接納,是得益於後全球金融危機時代,政府部門預算緊縮的同時,跨國公司亟欲尋求新技術、開發新市場。
換句話說,新自由主義政經發展促進了城市服務的市場化和私有化,也加速了智慧城市相關的計畫發展。
「特區」的任務漸趨多元
值得觀察的是,智慧城市的發展技術,時常透過建立一個特殊的監管時空加以執行。較為著名的案例有思科聯合三星與LG等大廠建設的韓國松島國際都市、由Alphabet出資成立的Sidewalk Labs所打造的多倫多智慧水岸新城(Waterfront Toronto)、台灣的桃園航空城與沙崙特區、日本國家戰略特區等。
這是由於政府在發展智慧城市的過程中,仰賴私人企業提供科技產品或服務,為使此類新興產品或服務能快速投入市場,並且不會與既有法規產生扞格,便借鑒了「特區」(zone)這樣的政策手段。
回顧特區制度發展歷史,早期在1960年代,特區主要是出現在拉丁美洲的後殖民地區以及亞洲的開發中國家,做為加工出口、勞力密集產業的聚集地,並附隨關稅特別措施或是特殊的投資獎勵、較為寬鬆的勞動法規等。
到了1970年代,隨著新興國家產業轉型,出現以高科技產業為主的科技園區。直至近年,由於數位創新技術的高速發展,出現許多需要與現行法規磨合的情況,特區被賦予更多任務。
諸如英國、新加坡及澳洲等國於金融法規上,相繼推行「監理沙盒」(regulatory sandbox)機制,目的在創造免責的實驗性時空(safe zone),供企業進行服務、產品測試,刺激金融科技發展。此後,監理沙盒機制不僅只侷限於金融領域,而擴及於近年熱門的共享經濟議題,或是無人車、無人機、人工智慧等,應用領域愈發多元。
我國立法院亦在2017年12月三讀通過俗稱台灣金融監理沙盒的《金融科技發展與創新實驗條例》,成為繼英國、新加坡、澳洲及香港後,第五個實施金融監理沙盒制度的國家。未來是否將監理沙盒機制推及至其他技術領域,扣連智慧城市的發展浪潮,促進公共服務的智慧化轉型,是當前熱門討論議題。
這種藉由特區進行法規鬆綁,並將新興科技以「試驗」的姿態投入真實的都市日常,乍看之下實為理性與科學的政策手法,然而在實際執行過程中,卻也產生不少尚未完全被理解與闡述的爭議。

爭議一:特區與主權之關係
在特區制度相關的討論當中,「主權」這一維度長期為研究的重心之一。特區由於係政府創造一個特定的時空,將部分國內法豁免或停止適用,因此產生國家權力的展現(實施律法)不均質的現象。
對此,柏克萊大學人類學教授Aihwa Ong就曾以中國、東亞的經濟特區為研究標的,認為特區做為「合法的例外」,國家主權不認為係被切割,反而應被視為國家為達到政經一體化的有效手段,更是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意識形態衝突與融合的前沿。
阿姆斯特丹大學教授Dennis Arnold,針對湄公河流域邊境經濟特區的研究亦表示,經濟特區可以彰顯和擴大國家影響力,而不是成為國家主權的例外。Arnold與Ong分別從不同的分析觀點切入,均認為特區非但不是主權的例外,事實上更是主權的彰顯或政治上的主動選擇。
從法律的觀點來看亦如是。具有法學背景的政治經濟學家Ronen Palan就以離岸金融中心、加工出口區等「離岸」空間為例,認為離岸是一個可以在國家干預相對較少的情況下,進行經濟交易的司法空間,但同時它也是一個受保護的空間。
就Palan的邏輯來看,既然離岸亦是司法得以彰顯(不論寬鬆或嚴格)的空間,國家主權便不算是退讓,反而藉此制度展示了國家的靈活性,成為達成全球化發展與鞏固國家主權的兩全作法。
主權與特區兩者之間看似衝突實則互相成就,而這種關係的形成,以上三位學者都認為與全球化新自由主義有關。特區作為迎合全球市場的治理工具,社會學意義上的主權(或是法學意義上的監管),在不同的空間可以放開或縮緊,對於人的管理也會有不同。由此可窺知主權是變動的、有彈性的。
由此回頭來看現今各國推行的「智慧城市」特區。Palan在30多年前對於未來離岸的預測——離岸與岸上兩種模式會保持衡平狀態,國家和企業之間將不斷進行貓捉老鼠的遊戲,利用新型的離岸設施進行創新——似乎可以得到驗證。
與過去不同的是,如今的監理沙盒制度或是以打造智慧城市為名的特區,添加了「時間」維度,並放鬆了「空間」維度。「特區」未必需要一個實質且固定的物理空間,便可以與全球化資本市場相扣連,透過暫時的法規鬆綁,虛擬貨幣交易、電子商務、平台經濟、大數據與資料分析產業皆可在「發展智慧城市」的大框架底下,盡情演示國家的「主權」。

爭議二:特區與都市化
Orit Halpern等人曾以韓國的松島國際都市為例,提出「試驗田都市主義」(test-bed urbanism)的概念,認為這種以數據為尊或科學理性至上的都市治理手法,將「人」(people)扁平化為「人口」(population),最終這種計算將導致都市發展的失敗。
同樣,都市計畫學者Martin J. Murray從另一個角度切入,批判新自由主義下,特區的發展由私人主導,形成一種「超領土主權」(extraterritorial sovereign)的飛地。另一方面,全球研究學者Jonathan Bach則談到,特區成為「The City of Tomorrow」的具現,充滿對於現代與進步的想像。
如果將這樣的說法,用於探討日本國家戰略特區計畫,會發現許多重合之處。包含為了加速推動自動駕駛以及小型無人機等「近未來技術」,讓申請相關實證計畫的過程更加方便的《國家戰略特別區域法》第37-7條修法,以及期望地方政府提出結合多項先進技術的「超級城市」(スーパーシティ)計畫等。顯示日本國家戰略特區便是日本政府對於未來城市的憧憬與探索。
然而,Halpern、Murray、Bach都談到,新自由主義與現代發展的想像加諸於特區,其結果未必盡如人意,甚至有許多發展陷阱。事實上,過去都市研究所探討的「不動產導向的發展」(Property-led development)模式,如今或許「不動產」可以被「技術、科技」替換,形成另類展演空間,以替城市吸引更多資本投資。
雖然日本國家戰略特區的「超級城市」強調由地方政府提出,且須為包含多項技術應用的整合型規劃,似可避免Murray所擔憂的碎片化與私有化,但由於高新技術本身的寡占性質與高門檻,導致公務機關沒有能力進行規劃並產出計畫書,最終這些計畫依舊由私人企業所主導。
類似的問題於其他的智慧城市發展計畫也逐漸浮現,形成科技公司與公民之間的緊張關係。比如Google母公司Alphabet在加拿大多倫多的水岸新城計畫,於一個人口約5000人的特區導入技術感測器、無人駕駛、智慧電網、數位身分系統等技術,但由於對資料利用的疑慮,導致加拿大公民自由協會(Canadian Civil Liberties Association, CCLA)在2019年就此項目向政府提出法律訴訟,讓Alphabet不得不提出新的資料利用構想。
未來,這些所謂的智慧城市特區,將如何處理或改寫政府、企業與公民之間的關係,可能會是值得深入探索的議題。

|參考資料|
- Bach, J.(2011). Modernity and the urban imagination in economic zones.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28(5), 98-122.
- Halpern, O., LeCavalier, J., Calvillo, N., & Pietsch, W.(2013). Test-bed urbanism. Public Culture, 25(2), 272-306.
- Kitchin, R., Coletta, C., Evans, L., Heaphy, L., & Mac Donncha, D.(2017).Smart cities, urban technocrats, epistemic communities, advocacy coalitions and the ‘last mile’problem. Information Technology, 59(6), 275-284.
- Murray, M. J.(2017). The urbanism of excep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Ong, A. (2006). Neoliberalism as exception: Mutations in citizenship and sovereignty. Duke University Press.
- Palan, R (1998). Trying to Have Your Cake and Eating It: How and Why the State System Has Created Offshore.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42, 6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