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宗潔/同理的極限,理性的侷限——讀《失控的同理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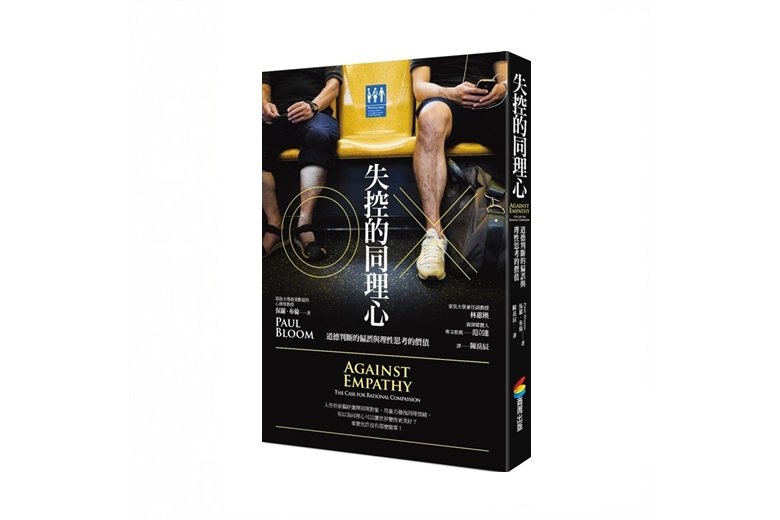
近年來,在推廣動物關懷這條路上,我常強調「無感」是議題難以推動的關鍵,如何讓一般大眾關心你所關心之事,讓更多人對動物他者的遭遇「有感」,進而願意展開行動,始終是運動訴求中核心的訴求與策略之一。
因此,保羅.布倫(Paul Bloom) 以「反對同理心」為全書宗旨的《失控的同理心》一書,確實帶來思維上的一大挑戰。尤其他所謂的同理心,又確實專指「感受你認為別人的感受」此一心理過程,而非更廣義的仁慈、憐憫,或是另一種換位思考的「認知同理」(理解別人想法的同理),於是展卷之前,不免在心中浮現了這個作者在書中反覆辯駁的質疑:如果沒有同理他者感受的能力,關懷與行動如何有可能?
但是,若先拋開是否同意作者立場這個問題,細究全書所批判的同理心失控現象,將會發現其中指陳的種種「同理心過剩」造成的不良影響,非但不是無的放矢,更直指當代社會許多議題在推動時的盲點。
同理心造成「聚光燈效應」
同理心有哪些「副作用」呢?首先,布倫認為,它會造成「聚光燈效應」。全書以2012年發生在康乃狄克州的桑迪胡克小學(Sandy Hook Elementary School)槍擊案開場,這起校園槍擊事件造成二十多人死亡,引發全球震驚,美國前總統歐巴馬在召開記者會時更因此激動哽咽。這類案例通常會被用以強調同理心的重要,以及人與人之間如何透過感同身受的溫暖關懷,試圖對抗生活中及社會上的種種殘酷與不義。然而,布倫卻主張,大眾對桑迪胡克小學校園屠殺事件的回應,反倒凸顯出「同理心的狹隘」。
當同理心宛如聚光燈,照亮少數特殊個案,很容易使得其他需要關注的狀況隱身於背景之中。短期與突然大量湧入的同理心,固然帶來撫慰人心的效果(包括釋出同理心的民眾,能夠從無能為力的心理狀態中解脫,覺得自己有所付出會讓他們比較好過),但當整個社會的聚光燈瞬間集中在單一案例上,反而可能迅速累積並不見得必要的物資。例如大量捐贈的絨毛玩偶堆滿倉庫,讓當地居民不知如何處理,部分善款甚至來自經濟水準較差的地區。換言之,「窮人送錢給富人,只因糾結於同理心」。
另一方面,同理心的聚光燈效應,不只讓善意的流動不成比例與「不見得必要」地流向少數地方,還時常造成「高估當下成本卻低估未來代價」的狀況。例如帶來負面感受的特殊案件,可能會影響民眾看待社會政策的態度,容易因當下的極端案例而全盤否定或支持某些決策,卻未將長期的利弊進行充分考量。更重要的是,聚光燈照向何方,完全取決於提燈的人,因此同理心往往也是一種充滿了個人偏見的選擇。
此外,布倫主張,「我們不可能同理所有人」的這個基本事實,讓同理成為道德照明燈的功能顯得不切實際。他以「觸動警告」的爭議為例,這個在學界引起辯論的概念,是指在教授課程或舉辦演講、研討會之前,先聲明其內容可能觸動某些情緒或歷史傷痛,讓學生與參與者有機會選擇是否出席。支持觸動警告者多半是基於同理心,而反對者則認為這是典型的「同理心正確」,但追求同理心正確不只會造成實際執行上的困難:我們無法預測甚麼樣的課程內容會造成學生情緒波動或傷害,每個人會被觸發的點有無數可能,將討論聚焦於此,或許反而因此忽略更重要的議題。
更重要的是,過度的同理心,很可能會造成同情疲勞,對身心產生不利影響。他以心理學上稱之為「絕對共存」(unmitigated communion)的概念進行說明,所謂絕對共存,是指「過度在乎他人,並將他人需求置於自身需求之上」,共存程度越高,對於其他人的苦難往往會有嚴重的低落反應,並且較難以抽離。在心理上過度同理與共享對方的情感,將會導致快速與過度的耗損,使得關懷和善行難以持久,這確實是許多關懷弱勢議題的行動者常見的「職業風險」之一。

同理心是「複製」式的感同身受?
那麼,如果同理心有這麼多缺點,我們為何還要堅持擁抱它呢?堅持捍衛同理心的價值,是否如布倫所言,是對道德缺乏想像力的結果?但是,這本書並沒有完全說服我從此拋開同理心。因為前述立論的重要前提都在於:憐憫與同理不同,前者是對目標抱持情感而非共享情感,善行與道德,無須在心理上感同身受。布倫用以駁斥同理心作為道德核心的例子,皆由此出發。
他強調:有個小孩被狗嚇哭了,我們可能去抱抱她,這個舉動代表我「關心」她,卻無涉同理心,因為「我沒有感受到她心裡的恐懼」;「我想幫助吃不飽的人所以出錢出力,這和我自己是否曾經長期挨餓也沒有必然關係」;又或者心理實驗中,成人在孩童面前假裝難受,兒童自身不需要有難受的情緒,也會提供關心或協助,例如輕拍、擁抱、開口安慰或是拿玩具過去,「過程中他們自己沒有難受的表現」。他甚至以黑猩猩實驗為例,說明即使是猩猩彼此表達關切時,臉上的表情也只是關心而非難受,換言之,猩猩並不是在「心理上感受了對方的感受」。
以此來框限同理心的「感同身受」,似乎過於拘泥於「感同身受的感受」,將其視為完全對等的情緒或行為。儘管我們確實無須將同理心的概念無限上綱,那將會過於寬泛而無法討論,但即使是依據作者所提出的分類框架——「認知同理」與「情感同理」,我認為也忽略了情感同理不見得是那麼「複製」式的感同身受,而可以是更廣義的,理解他者情感的同理。也就是說,我不需要和被狗嚇哭的孩子一樣感受到驚嚇,但因為我了解恐懼之為物,因此我能同理她當下恐懼的情感,那仍然可以是同理,而不見得要是憐憫或關心。
當然,本文或該書的讀者或會質疑:如果我們期待的就是一個更多善行、更道德、更公平的世界,用同理心、憐憫或其他詞彙來指涉我們所渴望的道德樣貌,是否有那麼大的差別?這些討論最後是否會落入「名詞釋義」式的糾結,而偏離了討論重點?事實不然。無論如何,布倫對同理心的顧慮與各種負面效應的分析,仍不失為重要的提醒。尤其當同理心很容易因為聚焦於少數個案而過度氾濫的當代社會,失控的同理心可能造成的反噬,確實不得不謹慎以對。
不過,我對於布倫一再強調「憐憫與關懷不需要在心理上映照出對方感受,也不需要同理心為基礎,因此更適合做為道德指標」的立場,仍不覺得是個足夠充分的論述。他主張理性又更優於憐憫的立論,也可能導向另一種理性迷思的陷阱——過度強調科學理性而貶抑情感的價值觀。畢竟若缺乏感受與想像他者感受之能力,憐憫將如何產生,書中始終未提供真正有力的說法,因此我更傾向於心理學界的另一種態度,亦即憐憫與同理有其交集之處,理性的思辨也未必要排除同理的感受。
至少,在討論動物議題時,無論呼籲憐憫也好、以布倫所支持的效益主義式的思辨進行評估也好,如果少了想像他者感受之可能,憐憫與善行或許從一開始就將失去得以萌生的支點。而且,無論同理、憐憫或理性,背後的行為準則說穿了其實殊途同歸:別失控就好。

- 文:黃宗潔。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系學士、國文學系碩、博士。長期關心動物議題,喜歡讀字甚過寫字的雜食性閱讀動物。著有《牠鄉何處?城市‧動物與文學》、《生命倫理的建構》、《當代台灣文學的家族書寫——以認同為中心的探討》。現任國立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副教授。
- 更多動物當代思潮:Web|FB
▼ 鳴人堂贈書活動,留言分享就有機會獲得作者黃宗潔的最新出版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