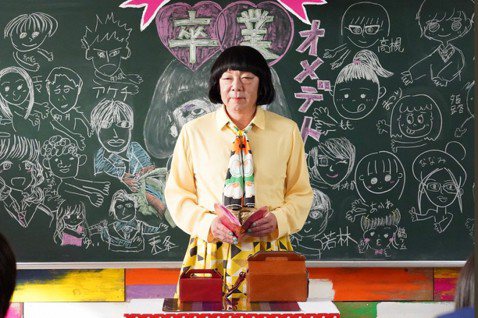跨性別與免術換證(上):誰是「真女人」?跨與順性別女性的虛假對立

2019年,《哈利波特》的作者羅琳(J.K. Rowling)由於在推特上聲援英國一位因為恐跨(transphobia)言論與行為而遭解雇的女性而引發爭議,批評者質疑羅琳同意這種恐跨情結,甚至是一位「拒絕跨性別的基進女性主義者」(trans-exclusive radical feminist, TERF)。羅琳隨後在2020年時又再次因為一則推特發文引發同樣爭議,她頓時在社群網站上成為「恐跨者」(transphobe)的代表人物之一,引發跨性別社群以及與她抱持類似看法的支持者間的激烈論戰,羅琳本人甚至因此收到各種辱罵與威脅。
‘People who menstruate.’ I’m sure there used to be a word for those people. Someone help me out. Wumben? Wimpund? Woomud?
— J.K. Rowling (@jk_rowling) June 6, 2020
Opinion: Creating a more equal post-COVID-19 world for people who menstruate https://t.co/cVpZxG7gaA
羅琳後來在自己的部落格上發表長文,說明她對於跨性別運動的疑慮,許多TERF——她們通常偏好稱呼自己的立場為「性別批判論」(gender critical)——亦抱持著同樣的看法。在理論上,她們認順性別——即出生時的被指定生理性別與性別認同一致——女性的身體構成她們獨特的生命經驗,因此是構成「女性身分」(womanhood)的根本關鍵,相對地,跨性別女性是以男性身體出生長大,因此他們得以在成長過程中,獲得屬於男性的紅利和好處。
在政治上,抱持性別批判立場的人擔憂,考量到跨性別與順性別女性之間不同的社會經驗,如果不去區分跨性別和順性別女性的差異,進而無條件地把跨性別女性視為「女人」,會損害女人作為一個政治群體的合理性,以及順性別女性在其中的話語權。而在實務上,他們經常主張,當今的跨性別運動太過「激進」,會侵犯到順性別女性與兒童的安全和健康1。
針對後者,性別批判論者經常提出的疑慮有二,一是激進的跨性別運動會「鼓勵」越來越多的青少年成為跨性別者,透過服用荷爾蒙或甚至是手術的方式改變自身身體2。二是,他們認為,當跨性別者被允許根據自身性別認同使用二元性別空間時——也就是跨性別女性可以使用女廁、女性更衣室等依照性別做出區隔的場所和空間,會壓縮順性別女性原本就不多的自由空間,使她們感到不自在與不安。根據他們的主張,這甚至會開啟安全漏洞,因為生理男性可以藉此「假扮」成跨性別女性,進入女性空間,侵害女性與兒童。
其中,經常和此類恐懼連袂出現、並將其合理化的討論之一,便是跨性別者的證件更換條件,亦即跨性別者在哪樣的條件之下,得以將自己身分證件上所註記的性別更改為符合自身認同的類別3。例如,當初羅琳在自己的長文中便提到,她對於英國政府計畫修法放寬跨性別者更改身分證件性別註記條件一事感到非常擔憂。

有「女人的身體」才是真女人?
無獨有偶地,同樣的討論近日也在台灣出現。根據台灣現行法規,跨性別者如果想要變更身分證件上的性別登記,必須滿足兩項條件:持有兩位精神科醫師評估鑑定之診斷書,並完成摘除性器官之性別置換手術。然而,由於性別置換手術等同於剝奪個人的生育能力,因此被視為侵害性極大的醫療程序,故全球跨性別者皆企圖爭取更自由地轉換性別登記之制度,至今也已有數個國家允許跨性別者可以不必經過醫療診斷與處置,就得以變更性別4。
台灣政府單位雖曾就性別登記制度提出政策建議,但一直都只處於研議階段,未能在法制化上有所進展。因此,有兩位跨性別者就因為認為台灣的性別變更規定太過嚴苛,分別提出訴訟,主張強迫手術的換證規定是對跨性別者人身完整性的侵害,政府機關應該放寬規定。其中第一位當事人小E獲判勝訴,已經成功更改性別登記;至於第二位當事人吳宇萱的案件,法院目前裁定暫停訴訟,將聲請釋憲。此外,協助兩位當事人提出訴訟的民間團體亦同步發起連署,爭取社會對免術換證之支持。
在父權社會的二元性別結構5下,我們每個人都只能被放在其中一個框架之下,並被要求要符合該性別框架下的各種氣質表現與行為想像。由於跨性別者自身的性別認同並不符合他們在出生時因為生理器官而受指定的性別,因此在二元性別框架下,經常感到難以歸屬、不合時宜。因為性別不只是生理特徵(或者說,性器官)而已,而是一套社會性的行為展演過程,但當跨性別者根據自身性別認同參與社會時,人們卻可能因為他們的性別登記——也就是根據被指定性別、但不符合當事人認同的判斷——而抗拒、排斥他們的存在。
變更性別登記之意義便在於此。已有許多研究指出,讓跨性別者持有和自身性別認同相符之證件,對於他們的身心健康和福祉有著許多益處。簡單地說,在實務上,這可以減少跨性別者在與體制互動時可能遭遇到的不安、刁難和其他問題,也更有利於他們取得如醫療、工作等各項資源。在心理上,這得以讓跨性別者感到自己被社會看見,他們的存在受到認可,進而減少各種心理上的焦慮、不安,也能夠更好地參與、融入社會。
如前所述,考量到性別置換手術對個人身體完整性的侵害性極大,因此才會有「免術換證」之倡議。然而,此議題卻在台灣社會掀起許多爭議,反對者多持有和性別批判論者類似的論點,認為一旦讓跨性別者自由變更性別登記,並得以根據性別認同進入、使用特定空間,會使順性別女性在這些地方不再感到自在與安全,甚至遭到實質侵害。

雙重「背叛」的跨性別女性
本文並不打算就法律與政策細節進行討論,包括免術換證之實際執行、可能出現的問題,以及可以採取的配套措施等,而是想要拉遠一些,著重於相關討論中各類言論所透漏之意涵。在性別批判論者的主張中,我們經常可以察覺到「恐懼」這個主軸,包括對跨性別者是否「真實」的疑慮、對自身安全的不放心,以及擔憂自己作為女性的政治權益可能被瓜分,等等。然而,這些恐懼究竟從何而來?為什麼跨性別女性會對順性別女性造成如此大的威脅感?而順性別女性和跨性別女性之間,真的只存在對立嗎?
父權社會以生理性別為基礎,將世界上的人口分為男女兩類,並遵循著「崇陽貶陰」的原則,將男性置於支配者的位置,得以掌握權力與資源。然而,生理上的「男人」僅僅是成為支配者的條件之一。要成為一個父權社會裡的合格「男性」,男人還必須要符合這個體制中針對男性的性別角色規定,也就是展演、執行、崇拜陽剛氣質,透過實踐這些所謂的「男子氣概」,來證明自己確實屬於男性社群。因此,成功表現出這些陽剛特質的男性會受到讚揚,相反地,未能或不願意服從這些性別規範的男人就無法成為一個社會意義上的男性,且會因此遭到貶低、攻擊,甚至排擠與驅逐。
從這個角度來看,出生時帶有男性性器官、但認同為女性的跨性別者,儘管符合某種天生條件,讓她們可以有機會透過實踐陽剛氣質,來爭取父權社會的認可,但我們卻很難說,她們確實因為自己的男性性器官而收穫了任何紅利。事實上,她們反而可能遭遇到雙重的審查與譴責,而處於更弱勢的處境。
在父權社會的眼光中,跨性別女性一方面「背叛」了自身的生理性別,未能扮演一個合格男性理當扮演之角色、服從相應之規範,因此必須受懲罰。另一方面,跨性別女性的陰柔表現也被視為不正當,因為她們不擁有「天然的」女性性器官,卻試圖「成為」女性,這挑戰了父權社會以生理性別為分類並予以相對規範的原則。
因此,對於父權社會來說,跨性別女性代表了雙重的不合格與背叛,她們也因此必須承受加倍的貶抑與打壓。由此看來,跨性別女性和順性別女性絕非對立之關係,因為這兩個社群都面臨同樣的父權性別規範,並在崇陽貶陰的邏輯下,被放置於附屬者的位置上,遭到約束與打壓。
父權社會所訂下的這一套陰性規範以看似不同卻同源的方式,同時規範著順性別與跨性別女性,前者會因為不夠順服而被批評是「不合格」的女性,後者則受到這一套邏輯的檢查和監管,被貶低成「不真實」的女人。事實上,當跨性別女性因為不被承認為「真女人」而遭遇排擠,這也等同於再次把特定的陰柔氣質、角色任務與規範,強加到順性別女性的身上,使其成為順性別女性不能逃離也不該逃離的專屬要求,而失去了其他性別展演的可能。
▍下篇:

- 針對這些常見的論點,跨性別社群與學者也已提出許多反駁論述,例如可參考這篇文章。
- 與此同時,他們也會主張,在青春期曾感受到「性別不安」的人,大多數會在日後自然而然地「恢復」;換言之,性別批判論者企圖暗示,假如這些人在青春期時因為感到不安而選擇跨性,可能會在日後後悔。但此論點也已遭跨性別社群用相關證據反駁。
- 在此要說明的是,事實上這兩件事情並沒有(絕對的)關係。早在證件更換條件討論出現許久前,跨性別就一直存在於我們的社會中,也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各類性別二元空間。當跨性別者的外表足夠符合傳統性別想像(passing)時,他們在進入這些空間時也不會引發太多注意。因此,證件更換其實從來不是跨性別者使用特定空間的必要要件,將兩件事情放在一起討論,其實反而造成混淆。
- 例如歐盟共有八個國家廢除了性別變更的醫學診斷條件,包括:希臘、法國、比利時、丹麥、愛爾蘭、盧森堡、馬爾他、葡萄牙,而後六者更讓跨性別者可以根據自我決定(self-determination)來變更性別。在歐盟以外,阿根廷有著全球最完善的跨性別權益法規,其中包括跨性別者不需要接受任何醫學處置(手術或荷爾蒙療法)或診斷,就可自由變更性別。
- 儘管有越來越多國家承認第三性別的存在,但在大多數的社會裡,二元性別的想像仍是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