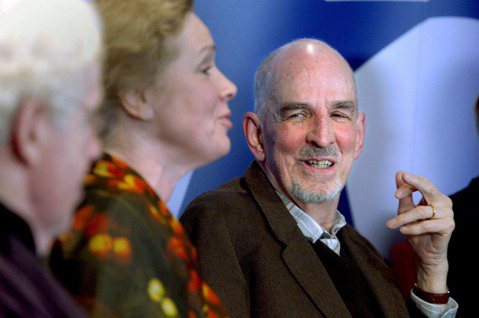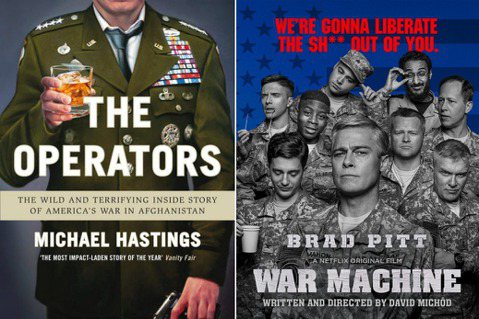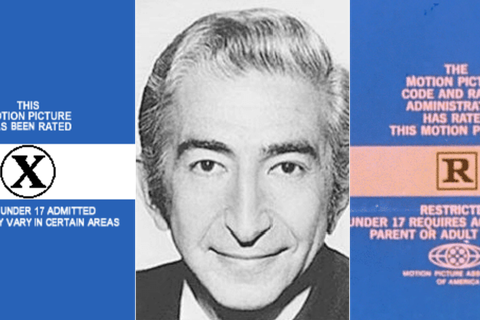新銳導演第一站:北藝大「關渡電影節」有什麼看頭?

今年稍早曾撰寫〈新銳電影灘頭堡金穗獎,為何已成死水一灘〉一文,針對表彰國內短片的金穗獎提出了一些見解。其中一項惹人議論的,便是點出「評審高齡化」的問題,還因此被扣上「年齡歧視」的帽子。但我並不認為年長者不能擔任評審,反而有在文中提出「年長的、資深的電影工作者在評選時提供專業意見也有其必要」。而評審名單也要均衡,因為「唯有納入更多年輕的創作者、評論者,汲取新生代觀點,方才能與新時代接軌」。
2021年的金穗獎確定改由金馬執委會負責主辦,屆時是否會有一些重大變革,或者在評審團引入新世代觀點,暫且不知。不過長期以來,其實有一個影展完全是以「年輕視角」來進行策劃的,它是位於台北藝術大學(以下簡稱北藝大)校區內的「關渡電影節」。關渡電影節展映的作品以學生短片為主,可惜難以吸引主流影展迷(即鎖定金馬、台北電影節的觀眾)的目光,加上地點又位處關渡的山區之中,對於校外人士而言,交通確實不太便利,因此許多影迷大概只聞其名,而不知它在策劃上的種種特色。
關渡電影節至今已舉辦達12屆,是國內少數全由學生自主策劃、選片的影展活動。一年下來,我們可以看到許多「大人」辦的影展,因此由學生自己辦的影展,顯得尤其可貴。關渡電影節在選片觀點上,也有其不群之處:由於可選映的作品超過30部,更使之能廣納各種不同類型的作品,幾乎沒有包袱的存在,只要是學生製片就行。


學生製片策展,低成本也有好作品
有些作品令人懷疑走出關渡電影節之後,是否還有機會獲得展映的舞台。例如來自北藝大、由黃若賓執導的《百齡橋檔案》(2020)採用偽紀錄片(pseudo-documentary)的形式創作,片長僅僅七分鐘,故事描述一名女生意外獲得了高強的武術能力,輕鬆就能將對自己暴力相向的男友震出幾十公尺外。
故事集結手機錄影、監視器畫面的素材,又與超能力有關,令人不禁聯想到好萊塢電影《超能失控》(Chronicle, 2012)。或許原創性不高,但也不能不否認,導演想達成的目的,應該也都做到了。換個角度來看,與其拘泥於高品質的影像創作,若有國內創作者願意嘗試低成本、低配置的偽紀錄片形式,往特定的類型(如鬼片)發展,或有在市場突圍的可能性。雖本片只是一部習作,其凸顯出的某種潛力與可能性,引人深思。
來自崑山科技大學、許志維執導的《月光捕手》(2020)也是一例。故事描述一對孤獨男女在傳說中的世界末日前夕相遇,兩人遊蕩在街頭、地下道,談論活著的意義。對於認真要追究角色動機、母題的觀眾而言,大概無法為如此鬆散的情節感到共鳴,只能大嘆:「這兩個魯蛇到底在幹嘛?」
但如果撇除學院式的檢視,便會察覺導演在場面調度與敘事節奏上的掌握,其實浪漫自如。兩位演員劉主平與潘綱大在略顯的空洞劇本之中,也演出了角色的靈性。只是這類「廢青作品」雖然向來能在年輕族群之間贏得追捧,但要進軍獎項,卻往往難以獲得太正面的評價。


片長過長的短片,野心還可以更大
有一些作品則因為其他因素,難以在其他影展與電影獎找到容身之地,不過問題並非題材,而是片長過長的問題。以台北電影獎為例,目前僅收片長少於30分鐘的作品,有些國際影展則可能在20分鐘,甚至15分鐘以內。哪怕拍出來的作品再傑出,卻缺乏放映的平台,似乎也成了白費功夫。
來自世新大學、由詹承廷執導的《青春劇烈物語》(2020)如是。故事描述一所高中的學期末,熱音社的四人組在面臨幹部交接前夕,關係產生了一些微妙的變化。鼓手林翰在社團之中並非最受歡迎的一號人物,但自認對社團投注更多熱情的他,希望能當上社長。不過,獲得「刮鬍泡」慶生待遇(在高中的世界,唯有萬人迷才能獲得這類整人式的慶生)的建甫,才是熱門人選,因為他的「型」更有社長相——除了看來更俊帥、性格外放、女人緣也更好。
不過作品無關於這群人對幹部職位的競逐,反而是編導透過這個即將發生的事件,讓角色去環視他們對自己以及對他人的認知。例如不想角逐社長的佑賢,看來像是不願爭奪目光,但片中一個廣告看板的線索,卻提示了他在原生家庭的處境,暗示著他在社交時對自己的定位。
作品不是那種揮灑汗水的矯情青春紀事,步調異常沉穩,剪接與轉場皆俐落得當,一眾演員的表現也恰如其分。導演在場面調度的才華,以及對學生心理世界的探索,令人聯想到吉田大八所執導的《聽說桐島退社了》(The Kirishima Thing, 2012)。只可惜片長超過30分鐘,未來參與影展難免受阻。以往我會稱這樣的作品「野心太大」,但我卻感覺導演的功力顯而易見,野心或許還可以更大。

具備「再現舊時代」的製片能力
同樣片長過長,但企圖心令人大開眼界的,則是來自台灣藝術大學(以下簡稱台藝大)、由張荷澤執導的《永恆之火》(2020)。該片混合劇情片與訪談形式,描述1970年代一群想要逃離暴政的法外之徒,試圖發動的逃亡行動。全片採取黑白攝影,將國民黨的刑求暴行以戲劇方式融入行動之中,反覆重演,使得作品徘徊在現實與虛構的界線之間。其創造的戲劇氛圍令人聯想到侯孝賢的《好男好女》(1995),至於形式部分則有王又平、李佳泓、黃奕捷與廖烜榛聯合執導的《錢江衍派》(2016)之風。
導演擅於利用光源來調度場面,並妥善運用有限的狹小空間,使得作品維持在一種高度的張力之下。簡言之,觀眾沒辦法從導演創造的空間裡,探出去呼吸到新鮮的空氣,那種使人窒息的壓抑感,是導演透過攝影等部門所共同創造的。就任何角度來看,《永恆之火》都是一個完美的示範,藉由有限的場景,一樣能讓觀眾有穿梭時空之感,顯見時代的氛圍未必只能透過布景來創造。
而該片也是本屆影展極少數不以當代為背景的題材,對極權時代的碰觸,延續了去年北藝大作品、林治文執導的《母親的呼喚》(2019)。同樣在去年以白色恐怖為主題、獲得社會高度關注、也在票房與獎項上有所斬獲的劇情長片《返校》(2019),這部學生作品的呼應堪稱是「不約而同」。由於製作資金考量以及題材處理的能力有限,過去很難期待讓學生去還原、再現舊時代,但《永恆之火》的表現,已經證明了台灣學生製片發展已經具備一定的成熟度。
新銳導演走向專業導演的第一站
本屆關渡電影節尚有許多可觀之作,除了上述提到的作品,動畫片《Blanket Talk》(2019)的短小精煉,通篇童言童語,結局令人驚異而動容。紀錄片《咪咪貓的奇幻之旅》(2020)則紀錄了沿途畫著咪咪貓的中年大叔,導演技法平實,卻深入了城市的心坎。短片《小傑》(2019)出奇地講述了一個關於精神亂倫的禁忌故事,撇開道德角度不看,導演確實牢牢捕捉住了人物釋放出情慾訊息的片刻。
許多作品都是在畢展之後緊接著在此首映,換言之,關渡電影節可能是某些新銳導演走向專業導演生涯的第一站。若想要知道當下學生對影像的執著與追求何在,或者預知台灣未來新銳之作的選材、形式走向,從關渡電影節切入,無疑是最好的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