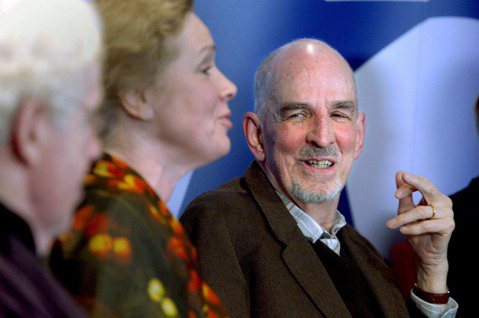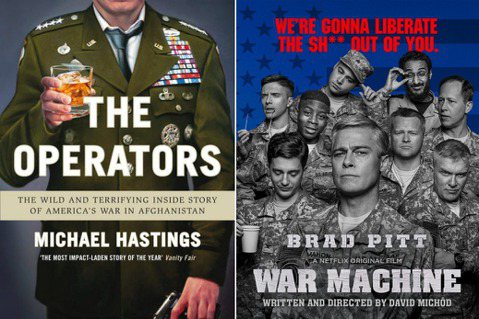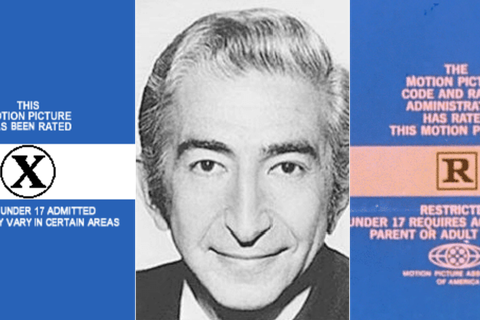當事人該為「真實事件」改編電影背書?談《無聲》的原型爭議

近日,作家林立青於臉書上公開發言,指出其對電影《無聲》產生一些質疑,原因是他認為「製作團隊沒有跟人本(教育基金會)及陳昭如合作」。之所以會有這樣的說法,在於他認為作家陳昭如是一位專門在台灣撰寫校園性侵題材的作家,若要在台灣談論相關題材,陳昭如是不可迴避的重要人物。
但林立青也說:「身邊的影評人朋友們越是讚嘆不已,我越是感到不安,雖然說新聞事實沒有著作權,但是到底有沒有跟人本及陳昭如合作,一直是我看到《無聲》時的陰影。」我沒有看過陳昭如的著作,也想了解編導到底參考了陳昭如著作的多少個案、又從中參考了多少內容。不過林立青卻也說,他至今沒有看過《無聲》。
《無聲》掠奪他人心血?
之所以這件事會成為一個爭議,在於有部分網路文章指出,《無聲》的故事原型改編自陳昭如的著作《沉默:台灣某特教學校集體性侵事件》。該書籍內容是關於一所特教學校裡的學生性侵事件始末:該所學校發生了上百起學生之間的性侵害或性騷擾案件,而老師卻置身事外,縱容狀況失控。
若要說《無聲》的編劇柯貞年與林品君沒有參考過這本書,大概沒有人會相信。不過本片目前並非入圍金馬獎的改編劇本,而是原著劇本,已說明片方並沒有認定故事直接改編自任何著作。
但由此能說明《無聲》就是掠奪了陳昭如的心血嗎?
或許要先釐清的是,《無聲》指涉的事件如前段所述,確實存在原型,而事件本身不是虛構的,所以絕不會存在任何抄襲的疑慮。事實上,如果今天每個拍攝關於社會事件的電影,都得獲得撰寫報導的相關記者或作家的授權,那麼很多電影恐怕不會有機會問世。
此外,當編導去處理這類事件時,是否非得要去向對該事件著力最深的人致敬,或按上一個顧問角色,不啻是一個學問,更沒有一個標準的答案。因為涉入事件越深的人,往往都會對戲劇改編存在疑慮,而非影視界人士多半也無法理解現實跟戲劇效果的差異。真要讓見證事實的相關人士為電影改編背書,可能才會是創作者災難的開始。
如果完全照著事實拍、怕造成冒犯,可能會讓電影顯得太八股、太溫;如果不理會這些「顧問」,搞到最後撕破臉了,反而為電影徒增醜聞。


是致意,還是消費?
事實上,大家喜愛的諸多真實事件改編電影,都存在很大程度的「戲劇化」成分。榮獲奧斯卡獎最佳影片、描述伊朗人質危機的《亞果出任務》(Argo, 2012)可能是近年最代表性的例子。如果這部片完全照事實來拍,恐怕未必如此傑出,因為真實往往是枯燥而冗長的。要符合電影的格律,便得適度進行加工和調整,這是全世界的編劇與導演都明白的道理。
當然,如果本片編導其實有接觸過作家陳昭如本人,但卻在沒有跟對方協議或事先知會的情況下,沒有在演職員表上向她致意,造成陳覺得不舒服,那又是另一回事,應該面臨責難。不過如果編導沒有與之合作,卻還要把人家的名字寫上去致意,或者公開對人家的作品表達太多謝意,無疑也可能成了一種消費,造成人家的麻煩。
萬一這些個案與他們的家屬以為自己被利用,因此跑來怪罪陳昭如怎麼辦?林立青一方面說他開心有影像創作者重視這個題材,卻又要求創作者拍攝這個題材時非得要跟相關單位、陳昭如和第一線輔導員合作,還指出受害者可能不希望導演這樣詮釋他們。
殊不知如果片方真的關照了所有人,《無聲》要不是拍不出來,就是會被拍成一部什麼點都戳不到的片。

淡化處理,或許才適切
截至目前,我沒有發現創作團隊或發行團隊有公開發文指出電影是在影射什麼特定事件、或者點名陳昭如本人。這樣的淡化處理,其實很適切。至於意見領袖、影評人或各路網友自己要連結真實事件與戲劇,更是無可厚非。大家都有揣測或聯想的自由,這些延伸討論,對於正義與真相的追求都很有幫助。
台灣這片土地有數不盡的故事,但是從真實事件衍生出影視改編的作品不多。因為許多創作者投入改編之後,立刻就會發現顧慮所在。有些台灣導演偏偏又擔心得罪人,太尊重事件原型人物的看法,因此往往拍出一些不痛不癢的片(劇情片與紀錄片皆然)。而我完全沒有在《無聲》這部作品看到類似的包袱。
說到這,大家知道去年的國片《幻術》嗎?這是一部讓演員全掛上政治人物實名上陣的奇片,劇情影射前總統李登輝是319槍擊案幕後黑手。先不論劇情與現實的差異,該片編導如果要尊重每一個事件當事人的想法,這部片根本不用拍了。而李登輝本人或他的發言人當初對這部電影不置一詞,一方面可能是不想為這部片造勢,另一方面如果貿然發表什麼意見,也可能會不慎涉及干涉創作自由的責難。
小結
無論是《幻術》也好、《無聲》也好,這些名義上並非改編特定著作,而是直接從真實當中取材拍攝的作品,都不該面對這樣的責難。這種批評,對於未來台灣的影視創作風氣是很大的傷害。如果這些批評成立,以後誰敢還去拍攝反映社會現實的題材?
一部電影能帶出種種針對社會公義的議論,從劇情還能延伸出對於原型案件本身的探討,已經證明了它的價值。比起為《無聲》扣上不知感謝的帽子,透過這樣的熱潮繼續推動更多變革(如法律咎責抑或制度修正等),無疑更有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