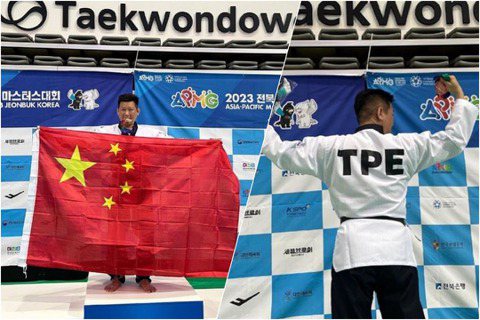來自蘇格蘭高地的格子呢軍團:足球文化的狂歡與政治交融

本(6)月2日,延宕近兩個月的世界盃歐洲區附加賽蘇格蘭與烏克蘭一戰,全場近五萬名的足球迷見證下於格拉斯哥漢普敦球場(Hampden Park)順利完賽,終場烏克蘭以三比一挺進半決賽。然而,早在終場哨聲響起前,大多數蘇格蘭球迷就在90+5分鐘烏克蘭前鋒阿提姆・多夫比克踢進終場前最後一顆球時,已起身轉向出口,包括那位坐在身旁穿著蘇格蘭足球隊服,手持烏克蘭與蘇格蘭國旗的主場球迷。
只見他迅速將蘇格蘭國旗收起,一同沒入離場群眾中。走向出口途中,不少主場球迷嘴中吐出「遺憾」與「丟臉」二字,控訴著蘇格蘭國家隊整場荒腔走板的表現,落寞離場的身影們,與背後興喜的烏克蘭球迷形成強烈對比。
社群媒體上,排山倒海慶賀烏克蘭贏球的訊息,都再再提醒著我們,這場賽事不僅僅是場世界盃資格賽,而是烏克蘭受俄羅斯入侵以降,再次於足球場上得來不易的勝利。就連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都盛讚這兩小時的喜悅,已是不大習慣的感受。
沒錯,我們本應將眼目望向賽事與勝負之外的社會意義,尤其不該忽視烏克蘭是在何等艱困的狀況下,成功完成這項賽事。同樣地,我們也該理解場內那些主場蘇格蘭球迷,如何參與這場令他們大失所望的賽事,以及背後的社會意義。本文是筆者當日參與現場賽事,針對蘇格蘭球迷的現場觀察與反思。

格子呢軍團、狂歡派對、與文化儀式
賽事哨聲前五個鐘頭,漢普敦球場雖未開放入場,但格拉斯哥隨處可見三五成群身穿蘇格蘭國家隊服,披著蘇格蘭國旗或蘇格蘭皇家徽章旗幟的熱血球迷,或是漫步在街上,或是等待接駁公車前往球場,或是剛走出店家。
只見這群被稱為格子呢軍團(Tartan Army)的死忠蘇格蘭國家隊球迷,他們高舉雙手,恣意穿行道路,接著放聲齊唱〈我們來了〉(We’ll be coming)、〈超級約翰・麥金〉(Super John McGinn)、以及〈沒有蘇格蘭,就沒有派對〉(No Scotland No Party)等足球歌謠(chants),整座格拉斯哥城市彷彿就是他們的派對主場。
蘇格蘭運動社會學家理查・朱利亞諾蒂(Richard Giulianotti)認為格子呢軍團作為國家社會認同的集合體,是超越蘇格蘭社會內部長期的族裔(蘇格蘭與愛爾蘭)、宗教(新教與天主教)、與階級(工人與資產階級)衝突的球迷群體,它衍生的自律行徑與與惡名昭彰的英格蘭足球流氓製造暴力、混亂等社會對立行為截然不同,扮演向外宣傳蘇格蘭足球傳統與文化的形象大使,而後被媒體及足球協會再現為賽事中的節慶狂歡者。
「格子呢軍團的根本精神,就是反足球流氓行為。」——一位蘇格蘭國家足球隊球迷告訴筆者。
從格拉斯哥街頭,這群軍團成員們熱情著唱著歌謠,帶動身旁群眾氣氛,再將這股熱情帶上雙層公車,高昂的歌聲伴隨踩踏的地板聲,一路唱進漢普敦球場,最後與球場內的格子呢軍團合流齊唱。這些過程,對蘇格蘭球迷而言,不僅是狂歡派對爾爾,更是跨越各種社會藩籬的文化儀式。

響應和平、足球的愛、與蘇格蘭政治
走進漢普敦球場,兩座偌大的電子螢幕分別以英語及烏克蘭語寫上「和平」(PEACE—МИР),象徵著蘇格蘭與烏克蘭足球協會共同以足球倡議和平的決心。不禁令人好奇,這場以「和平」為基調的世界盃資格賽附加賽,會如何影響雙方球迷的反應與賽事氛圍。
當雙方球隊進場時刻來臨,披著國旗入場的烏克蘭國家隊率先受到全場五萬球迷站立掌聲歡迎,聲勢絕不遜於後者進場的地主隊蘇格蘭。不過,當哨聲響起時,雙方球迷正式歸位,時而替自家球隊助威吶喊、時而為裁判判決不公抱不平,時而互譙對手踢法過於野蠻。原先以為的以球會友,從來就只是筆者自己浪漫的想像。

或許,正是出於對足球的尊重與熱愛,才不讓這場賽事被道德綁架,失去它原先的重要性。正如蘇格蘭隊長安迪・羅伯森(Andy Robertson)賽前受訪表示「真的,我們都十分同情烏克蘭的狀況,我也相信蘇格蘭足球協會與人民都願意做烏克蘭的後盾,但是,在足球場上的90到120分鐘,我們必須與這些情緒切割。因為,我們要前進世界盃,我們就得預備好烏克蘭到來的挑戰與情緒。」
三十年前,當蘇格蘭民族黨前副黨魁吉姆・西拉爾斯(Jim Sillars)在1992年國會選舉敗走後,諷刺蘇格蘭人的愛國主義僅限於漢普敦球場內的90分鐘正賽裡。誰又能料到蘇格蘭接下來的三十年,足球認同不單只是族裔與宗教間矛盾衝突,也是探究蘇格蘭人民在獨立、脫歐議題傾向的討論介面。
運動政治學者史都華・惠格漢(Stuart Whigham)、約翰・凱利(John Kelly)、與艾倫・拜納(Alan Bainer)曾研究格拉斯哥流浪者(Rangers)與賽爾提克(Celtics)隊的支持者在2014年蘇格蘭獨立公投時的政治立場,發現傳統的政治認同分野,諸如族裔、宗教矛盾,已逐漸被社會經濟、意識形態、與政治變遷所鬆動。
在蘇格蘭,足球從來就是高度政治化的運動,球迷的情緒反應更是複雜的社會認同建構而成,更甭提他們對公共議題的意識形態與政治傾向的形成。

形象大使、漢普敦球場、與賽事外部性
格子呢軍團被媒體塑造成國際賽事的形象大使,也絕非完美的群體。總有少部分球迷為了己利,連帶危害到整體球迷的社會形象。例如:攜帶酒精類飲品入場即是一項常見的違規行為。賽事開始前半小時,漢普敦球場外早已擠滿入場的觀眾,各檢票口更是大排長龍,但總有少數球迷在檢票口前約三十公尺前聚集,看似在等待人潮褪去,再行前往檢票口完成安檢程序入場。
事實上,他們正想盡辦法將手上的隨身酒瓶藏匿在私密處,再夾帶偷渡進場享用。運氣好的球迷,躲過隨機抽檢的命運,順利進場享用;反之,則當場被安檢沒收,自行丟進垃圾桶,鎩羽而歸。
更難以啟齒的莫過於球迷在格拉斯哥市區至漢普敦球場路途中隨處小解,即便蘇格蘭政府早於1982年針對隨地小便祭出最高五百磅的罰緩,2004年甚至將其列入反社會行為法中,但令人不解的是,2022年格拉斯哥隨地小便的案例仍占全蘇格蘭四分之一,格拉斯哥記者卡特歐娜・史都華(Catriona Stewart)認為即便去年隨地小便的通報案件僅剩228件,但根本問題可能在於2008年以後,蘇格蘭政府為降低公共支出,關閉將近兩百處公共廁所,就連現今格拉斯哥皇后街車站廁所,現今仍需付費50便士(約台幣二十元)才可使用。

漢普敦球場賽事的外部性還不只如此,當地社區居民抱怨每當漢普敦球場舉辦賽事,他們都得忍受沒有停車空間、滿地的垃圾、以及半夜不知名人士集體闖入私人土地小解等困擾。甚至,若有社區居民想要勸阻,可能還有人身安全疑慮。這些社區外部性問題,也讓格拉斯哥警方在本月15日蘇格蘭與亞美尼亞的歐洲國家聯賽前一週,發布一則「在地植物不需澆水」的推特文,勸導球迷尊重當地社區。但該片推特文觸及率之低,令人質疑其勸導的實際效果。
來自高地,一個熱愛足球的軍團
無論勝敗,無關內容,蘇格蘭與烏克蘭一戰絕對是深具意義的一場足球賽。它振奮了烏克蘭人民的心,為世界帶來正向的消息。反之,輸家蘇格蘭,雖受到大部分網路鄉民的訕笑,甚至來自主場球迷的噓聲,但是,仍有幾位死忠球迷和筆者說:「下個四年,我們會有機會的。」
筆者希望讀者能透過本文介紹格子呢軍團的行為舉止,就足以讓我們知曉,大英帝國除了熟知的英格蘭足球論述,尚有你我較不熟悉的蘇格蘭足球故事。當然,一場賽事的觀察必然偏頗,筆者希望未來有更多機會親身參與更多蘇格蘭足球聯賽、國家隊的賽事,與更多格子呢軍團對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