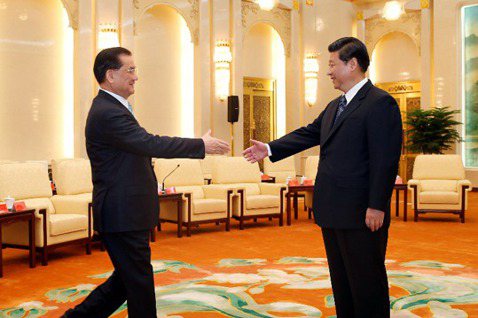她從海上來(下):語言,一道看不見的海洋屏障

▍前情提要
在上一篇〈經濟、空間與性別鑄成的失語困境〉中,我試圖以「經濟」、「空間的配置」和「性別」幾個面向來討論移工與雇主間的權力不對等,是如何在事前升高移工成為性暴力受害者的風險,而事後又如何增加了司法救濟、證據保存的困難。若上一篇討論的是「失語」的困境,是心有所想卻無處可發,那麼這一篇的重點將置放於,受到性暴力的移工突破層層限制,決定「發聲」,此際她們又將遭遇怎樣的疑難。
語言隔閡與通譯的不足
經濟的弱勢,擔憂失去工作,讓移工有苦難言;空間權利的弱勢,增加移工受性暴力的風險,也因空間上的隔絕使證據保存不易。此外,構成受性暴力移工的多重弱勢的處境,尚有語言。語言的隔閡以及現形通譯制度的不足,再一次使移工沈入更巨大、更黑暗的失語泥沼。
於此,受訪的NGO工作者、檢察官與法官都坦承,在法庭活動中,無論文字或語言都用中文完成,對臺灣人來說,法律文字普遍費解,法庭上的肅穆與莊嚴氣息更增加受害者心理上的壓力,近用司法資源,臺灣人都不免畏懼,遑論無法充分掌握中文的異鄉人。
語言問題為其一,另一則為「國族」問題。汪英達指出,「如果你打1955報案,且是緊急案件,如發生性侵或毆打等情事,電話中對方會詢問你的安全是否受到威脅,以及你是否有報警的打算。若你給予肯定的見解,不久後,會有巡邏員警前往現場查看。一般的派出所,並沒有外事警員的編制,也就是說,這位巡邏員警通常是沒有辦法與該移工溝通的。」此外,汪英達揭露的另個事實是:基層員警對移工的普遍不友善。
他指出,有些時候,外籍移工明顯的是性暴力受害者,然員警卻詢問移工是否為逃跑外勞。「我們庇護中心曾遇過有員警直接當著雇主的面,以中文詢問該移工,『妳的雇主有欺負妳嗎?』」,他質疑,在這種情況下,移工真的敢說嗎?
或許有人會認為,語言就算隔閡,我們還是可以找翻譯來協助受害者,讓她的受害情境得以完整於法庭上呈現。然而,這恐怕是對於移工的特殊性疏於瞭解了。
Sherry提醒我一件事,能夠像她一樣,以英文流利溝通的菲律賓人並不如大家所料想的多。以A來說,A是菲律賓人,但A精通的僅有當地的Tagalog,而政府給菲律賓籍的移工找來的翻譯,多只精通英文,而不會菲律賓人日常溝通的Tagalog。1
同時,一般的通譯由於不具備法律,甚至翻譯的背景,所以在開庭之前,不僅不會與雙方當事人先做些基礎的溝通與了解,在法庭內,更不會就法律程序做出任何進一步的解釋,對於本身即不諳台灣司法系統的移工來說,通譯給予的協助非常有限。A反應之後,雖在律師的協助下順利地更換通譯,但由於人選有限,日後所換的通譯仍舊無法提供A有效的協助。
通譯的問題,是很多法官在辦案時,都難免感到頭疼的。具有仲介背景的通譯,本身即有道德風險;而多數通譯本身並不具備語言上的專業,或者法律知識,只是單純地「會說該移工的語言」,卻因檢察官或法官所能遴選的名單有限,最終只能選擇將就。曾有法官不具名表示:「有時候看到移工只講了兩、三句,通譯轉過頭來卻說了一大串,心底雖覺得複雜,卻也不能說什麼,畢竟我也不理解移工的語言。」
受訪的蕭永昌檢察官及王子榮法官指出,最大的問題是通譯的報酬太低廉了,導致通譯的素質始終無法提升。王子榮法官更進一步地表示:現行運作的狀況,移工必須有點「碰運氣」,不是每一間法院都能夠培養其長期合作的通譯,以他所任職的法院,透過多次交流,已逐漸培養出幾個固定人選,而這些通譯也因為跟法院有穩定的合作,逐漸養成法庭知識。
除了通譯之外,還有一個很關鍵的問題。性暴力發生後,社會局會依照規定指派一名社工協助受害移工,A的個案中,警詢時雖然社工都在旁陪伴,但兩人之間卻因諸多考量,始終無法在互信的基礎下互動。汪英達嘆了一口氣,他表示,相較於社工,移工們通常更信賴同國籍的姊妹或NGO,像A真正信任的是有同國籍的姊妹Sherry,以及Sherry所服務的NGO——桃園市群眾服務協會移工服務暨庇護中心——然而因法規限制,他們只能在門外焦急等待。這應是汪英達心內的莫大遺憾,採訪過程中,他不只一次地強調,「A與我們具有信賴關係,我們卻無法進入法庭,我們不斷地想著,如果我們可以進去,那該有多好,至少我們可以了解,究竟A與通譯之間出了什麼狀況,而不是每一次只能在門外乾著急。」
王子榮坦承,這確為立法上的疏漏,法條訂得太死,有時,移工信賴的對象可能是在台灣的同鄉,或者是與他們語言相通的NGO工作人員,目前立法上,NGO既不具備親屬關係、也不符合法條規定的職業身份,在性侵案件中的被害人接受訊問時,並無法在場,提供意見,未來應修法,讓被害者信賴的對象可以陪同他們,降低他們接受訊問時的心理壓力。

我們如何看待飄洋過海的移工?
在書寫這篇文章前,我在網上瀏覽幾個可見度較高的移工討論區。很快地,我從這些平台上,幾個比較熱議的話題,感受到從中所透露出的徵兆。通常,這些平台的使用者,除了仲介之外,多半是家有老幼,或身障者、重殘者,而現有的家庭成員無力負擔照顧重責的家庭。相對於移工,他們雖是較有資力的一方,但若置於台灣社會整體,他們立即顯得無助且蒼白。即使移工薪資相對便宜,對不少家庭來說仍是重擔。也因為不全的社福制度,讓部分家庭選擇較為高壓、強硬的管理方式,以確保家中的看護人力不至於出現空窗期。
好比說,汪英達先生有談到一點,移工若在台灣已建立起與同鄉的人際圈,將提升於她在受害時儘速得到援助的機率。但,不難想見的是,「外勞在台灣建立起與同鄉的人際圈」,在部分雇主眼中,將帶來精神上的緊張。他們認為移工與同鄉過從甚密,將提升她日後不告而別、轉往打黑工的機率。有些雇主甚至提出,應極力避免移工建立起自己的人際網絡,輕則上班時容易分神,想跟朋友聊天,重則容易「學壞」,會開始爭取放假、加薪等等,可說是「後患無窮」。
而在討論如何管理家中的家事外勞時,常見的討論是怎樣的管理是「合理」?法律或倫理的界線又如何畫出?然而,只要一個不小心,這樣的討論便易擦槍走火、煙硝漫升。光是「家中無足夠的房間,給外勞睡客廳,鋪個床墊好嗎」如此日常的問題,也能引來兩種思維的摩擦與衝突。若有人答「換作是你,工作一整天,晚上還要睡客廳,你隔天有精神工作嗎?騰一個空間,給他們一點隱私權吧」,後續的回應也可能是尖銳的「他們如果不滿意就回去啊,要來台灣工作領這個錢,就是要付出這個代價」,「台灣的房價這麼高,家中即使有三房,夫妻一房,小孩一房,老人家一房,那些喊說要給外勞獨立空間的,要我們這些財力不佳的家庭情何以堪」。
有時,煙硝甚至能引起更廣泛的爆裂,也像是上述提到的,「自由轉換雇主」的權利,多數雇用外勞的家庭無一不反對,他們認為「為什麼寧願保障外勞轉換雇主的權利,也不願看見小家庭在空窗期的無助與痛苦?」
越是深入這議題,便越能感受到移工與雇主之間的關係,隨著演進,隨著制度與和社會風氣的變遷,被引導成一種零合遊戲的局面,意即,一方之所得必為一方之所失。外勞與雇主之間,似乎隱約有一條界限分明的線,若站在移工這一端,那雇主那一方很難不將你視為威脅;反之亦然。
移工與雇主之間的膠著,其實是許多問題的倒影,是台灣長照困境的倒影,也是台灣低薪問題的倒影,甚至能說,是全球化與自由化之後,勞工易遭剝削的倒影,這麼多問題聚在一塊同柴薪的堆疊,只需要一根小火柴,就能引起大火。對A而言,對於阿妮而言,對於更多飄洋過海,只想求個經濟安穩的移工,卻遭遇性暴力的移工而言,她們也許在深夜時分也曾經自問,「為什麼是我?」。當然,這個問題可以輕易地以個人的命運作為解釋,但在經過層層的抽絲剝繭之下,這個問題也能深沈地理解為:這社會上,有些人始終站得,比我們更逼近危險。
移工為什麼容易成為僱主決定施展性暴力的對象?有什麼物質條件阻礙了移工的求援?又有哪些因素導致性侵或性騷擾證據的保存不易。要受到通盤檢討的部分,絕不應僅止於移工這一個區塊。記者會當日所揭櫫的「看見移工處境」,應只是一個起點,從移工處境出發,將有許多更為錯雜及嚴肅的問題,亟待我們的正視。我們必須在「如何看待飄洋過海的移工」這份提問上,填上自己的答案,那將決定移工處境的未來往哪裡去,而台灣人又可以留給這塊土地甚麼樣的價值。

- 在此,有個小插曲不得不談,這並不是A第一次與通譯交手,兩年前,A的第三位雇主,在A工作時以肢體猥褻A,A於是對雇主提出告訴,當時,編派給A的通譯,具有仲介背景,在為A翻譯的過程中,不知道出了什麼差錯,通譯突然在A與醫生的面前將驗傷單撕毀。由於事情發生在兩年前,究竟為什麼該名通譯要做出此舉,已難以考究,但這個事件卻影響到A對於台灣司法系統的不信任,並間接導致當她再度被新任雇主侵犯時,對於尋求司法救濟始終猶豫不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