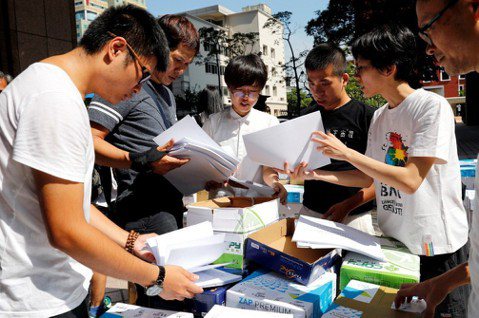宋逸民事件的基督教迷思(上):教會是保守反智代名詞?

「藝起發光」教會所引發的一連串爭議,尤其是當事人之一小甜甜的婚姻狀況曝光後,社會對於該教會與牧師等人的態度一片譁然,也困惑於基督教會的組織,究竟是怎麼運作的?為何有些神職人員會以宗教語言來面對社會質疑?而神職人員在教會中又被賦予什麼樣的權力?真的可以任意支配教友的心智和信仰生活嗎?
隨著過去十年,因台灣LGBTIQ團體更積極於現身並爭取相關權益,由台灣基督教會所領導的反對勢力也隨之浮上檯面,在社群媒體的擴散效應下,也給一般民眾留下某些特定印象,例如「靈恩派」幾乎成為反智的代名詞。看似百花齊放的各路基督教派,是如何在台灣發展起來,一路演變成如今的樣貌?
基督教在台灣和教會的公共角色
台灣的基督教發展,始於19世紀後半葉,1859年,西班牙籍的天主教道明會郭德剛和洪保祿神父抵台傳教,隨後於清光緒年間被劃入廈門教區,後因中日戰爭等因素,台灣於1913年終於成為獨立教區。緊接著道明會腳步的,是蘇格蘭長老教會的巴克禮牧師,和加拿大長老教會的馬偕牧師,兩人先後來台一南一北,以醫療與教育雙管齊下展開宣教工作,成立了台灣基督長老教會(Presbyterian Church in Taiwan, PCT)。
不同於基督教在中國漫長的發展,始終必須仰賴政權的態度,透過與官方的往來和合作,甚至透過與東印度公司來拓展宣教路線,天主教與長老教會在台灣並沒有與中央政權打交道的需求,傳教士深入民間、落腳偏鄉和原住民部落,落地生長的信仰。天主教允許中國信徒祭祖、祭孔,是歷經幾世紀的禮儀之爭與政權間的張力下,入境隨俗的一種生存策略,這與來到台灣的傳教士們因進入「邊陲視角」,開始對殖民主義有所反省、推動信仰的本土化,形成鮮明對照。
中國基督教會在五四運動後才有了本土化意識,也因此信仰與「救國」始終是分不開的,不論是希望以基督教帶入中國的思想、理性、科學等手段來救亡圖存,還是寄望信仰對於國民的「生命轉化」,都深深影響了當時在中國興起的新興本土宗派。加上受內地會以訓練中國本土傳教士「憑信心過生活、工作」的精神影響,掀起一波中國基督教的改革。

不同於歐美傳統宗派擁有嚴謹差傳與訓練制度,這些新興差會和福音運動在動盪的時代背景下「野蠻生長」,沒有時間和資源成立神學院或評鑑制度,而是從走過的每個鄉鎮城市的傳道田野經驗中,形成類似師徒制的訓練體系,新生的「上帝僕人」的認證不再需要來自傳統教派的考核。這樣的宣教策略讓基督教在中國的發展快速超越之前數百年、僅侷限在特定區域階層的困境,開始深入常民生活體驗,信仰也有了更活潑的面貌。
因中國共產黨主張無神論、對教會也不甚友善的態度,國共內戰期間,教會界都已有了來台佈局的風險意識,國民黨政府遷台後,不論這些教派先前在台灣是否已有發展,都改由中國過來的教會領導階層接手,而台灣的教會界也一分為二,俗稱「台語教會」與「國語教會」。而後的美援,有部份資源和社會救助工作,也是透過國語教會體系,以及由蔣宋美齡所主導的教會組織來進行,這層關係也更加深了彼此間的鴻溝。
1951年,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以下簡稱長老教會)受邀加入普世教協(WCC),由於這個運動主張教會是「超越國家、民族、階級的普世性實體」,並不拒斥社會主義國家的教會成員,在後來由美國所領導的冷戰、以及國共持續對立的大歷史背景中,顯得極為突兀,與國語教會、國民黨政權間的衝突,也因此事更加白熱化。
隨後,國民黨要員張靜愚追隨美國基要派牧師卡爾.麥堅泰(Carl McIntire)批判普世教協的腳步,於1960年發起了「反共護教運動」,國語教會紛紛加入,指責普世教協對信仰多所妥協、有違聖經教訓。表面上這是一場教義之爭,本質上卻是政治意識形態之爭。長老教會在總會議長謝緯牧師因離奇車禍過世後,由繼任的高俊明牧師暫時退出普世教協,然而這並未讓國民黨政府停止對長老教會的不信任,隨後又發生了查禁台語白話字聖經、禁止教會公報以羅馬字印刊等事件。

長老教會在此之前,並沒有要與任何政權積極對抗的意識,卻一再被壓迫,終導致從事神學教育者與知識青年們聯手,寫下三大宣言,成為近代史上建立台灣主體意識的重要轉捩點。可惜的是,長老教會至今還沒能獨自梳理白色恐佈期間,為數不少成員被監控,或被迫、或被收買的複雜歷史,完成教會內的轉型正義。
這場對抗的影響也延續至今,特別是在國家與文化認同上,包括近年應對中國威脅的態度、以及如何回應習近平上任後,連部份合法的官方三自愛國教會都遭迫害的情況,也都沒有共識。諷刺的是,後來重回普世教協的長老教會,延續70年代三大宣言和信仰告白的精神,堅持對主體性的追求,以及宗教自由不能妥協的原則,反而成了以信仰反共立場的真正繼承者。
雖然基督教並不是台灣的主要信仰,但「國語教會」與國民黨的歷史淵源,和長老教會從黨外時期就與親民進黨人士交好的背景,加上雙方都有向掌握更多社會政經資源的上層人士宣教的意識,比如受靈恩運動影響的教派從美國引進的「七山策略」,就包括著重對演藝人員宣教,而長老教會更有成員曾直接受邀擔任政務官,歷李登輝、陳水扁、蔡英文三任總統,都有能夠「直達天聽」的管道,造成基督教在台灣一直有巨大的影響力,與其信徒人數(只佔總人口5至7%之間)不成正比。

教會組織與神學教育制度的比較
然而,此次事件所延伸出的種種爭議,並不是一些網友想像的那樣:「國語教會=靈恩=保守反智」,好像有泛靈恩表現的教會就是偏藍,就是有黨國思想,並且特別缺乏理智,才會產生這樣的信仰內涵或教會體系。
首先,台灣的教會不論是國語教派還是長老教會,是福音派還是靈恩派,以西方政治學的坐標來劃分,教義上都同屬保守、偏右的這一邊,頂多程度上略有不同,且不乏擁抱基要主義的教會,甚至反對女性擔任神職人員,在任何情況下也都不贊成離婚和中止懷孕。但也有如長老教會或校園團契可能落在中間偏右位置上的;僅有少數神學研究者、長青團契、基督徒學生運動等團體,是以左派理論來審視或進行信仰反省。
再者,以制度而言,屬於本土的長老教會,其實與1949年後從中國遷來的信義會、中華聖公會、基督復臨安息日會、宣道會等都有類似「總會」的上層組織,也都有制度化的神學教育體系。早年台灣神學教育雖未獲教育部認可,但其課程和評鑑制度均比照歐美宗派母會,傳道人的培養、聘任、轉任均有一定規範。
在歐美教育體系承認的神學院裡,要成為牧師,所受的訓練稱為「道學碩士」,而非一般信徒也可以上的神學課程(如宋逸民在中華福音神學院所拿之證書),除語言訓練、聖經與神學知識外,也包括組織管理、諮商關懷等基礎課程,以因應相關工作所需的技能培養。

國語禮拜堂等一些中小型的教派,雖未有自己專屬的神學院,但在聘用牧師時,仍會要求在其它宗派神學院的道學碩士學歷,即使早期的靈糧堂和行道會也是如此。而直接自我認同為五旬宗(靈恩運動的前身)的神召會,在牧師資格的認定上,仍有明確的法規,可見並非所有泛靈恩教會,都接受寬鬆的按牧(成為正式牧師)標準,或自立為神職人員。
在是否投入社會關懷的見解上,長老教會及與蔣宋家族較有淵源的美南浸信會、衛理公會,同受加爾文宗影響,在教會治理上,也都同樣主張應由信徒和神職人員共同管理教會,組織則由各級會議和議會構成(地方教會會員和長執會、區域中會、全國性總會),而牧師是由信徒會議或推選出來的長老來選聘,頗有現代民主制度的雛型。
即使是新興教派,大部份教會仍有執事會(由信徒中選舉或推派產生)、長老或監督等角色,與牧師形成共治,有些教會如靈糧堂還另設有董事會,牧師更像是一個CEO的角色。
區隔國語教會與長老教會的,是身份與文化上的認同差異,而非神學觀、教義或教會組織形式。例如在同性婚姻專法的立法過程中,長老教會一樣通過反同牧函、甚至有牧師以深綠身份跑去為國民黨候選人站台,但也曾發生被認為是黨國牧師的周聯華牧師,在懷恩堂促成了教界第一場「紀念二二八平安禮拜」,促成李登輝前總統等政府高層,與民進黨在白色恐佈中的受難者一同出席,也奠下五年後政府正式為二二八事件致歉的基礎。
可見「國語教會=靈恩=保守反智」這種簡化的等式,是無法成立的。
▍下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