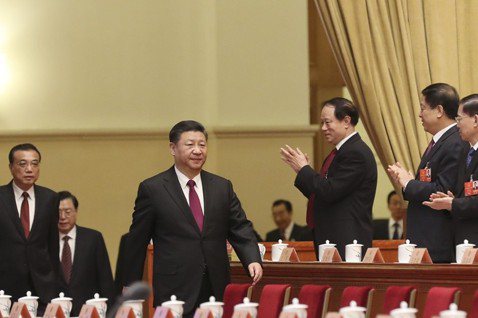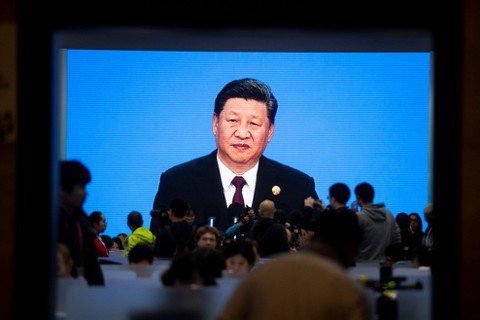陳嘉銘/不馴服的正義——《正義與差異政治》推薦序

▎前言
美國政治哲學家艾莉斯.楊(Iris Marion Young)的名著《正義與差異政治》出了中譯本!艾莉斯是作者在芝加哥大學政治系的博士論文指導教授,過了十年,隨著我閱讀和思考地圖的成長,我對她的理解不斷增加,下筆才能簡單乾淨起來。寫這個推薦序對我來說是一個在尋訪楊的過程中,翻搜自我靈魂(soul-searching)的旅程。和大家推薦這本書、這個哲學家。
我第一次見到艾莉斯的時候,她正聲音宏亮、神情愉快地走進教室,她有著一張大又厚實的嘴巴,臉上掛著哲學家中罕見的大笑容,看著學生的眼神不時跳出溫暖的笑意,這真是古怪極了。
芝加哥大學的師生平常多像是羅馬競技場的角鬥士,背著盾、杵著劍,全身緊繃地隨時準備說出聰明的話語。快樂在芝大是一種像愚蠢般奢侈的罪惡,這位世界最頂尖的女性主義學者和左翼哲學家卻這樣毫無防備地、快樂地、大聲地和我們打招呼。這樣看起來一點都不聰明啊──可是這也讓人太想擁抱她了。而三年後,艾莉斯.瑪莉雍.楊成為了我的博士論文指導教授。
楊教我的第一門課,帶我們討論法國社會學家米歇爾.傅科對政治理論的可能啟發。她打趣地說,許多人說她愈來愈傾向康德主義了,所以她要回頭讀傅科平衡一下,我後來才逐漸能體會這句話。
如果你曾經被康德感動過,篤信每個人都必須是自己的目的,不能只是他人的工具,此感動勢必也會驅使你喜愛傅科,著迷和顫慄於他對現代規訓體制(監獄、醫院、工廠、軍隊等)和治理理性的批判,也因此你不得不回頭批評康德的普遍性理念的缺陷,而這全都是因為你太愛康德了。
有些評論者將楊歸類為康德主義者,有些說她是像傅科一樣的後結構、後現代主義者。你說康德和後結構主義者不是不相容的兩個極端嗎?喔不,楊心裡一定很清楚,如果你真正關心那些被現代制度壓迫的人們,你如何能不同時既是康德主義者又是後結構主義者?你必得兩者都是。
貼近正義議題:從社會群集的路徑出發
如果上個世紀八○到九○年代論述正義的關鍵字是「差異」,本世紀頭十年論述民主的關鍵字無疑是「涵容」。當代沒有一本討論差異和涵容的著作可以跳過楊的論述——當代也沒有一位政治哲學家,將差異和涵容這兩個理念的底蘊,闡明得比楊更貼近那些邊緣、無力、被剝削和歧視的人們的社會生命處境。
什麼是差異?每個人都有平等的權利和機會,被法律平等對待,不就已經足夠了嗎?為什麼我們還要特別關注人與人之間的差異?楊帶著說故事的語調說,從前有一個黑暗時期,人們出生就屬於不同的政治、種姓或社會階級。因為不同的階級、種族、宗教、性別、職業等身分,人們被給定不同的特權和義務:有人出生就是統治者,有人出生一輩子就是貧農。
接著,啟蒙時代來了,我們開始相信每個人都有一樣的理性和道德感受,人人平等,都該擁有平等的權利和機會,被法律和國家平等對待,不能因為性別、種族、宗教、階級等差異而有不同。啟蒙並不排除個人間的個性和人生計畫的差異,事實上,啟蒙之子的自由主義當然鼓勵每個人探索自己的個性,實現自己的個體性。
但是對楊來說,從關心當代正義的觀點來看,意義重大的差異,不是個人間個性的差異,而是每個人屬於不同社會群集(social group)的差異。一個人必然同時屬於許多種社會群集——她可能屬於女性、母親、原住民、每日只能聽從命令的勞工、同志、住在貧瘠的鄉村、老年、對抗污染和徵收的居民等等不同的社會群集。
在此世,你被擲入這些社會群集裡,無法選擇屬於哪個群集。每種社會群集的產生,坐落在什麼社會位置、被社會怎麼對待,主要被動態的社會過程所形塑,不是由單方面的文化本質、生理特質或者個人決定。楊認為啟蒙社會所謂平等的制度,反而對某些社會群集帶來壓迫。注意到人屬於不同社會群集的差異,才能夠看到自由社會仍然持續對不同的人進行不同的壓迫。
抽象來說,差異指的是那些無法被普遍制度窮盡的人的特殊性。哲學家採取不同的路徑探討差異,有的從社會本體論、有的從對理性的批判、有的從社會反抗等等。「社會群集」是楊提出來最有創見的概念之一,這是她探討差異的獨到路徑,比其他哲學家更具體和貼近我們的切身經驗。透過這個概念,楊非常有力地說明為何在啟蒙和自由的社會,差異仍然是關鍵的正義議題。

中文名的發音練習:一堂指認壓迫的課程
楊的課輪到我自我介紹,我如往常用美式英文發音唸了我姓名的羅馬拼音。多數美國人無法唸出或記得我的名字,因此常會迴避叫我的名字以免困窘,這常會讓我覺得自己是美國社會裡突兀的隱形人(突兀和隱形其實相矛盾,因為矛盾因此更突兀,只好更隱形)。楊說,「可否請你用正確的中文發音把你的名字再講一遍,我想要試著念念看」。之後,她跟著我念了幾次,都無法準確地用中文念出我的名字,只好笑著說:「Chia-Ming,看來我還需要多多練習。」
楊說她對政治哲學的熱情始於女性主義。在絕大多數的社會,女性生活在文化歧視、經濟剝削、無力、邊緣化和暴力威脅中;過去這些經驗被「正常化」、「私領域化」和「去政治化」,因而被理所當然的接受。沒有比去政治化更政治化的策略了。女性的禁錮來自許多看似最中性、正向、細瑣、和政治最無關的社會關係,因此最了解政治的無非是女性,而不是那些眼中只有物質力量的現實主義者。
也因此,女性主義最敏於拉下各種「去政治化」的假面具,為所有其他弱勢者的壓迫開闢出一條被看見的道路。政治不只是公領域或者政府的事,為了讓所有壓迫可能被看見,女性主義建議,我們最好將政治界定為一切「可以被集體重新評價和參與改變的事物」,政治無所不在。
既然政治無所不在,楊接續著說,如果我們了解壓迫在各種社會過程、關係和結構中如何產生,我們就會認知到我們對正義的責任無所不在。個人間的人際互動當然也是政治,我們常在人際互動中延續了某種促成壓迫的社會關係和結構。楊在公眾場合困窘、吃力、不準確地唸出我的中文名字,她教會了我什麼是社會群集(我做為一個英語不好、不熟悉美國社會,不會small talk,沒有勞動力、來自東亞的男性)、為何政治無所不在(我和美國人的人際關係誠然是)、以及什麼是正義的責任。
你可能會懷疑,難道任何社會關係都是壓迫嗎?沒有一個正義的標準,怎麼定義壓迫?楊的分析拒絕停留在抽象層次,因為抽象對被壓迫者沒有幫助。她具體分析了所有社會群集可能面臨的五種壓迫面向:剝削、邊緣化、無力、文化帝國主義和暴力——即使沒有清楚的正義標準,我們還是可以辨認壓迫。

《正義與差異政治》如何開創正義論述的新典範?
一本書成為經典的旅程常常難以預料。一九九○年出版到現在,楊的這本名著《正義與差異政治》歷經幾次知識界的辯論,愈突顯出它掌握社會現實和規範理想的深刻和準確。快三十年了,回過頭來看,這本書開創了正義論述的新典範,對今日思索正義持續帶來衝擊。容我大膽評論,這本書可說是摘下了九○年代正義論述的桂冠。(如果你有興趣的話,我會說七○年代正義論述的桂冠是美國哲學家約翰.羅爾斯的《正義論》,八○年代是經濟學諾貝爾獎得主阿馬蒂亞.森的能力途徑)。
《正義與差異政治》這本書完整而且深刻地總結了二十世紀六○年代以來各種新社會運動訴說的壓迫經驗和正義訴求。它像海綿般地吸收了當代歐陸哲學家關於差異、認同、排除和他者的思想精華。它集批判理論、新左派論述和女性主義於大成,而其提供的分析架構,幾乎涵蓋了所有追求平等和解放的當代新社會運動,包括:女性主義、各種性向、種族、原住民、族群、不同壓迫處境的工人、環境、身心障礙、各種身心疾病患者、老年、青年、民族主義、後殖民等等抗爭歧視和壓迫的運動。
我要解釋《正義與差異政治》如何開創了正義論述的新典範。讓我們先回到冷戰時期全球三個正義論述的主要典範。第一、全球一半以上人口相信的馬克思主義;第二、自由主義福利國家的理念,最好的代表性論述是羅爾斯的《正義論》;第三、柴契爾夫人和雷根總統採取的自由放任資本主義路線,代表性論述包括了羅伯特.諾齊克的自由放任主義(libertarianism)和弗烈德利赫.海耶克、米爾頓.傅利曼等經濟學家。
馬克思主義主張所有壓迫的根源來自經濟結構,在資本主義體制中,資本家掌握生產工具,工人階級的勞動被剝削,國家等意識形態只是為資本積累服務,唯有生產工具歸為公有,人類社會才能獲得解放。對楊來說,她同意許多壓迫的根源得助於資本主義體制,可是傳統馬克思主義窄化了我們對壓迫的理解。即使有一天資本主義被推翻,女性、各種性傾向、種族、原住民、精神障礙者等等社會群集面臨的壓迫仍會繼續存在,因為它們各有獨立於生產工具私有的壓迫根源。
此外,即使只論勞工,勞工面臨的不只是剝削,還包括勞動分工造成的非管理階層工人的無力、無法發展自我的處境。傳統馬克思主義也忽略了社會偏見和過程對特定群集的勞工造成的特定壓迫。舉例來說,擁有臺灣國籍的新移民女性的居家照護工作收費只能比臺灣出生的女性低,工作遇到的暴力危險、被占便宜和歧視的狀況卻遠多於她們。
楊要我們鼓勵和認可各個社會群集的存在。多數認同政治的倡議者從黑格爾哲學出發,主張認可弱勢的目的,就是要矯正對弱勢的文化歧視,許多左派因此批評差異政治忽略了財富重分配才是正義的首要關懷。可是楊的差異政治和馬克思的親近性遠甚過黑格爾。
對楊來說,認可社會群集的差異性,鼓勵他們(如上述新移民女性)團結、分享生命經驗和集體發聲,終極目的不是在文化上矯正歧視而已,而是透過認可他們,才能幫助他們對抗更大的社會經濟的不平等和壓迫。認可差異只是解放的工具,或者說只是解除壓迫的一部分。

楊的思路繼承了批判理論和新左論述的醇正精神,這也是晚近文化研究的最大貢獻,除了少數例外,所有的文化歧視都帶來社會、經濟和物理上的壓迫,同時所有的社會和經濟的壓迫都得助於文化歧視。政治經濟學是文化的,而文化就是經濟。這是楊主張的差異政治最精微獨到之處,她的精準無人能出其右。
楊對自由主義福利國家典範的批評,對準了羅爾斯提出的正義理論。羅爾斯同意有效率的市場是必要的,但是必須給予弱勢補償。他推演的正義原則要求社會合作產生的果實,必須在有效率的諸多政策中,選擇能夠分配給最弱勢者最大福利(羅爾斯的詞彙是基本善,我代以福利稱之)的政策。可是對楊來說,這樣的正義考量只考慮社會經濟體制終端結果的重分配,這犯了兩個錯誤:
- 人們在社會經濟過程遭遇的歧視、創傷和壓迫,不是事後在終端給予福利補償可以彌補。福利國家或者羅爾斯的思維,把社會經濟過程黑箱化,要我們對黑箱內部過程視而不見。但是舉例來說,低技術勞工在工作過程中的每日無力和自我發展被剝奪,社會福利如何彌補?
- 福利國家或者羅爾斯把正義的核心意涵理解為福利的重分配,把人視為福利的擁有者、生產者和消費者,而不是有血有肉、能力需要發展的做著各種事物的人(do-er)。人遭遇到的各種壓迫,不只是因為他該分配到的福利被剝奪,而是因為他做為做各種事物的人的能力發展和自我決定被限制或傷害。只把人視為福利分配者,看不見這些傷害。也因此,福利國家看不到人在社會經濟過程中遭遇到的各種壓迫。楊的差異政治要把這些過程打開來被看見。
冷戰的第三個典範,自由放任資本主義主張沒有政府介入的社會經濟過程就是自願和自由的,因此也完全是正義的,保護自願交易的財產權和契約就是最大的正義。這樣的思維是鼓動全球新自由主義經濟體制擴張的火爐,也構成了對今日人類社會最大的威脅。我想我就把這個功課交給讀完這本書的讀者了:楊會怎麼批評自由放任資本主義?

不馴服的正義
我們現在已經可以大致看出楊勾勒的社會正義新地景。三個冷戰典範都看不見社會過程中發生的各種壓迫,他們無法指稱新社會運動抵抗的壓迫為不義。性別、性傾向、原住民、族群、不同處境的勞工、身心疾病患者、老年、青年、環境居民等社會群集是社會過程的產物,它們不只透過社會關係和互動產生和再生,也同時在巨觀的物質、文化和社會結構(例如文化帝國主義、勞動分工、科學知識等等)的背景下產生和再生。我們只有同時關注社會過程、分析社會關係、了解互動的變化、琢磨不同和多層次的結構,才能試著去理解某個社會群集受到壓迫的具體面貌。
你可能會說這樣的正義樣貌太複雜了。我要以一個社會圖像幫助讀者試著不去排斥楊的新正義典範。冷戰三典範分析的是方正、對稱、均質和邊界清楚的民族共同體或者經濟體系,每個人有對稱的權利與義務,對等的利益互惠關係,這是一個井然有序、馴服的工業的社會圖像。
然而,楊的差異典範散射出來的正義社區卻是一個都市的社會圖像,我們不再是對稱和均質的個人,而是分屬不同群集社區,來自不同地方,背負不同歷史意識,說不同母語、擁有社會過程賦予的不同優勢或劣勢。
我們不僅匿名,而且無法完全同情想像彼此的生命經驗,我們每天在轉角遭遇不熟悉的生命群集,我們都市的成員邊界也並不百分百清楚。如果我們能用這個不馴服的都市生活圖像去領會楊的正義典範,或許我們能慢慢脫離「均衡、對稱、熟悉」對我們的永恆誘惑,然後或許有一天我們能像楊一樣,和被壓迫者們一起說話。
系上的老師、學生、行政人員,楊的學者和社運朋友都著迷地喜歡楊。楊的追悼會在芝大校園的約瑟夫.邦德教堂舉行,那是一個一年中有半年被樹藤綠葉包覆,半年被白雪覆蓋,美得讓人對死亡感到溫柔的教堂。
一位老師上台說,楊剛來芝大任教時,他們這些菜鳥老師組的馬克思主義讀書會冒昧邀請了她,沒有預料到名氣這麼大的楊竟然一邀即到,一位一位來自各領域的人上台敘說著類似的故事。楊的女兒說,我母親幾乎沒有拒絕過一個弱勢團體對她的邀請。我想起有一次到市中心玩耍,遠遠看到楊在一個旅館門前的走廊,和一群失業員工一起舉牌繞圈子,抗議旅館不當遣散,他們就這樣輪班繞圈抗議了一整年。
我不知道楊一天有多少時間,她是系上花最多時間改學生寫作的老師,也是最願意瞭解和討論同事學術想法的人。楊不只是一位難以超越的哲學家和老師,她還是個慷慨的人。慷慨在人類還知道什麼是高貴的古典世界時就是高貴本身,它還有另外一個名字叫做「壯美」(magnificence)。
這是一個慷慨的人,這是一本壯美的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