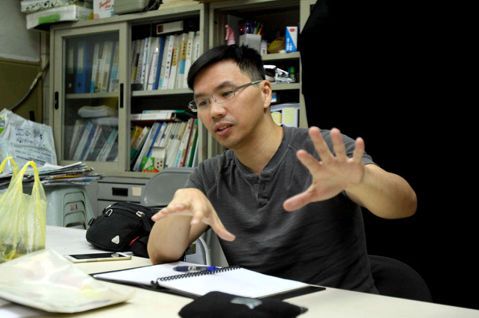【尋找捷運潛水夫】文明二十年,潛水二十年

二十個年頭,該如何計數?
一段從稚嫩到成熟的時間?或者成熟到飽經風霜的歲月?
在減壓症(潛水夫症)工人身上是無止盡輪迴,在痛楚與掙扎之中。
陳定安(新店線CH221標罹病工人之一,至今未和解),這次工人們上台北致詞的代表,他們都推託自己不太會講話,但在《尋找捷運潛水夫》片中,那是真實而毫不掩飾的,在此亦是。站在首映會上,他幾乎用盡全身力氣,如此卑微,向著社會講話。
那是必要,也是不得已。
身體上,如針扎一樣的痛,差不多跟了他一輩子,從年輕到老。
「吵才有糖吃」
這是現任台北市長柯文哲八月時,針對台北捷運潛水夫症工人重啟談判,對著媒體所說的。的確也是,他們要吵還不容易,必須知道能夠吵、有勇氣吵,再來,還要有力氣吵。
每一次上來臺北,無論是開調解會,或是這次紀錄片映會,都是在天未破曉時啟程。從玉里到台北,258公里,幾乎等於他們一輩子的距離,到現在仍走不完。年輕時,比起家鄉,台北薪水高,彷彿一個夢,可以快速累積財富,養家、生活掙扎,咬個牙就過了。罹病後,這批工人得不到補償,也就帶著病痛回鄉,只能偶爾打零工、務農,發作時的痛楚連手臂都舉不起來,藥止不住,更遑論中醫推拿。到現在病情惡化,沒辦法久坐的他們,也只得忍著,搖搖晃晃好幾個小時到台北,為得是當初資方欠他們的照顧,有的那時一毛也沒拿。
「罹病工人已全數獲得照顧」,二十年前捷運開通,在台電大樓、江子翠站外各豎立一紀念碑,如今更顯諷刺,工人們都笑著這是他們的墓碑,抗爭之後留下的墓碑,只差沒一一刻上名字。

新店線CH221標施工時,承包商為阻擋地下水滲透,且兌現政治人物承諾——一年一線通車高效率——不當使用「壓氣工法」,將高氣壓灌至坑道內,且未照法定程序減壓、安全衛生訓練名冊造假、高壓氧急救艙僅供日籍承包商的工程師使用……這些高效率的追求卻造成工人罹病,在他們的記憶裡,北捷等於熱、濕、悶,「噢,以前下去時還沒有開始工作,已經在流汗了」,工人們這樣說,比起現在通風良好、先進的北捷,真的很難想像。
當時板南線CP262標,也使用同樣作業工法,直到新店線工人群起抗爭引發社會囑目後,才緊急停用,不過那批在坑道下的工人早已罹病,不只台籍,更包括超時工作的泰籍工人,而這批移工在工程結束後,來不及發聲就早已被遣返回國。
「那眼淚是自己流下的耶」
一九九五、九六年,潛水夫症第一波抗爭。當時一位工人在捷運外包商的工地意外受傷,向工傷協會求助,經協會發現,此工人曾在捷運工地工作,疑似患潛水夫症,經轉介至基隆海軍醫院就診,確診為減壓症職業病。往後,工人們集結,要求當初聯合承包商日商青木、台商新亞,與發包的捷運局與台北市政府負起責任。往後較早得到消息的第一、二批工人以每人七十萬元與承包商和解,不過當時第三批工人,也就是住在玉里的這些工人,因消息來得晚,且彼時身體損害來不及上台北,也未達當時承包商認定的賠償標準,而未獲任何和解金額。罹病工人們長達三年不斷行動,阻擋了當時建造中的高鐵使用此工法、高雄捷運則在多年後謹慎使用,而保護了高捷工人未罹患職業病。

那些潛水夫
二十年後,在協助花蓮工人重啟談判的抗爭過程中,當初籌畫抗爭的郭明珠、顧玉玲決定邊打仗、邊拍攝紀錄片,也就成了今天的《尋找捷運潛水夫》一片,沒有過多回憶與抗爭,在這二十年間,那些患病的工人去了哪裡呢?
有些工人去世了;有些回鄉務農;有些搬到小時候住的地方,和晚輩住一起,工人四散在汐止、深坑、基隆、板橋、台北、桃園,還有未和解的,都在花蓮玉里的山間。
「那時候的痛,就跟現在差不多,治療已經沒有什麼用了」,朱志誠回答提問的觀眾,因為錯失了治療的黃金時期,這句話似乎有點宿命,卻也是真實。
「累了,二十年了,我們都老了,不想再跟政府溝溝迪(糾纏)」,最年輕的工人李世憲在映後座談會說著,他的聲音很細很小,多少夾雜著無奈。一上台北,便在新店線CH221標段工作兩個月,接到兵單後,馬上去當兵。儘管當時在坑道內的時間不長,因此未達到資方刻意拉高認定的職業病標準,而無和解,但現在骨頭壞死、關節病變,這段時間承擔的不只是痛,而是沒有辦法好好生活、沒有穩定工作的飄泊,也因而沒有能力額外接受高壓氧治療。一直到現在,終於在二十年後,達到資方所訂的職災標準。
李世憲還有一個哥哥,李世德,他倆當時一同北上工作。李世德現住在花蓮的療養院裡,為精神疾病所苦。外人在猜,他的精神疾病多少與這十數年間用藥過度有關,持續的止痛藥及相關併發症,直到身體與精神都承受不住。
當時CH221標段的出入口,新生南路與羅斯福路口,現今變成平整的大馬路,對面是台大正門。「啊,痛噢,我剛出坑道時,走沒兩步就跌在地上,我就想說,欸,那欸軟腳,再爬起來,又跌下去」,張孝忠這樣說著,他是最嚴重的患病工人之一。跌在地上,卻以為是過度疲勞所致,當時沒有勞教,也沒勞動檢查員會檢查,他們從沒想過一輩子沒潛過水,卻得到這種病。
說後悔去做嗎,也許有工人會這麼嘆氣、悲憤;也有一些放手,想著成就交通便利,且犧牲自己。「都過了,後悔也沒用了」,許勝卿說。部分捷運工人早期也當過礦工,從塵肺症,到潛水夫病,他們幾乎接收所有台灣經濟起飛後的各種後遺症。
「現在幾乎不會搭了,捷運很貴,我搭公車就好了」,曾春雄被訪談時這麼說著,人來人往的路口與沉穩寧靜的紀念碑,同在這一座堪稱進步的城市裏頭。
二十年過去了,那些痛不會減少,他們要的不是再多的賠償金,而是能夠接受完整的醫療協助、在未來公共工程當中,不要再有職業災害發生;不要再像他們一樣受苦,如此微薄而已。

- 文:王詠葎,1996年秋天生,台北人,曾讀過中文系,目前習於清大人社院學士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