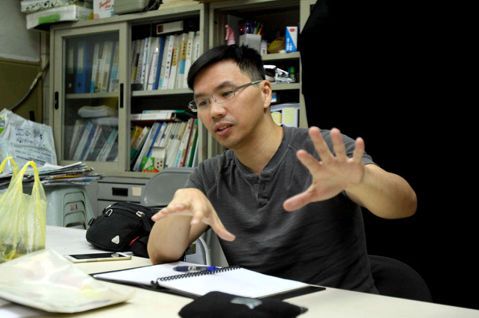【尋找潛水夫】災難立法:捷運工傷必須成為預防立法的典範

下午開會,張孝忠幾乎快睡著了,其他人說他昨夜沒睡好,跑到地上去睡,怕因為痠痛翻身,不小心吵醒其他好不容易入眠的「戰友」,大家明天還要一起去勞動部打仗。
失語之傷
中午他點牛肉麵,麵沒吃、肉也沒吃,只喝了湯。沒問哪又痛了起來,他的面容疲倦,自今年八月調解會後再見到他,笑容越來越少出現。以前總會講些冷笑話,拿自己的潛水夫病來調侃一下,其他的工人也會一起笑,因為他們了解那痛;他們知道張孝忠是最嚴重的,電視記者都會採訪他,還到過他家拍過影片。
剩下完整的牛肉麵最後留在店裡,他沒打包帶走,然後眾人慢慢地走回民權西路上的辦公室,有些人是一拐一拐的,其中當然包括張孝忠,他的臉愈來愈暗沉,右手扶著腳,每一步都是艱困。
12月12日早上,潛水夫症工人們至少站了四十分鐘,為了抗爭,最後濃縮成新聞的四分鐘。那痛,再加上歲月,他們也不過四十多歲,壯年正盛,如今凋零。台灣一直是災難立法,有了關廠工人,才有失業救濟金;有了RCA(美國無線電公司之員工在離職後,大部分罹患癌症,至今未被認定為職業病)才修訂職安法,那潛水夫症工人呢?當時疏忽無法提前預防,而今能不能作為防治職業病的典範?
失聲的政府
若是這群本地勞工沒有辦法被自己的政府所保護,更何況現在在台灣的六十萬移工呢?作為補充性勞力,他們從事工作部份偏向粗重、危險的營造業。僅被作為一次性商品的他們,在職災、職業病發生後,早被遣返回國了。
捷運潛水夫症工人抗爭當天,我問了特地前來的法扶副執行長,林聰賢律師,「為什麼政府沒有辦法預防職業病呢?」,他聳了聳肩,指著後頭的勞動部,笑裡帶點無奈,「那要看勞動部強不強硬。台灣不願意立法,多與強硬的資方有關」,又繼續追問下去,「那到基金會申請職業病訴訟的扶助,究竟是那些呢? 是辦公室文書工作? 還是?」
「不不,他們(辦公室工作者)大多都認了,在我記憶中幾乎沒有職業病,頂多職災。由於職災很好判定,職業病牽涉到因果關係,還有時效性問題。法院在判定時,多仰賴職業病專家的鑑定,而這在台灣很少,其他的醫生也未必敢開。」我沒繼續問下去,近正午的陽光有點熱。
就當日抗爭結果而言,勞動部給了許多「表面的回應」,像是面面俱到,但又一點也不具體,前幾次的調解結果亦是。面對潛水夫症工人們提出的訴求,要求公共提撥百分之二的工程款,成立安全衛生基金,作為預防職業災害之用。「是,我們在政府採購法……丁類審查有明定……」、「我們會送工程安全委員會審查,書面審查會載明建議工程發包單位……」,最終只淪為依法行政、綜合判斷後的解答。

工會須介入
從最開始工會的保護,到最後的法律安全網,受傷的工人永遠只能落到最後的訴訟才能一搏,好一點的,就是雇主願意負起賠償責任,不必耗費幾十年時間訴訟。這是一個結構性的問題,台灣大部分工會處於積弱不振的狀態,戒嚴時,因為害怕左翼勢力,工會多被執政者掌握;解嚴後,許多職業工會只被作為掛名勞保的功能之一,實質上是名存實亡。再者,工人們也未必有意識加入工會,從小並未有職業面向的教育,永遠只教學生要忍耐,爭取權益時只被冠為「不知足」、「要糖吃」的貪婪形象。
薪資過低? 工時過長? 忍一忍就過去了,至少還有工作、至少還有薪水,這也是其中一個台灣工時排名長的原因。台灣社會一直羨慕北歐生活,工時低、薪資高,那是他們待廣大勞工友善,還有是一整個社會體制的支持,才有的結果。以北歐1丹麥而言,10萬勞工當中,有九十八位被認定為職業病(2005年),且具補償,鄰近的韓國是九十二位(2007年),而台灣遠低於國際標準,僅四點四位。
北市產總的鄭雅慧也表示,「我們已經輸掉七天假,若是工會沒有做好職業病預防,過勞、傷病都可以預期,他們就是後果。」,潛水夫症工人們正站在她後面。
職業病一旦發生,工人只得默默忍受,大多相信那是自己年老體衰所造成的。就算懂得要向雇主求償,也都孤立無援,工會頂多也是協助性質,甚至在營造業當中,惡質的建設公司售出建案之後,便宣布解散,工人們在發生職災後有時求助無門,更遑論潛伏期較長的職業病。
因此,12月12日潛水夫症工人在勞動部前的抗爭,北市產總、環保局工會、南科工會、中環工會等,才會站出來共同呼籲,工會應作為工人的防護網、預防職業病的第一線,若是發生任何在職場上的損害,工會應當介入調查、鑑定與處理體系。

還沒打完的仗
抗爭當日下午,潛水夫症工人與勞保局專案討論,由於之前的持續抗爭與施壓,勞保局已承諾會竭力協助工人取得傷病補助。但對工人來說,又是另一道高攀的關卡,什麼文件要去哪裡開證明、哪些事情可能會碰壁,這些行政程序不一定是友善的。
張孝忠兩眼發直盯著前面看,我知道他在硬撐,專員很好心告訴他哪些表格必須填、什麼文件需預備,以他身體的敗壞,也許可以申請失能給付。
「捷運比台鐵複雜很多耶,火車我只要一直坐、一直坐就可以到玉里了」,會後離開時,朱志誠向我抱怨。
的確,剛才買票時就花了好一番功夫。
張孝忠一直很安靜,我走在他們的後面,領前頭的他們差一點走錯方向,台北車站很大、人很多,極容易迷路,就跟他們口中的「捷運」一樣。
電扶梯一路向下往台鐵車站入口,我們侷促一隅,張孝忠站在左邊,後頭的人怒視著他。我拉了他一把,示意他向右,他只嗯了一聲,不太懂意思。
剩一個小時普悠瑪才進站,他們決定先去晃晃,我與之分別,目送他們背影,很慢,很慢,比起車站的其他人,我知道幾個小時之後,他們會順利到家,畢竟來來回回奔波了好幾次,但抗爭的遙迢之路又有多遠呢?需要花多久時間才能走完?在他們之後,還會有其他人來走嗎?

- 文:王詠葎,1996年秋天生,台北人,曾讀過中文系,目前習於清大人社院學士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