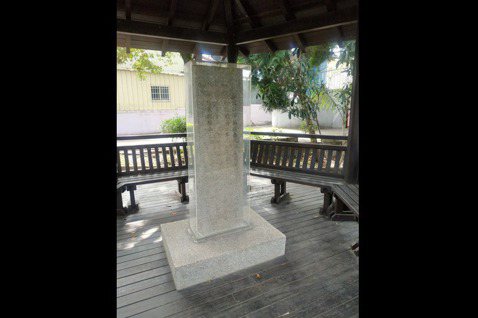從威權回歸「公僕」角色:警察文資地景需要一些庶民觀點

台灣在1982年開始有《文化資產保護法》,2000年公民才開始有申請文化資產的公民權利。
早期台灣文化資產的詮釋,多由擁有權力者掌握話語權,民眾大多聽信官方所聘請的專家。但是隨著民主化,人民開始爭取文化權利,社區居民與曾經是文化資產的使用者,也逐漸開始有人用庶民觀點論述文化資產。這些融入庶民觀點的文化資產,真實、貼切,某種程度來說反而增加了多元性。
不過或許是日治以來,警察一直扮演著國家勢力的延伸,在日治時期被冠上「大人」的稱號,長期以來也少有正在使用的警察機關可以供民眾參觀了解,導致相關地景,即使逃過都更拆除,成為文化資產後,依然侷限在專家學者採用的建築美學說法居多。社區居民與曾經是使用者的的非官方看法,反倒難以呈現。這種「缺乏庶民觀點」的情形,充斥在大部分與警察有關的文化資產上。
日治時期警察文資地景多侷限在建築美感與稀少性
日本統治時期所留下的警察文資約略可以區分成幾個類型,例如:武德殿、警察署、保甲事務所,派出所、警察宿舍……等。
老建築能以文化資產名義留下的理由,必需符合《古蹟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或是《歷史建築紀念建築登錄廢止審查及輔助辦法》。
以下舉例幾個指定古蹟或登錄為歷史建築的警察文資案例,及其理由:
- 現今是台南市立美術館一館的原台南警察署,強調的是台南州技師梅澤捨次郎設計,折衷主義裝飾藝術式樣風格建築。
- 彰化縣警局彰化分局(原彰化警察署)指定古蹟理由是:富含日式建築特色,尤其是建築物立面呈圓弧流線型,表現現代建築折衷式樣,而扇形建築的看守拘留所及其內部格局,還有二樓牆面上留存的槍口等相當特殊,顯現當時建築潮流。
原臺南武德殿指定古蹟理由則是:1936年建,為日本傳統社殿風格建築,垂脊以瓦作之切據、鬼屋紋樣尤為特別,為本市僅存之日式社殿風。
- 埔心舊館保甲事務所,登錄歷史建築是因具有20世紀初官式辦公廳舍的建築工藝價值,包括外部型制,洗石子、板條天花等。強調是為日治末期紅磚造辦公廳舍的典型。
以上由文化局提供所論述的「價值」來分析,理由大多集中在「建築」實體的論述,但是這種官方說法往往難以呈現文化資產的多元面相,也缺乏人與土地之集體記憶連結。


警察文資地景中被忽略的庶民價值
關於日本時代的警察文資地景,老一輩人經常有兩極的說法,這些口述歷史常被忽略,因此庶民說法,甚少因為後續的文資調查,就會出現在官方的解說上。
有些上了年紀,經歷日本統治的報導人認為日本時代警察管理很嚴明,幾乎是 「夜不閉戶、路不拾遺」,但光是這樣的論述,要成為文化資產登錄的理由之一,似乎又過分單薄,因為舉證需要人、事、時、地……,與歷史場景連結,才足以成為指定、登錄的理由之一。
然而,不少文獻與口頭訪談也提到日本警察手段嚴峻,讓人痛惡。台灣百姓對「日本警察」的深度恐懼,也表現在稱呼上,他們表面上尊稱日本警察為「大人」,暗地卻罵警察為「狗」。
高壓引來了台灣人的反抗,事件屢屢發生。如日本政府在1923年以執行《治安警察法》為由,造成「治警事件」發生,在這個事件中,日本政府的警察阻止台灣人演講、聚眾等自由,逮捕台灣文化協會成員多人。參與者蔣渭水、蔡培火遭到判刑四個月;林幼春、陳逢源、林呈祿、蔡惠如、石煥長遭判三個月徒刑;蔡式穀、蔡年亨、鄭松筠、林篤勳、林伯廷、石錫勳則遭到罰鍰百圓。
這些參與「治警事件」者,不僅不把坐牢當恥辱,還將入獄當成光榮印記,除了出入獄有攝影紀念、鑄造了紀念徽章,其中屢遭日警拘留、多次繫獄的蔣渭水在獄中寫下〈獄中日記〉、〈獄中隨筆〉、〈北署遊記〉、〈三遊北署〉等著作,這些文獻成為重要的史料。相對地,當時的台北州北警察署則被認為是以國家之名打壓民眾自由的邪惡機關。
不過目前在台灣遺留的警察文資,大概也只有1933年,蔣渭水過世後興建的第二代北署(現新文化運動館),官方在解說導覽時,尚能詮釋前述其「邪惡」的形象,其它日治時期的警察署在官方的網站導覽中,反倒是對高壓統治的記載付之闕如。


以保甲事務所為例,這些保甲老建築,理應有日本政府採取十戶為一甲、十甲為一保,互相監視告密,並規定連坐處罰的口述史。不過在指定、登錄為文化資產的過程中,並未見到這些文字記錄,更遑論採用紀錄片方式,將報導人的口述,在保留下的文資場域裡播放闡述了。而在日式建築的活化利用上,這類場所也不應該簡單的只是成為吃日本料理、穿和服拍美照的場所。
然而,歷史有多元面貌,面對日本時代留下的警察文資地景、文物,除了建築美學及上述的高壓統治歷史之外,能不能有其它庶民觀點呢?
筆者在相關的日本時代報導中,發現也有屬於鄉野傳奇的故事,不過,這類潛力故事,恐因為政治、制度因素,及現有史料不足等問題,現階段只能被視為傳奇的「野史」文獻——其中森川清治郎成神就是類似案例。
森川清治郎是一位日本警察,1896年來台擔任巡查,在今日的東石鄉服務,根據日本的《台灣日日新報》紀載中,這一位警察與其他日本警察有很大的不同,他曾替地方設學堂教民讀書,教導新的農耕知識,也替地方人士洗刷冤屈,「公僕」形象深受地方敬重。
而森川清治郎之所以成為東石鄉廟裡供奉的神,是因為他在1902年受託替貧苦的東石居民請願,希望日本政府能減輕地方的竹筏課稅,這個舉動反而被日本高層認為是煽動村民,對他訓誡處分,事後森川清治郎自殺,死後被地方視為神來祭拜,當地居民尊稱為「義愛公」。
筆者針對「義愛公」的史料分析,只能確認「義愛公」真有其人,事蹟尚待更多考證,但是他的「公僕」形象與治警事件中壓迫台灣人、甘願淪為國家暴力的打手是截然不同的1。由上述的案例,給筆者最大的反思是,「警察」不應該成為政治人物打壓人民的工具。唯有回歸到「公僕」角色,才能使警察獲得人民尊重,社區也才能將周邊的警察地景視為容易親近的場所。
而我們的「警察博物館」,或是相關展館,能否展示《台灣日日新報》中「義愛公」的文獻呢?

當代警察文資地景論述的幾種可能
可惜的是台灣面對戰後的警察文資,依舊是採用建築美學的角度,而且全台只有一處取得文化資產身分。桃園縣警察局桃園分局(目前是桃園新住民文化會館),民國68年八月竣工,登錄歷史建築的理由強調:「保留1970年代警察廳舍的標準式樣及圖面,留存已少,具清楚之時代風貌。」
我們不禁要問,警察相關地景,為何少有以具地方歷史價值,或是以地方貢獻之人物的紀念建築名義被保留?而即使成為展館,內部展示為何跟原本建築可以完全無關呢?
這些地景除了多一些地方庶民的歷史陳述之外,我認為有幾項是應該做的,分別是:盤點潛力點及老文獻、老文物;彰顯警察博物館價值;地方政府協力修繕活化文化資產。
1. 盤點潛力點及老文獻、老文物
固然地方的文化局有普查文資潛力點,並將建築主動列冊的權利,但屬於警政類的地景,或是老文獻、老文物,警察作為過去或是現在的使用者,應該比一般人更清楚哪些具有潛力價值,因此警察單位是否能主動提出,便成為重要問題。
舉例來說,戰後宜蘭有一個「殉職警察人員紀念碑」,是為了悼念1967年,宜蘭縣警察局三星分局,包含警官、警員、司機……共七名人員,他們之所以殉職,是前往太平山慰問其他同仁,並發送禦寒棉被給民眾的,不過在回程當中,發生汽車墜谷,導致身亡。筆者認為,或許這個紀念碑並不漂亮,但是值得探討其背後的意義。
另一個案例是發生在1984年,台中縣警局刑警隊長洪旭,因緝捕當時的十大槍擊要犯林博文,不幸中槍殉職,官方罕見的將他的事蹟拍成電影,還大力宣傳——雖然也有傳聞這些行為是為了遮掩並轉移民間熱烈討論政府醜聞「江南案」2,但這些並不能否定洪旭的因公殉職。
洪旭的葬禮,當時可以說是高官雲集,佔據了新聞的版面。政府不僅立了銅像,還將竹崎鄉的墓園命名「忠勇墓園」,墓碑有當時的總統蔣經國贈匾「忠勇足式」,不過物換星移,今日的墓園卻也因媒體關注不再,昔日的風光逐漸埋沒在荒煙漫草中。回顧這段歷史,嘉義警察單位是否可考慮基於保存歷史,來維修並整理環境呢?
而另一個問題是,一個跟警察有關的地景,能否有一些庶民有關的文獻展示呢?例如過去警察尋人、緊急救援、參與防疫……呢?而這種屬於警察及少數人才會知道的潛力文化資產,其實需要的是警察與地方文史工作者共同投入,才有可能發掘。


2. 彰顯警察博物館價值
有文資身分的警察文資地景,不少仍是警察機關在使用,如彰化市警察局、臺中市警察局第一分局……都是這樣的老建築,這些場所也可以考慮特定時間採預約制度,適度開放,例如一年一度的警察節、古蹟日,不僅可以詮釋建築,也可以藉此與社區互動,擺脫冰冷衙門形象,是生活博物館的一種展現。
另外台灣是有實體警察博物館的,屬於中央的是內政部警察史蹟館,由於缺乏知名度與行銷,許多公民並不清楚,內政部有責任將其高度活化。
至於彰化員林的警察故事館,雖然是日治警察宿舍建築的活化再利用,但至今沒有申請文化資產身分,這可能會使建築維修因缺乏專業而走樣,文化局有主動協助的義務。雲林最近則是將歷史建築斗南警舊廳舍,活化成警察故事館。
最重要的是,怎樣才能使這類博物館被庶民親近,是需要有地方故事來支撐的,也是這類博物館必須思考的。
3. 地方政府應協力修繕活化文化資產
維護警察地景類的文化資產,其實最需要的是地方政府文化局的協助,已經有歷史建築身分的北斗保甲事務所如今管理權是國有財產署與鎮公所,卻被民眾投訴,「花2000萬整修,擺五年不用」,成為地方「蚊資館」。
另外,彰化二林武德殿其實跟二林蔗農事件息息相關,但因為土地爭議,遲遲無法修復。像這類的歷史地景,對地方深具意義,公部門不應該放任風吹雨淋與閒置。
台灣的警察文資地景,雖然經歷過威權的年代,也正在走向未來,警察回歸到維護治安協助人民的角色,脫離政治不當干預,或許正是現在要追求的。
在這樣的文資場所,除了談建築美學之外,能不能也成為討論警察勞動權會館、展示「助人日誌」等文獻,讓這些展館被庶民接近,是必要且務實的做法。

- 就目前資料而言,森川清治郎的史料仍十分不足,其「義行」事蹟資料出自1923年及1930年日日新報,其卒年1902年則查無相關報導,因此現階段有限資料,很難由兩篇報導的史料判斷全貌,不過若視為「傳說」則較無爭議。另新聞史料仍需要嚴謹判讀,有時候報紙的史料也要再三求證,例如南海血書、吳鳳,這類文獻,並非不能展示,而是思考如何展示。
- 此為管仁健觀點,資料見〈管仁健觀點》國民黨養出來的「狗導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