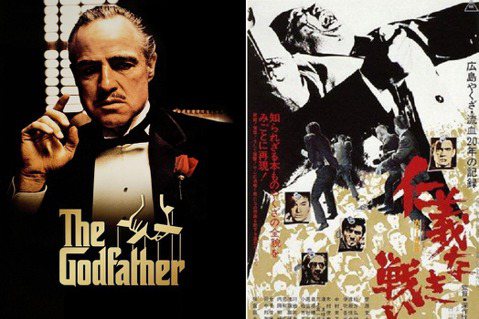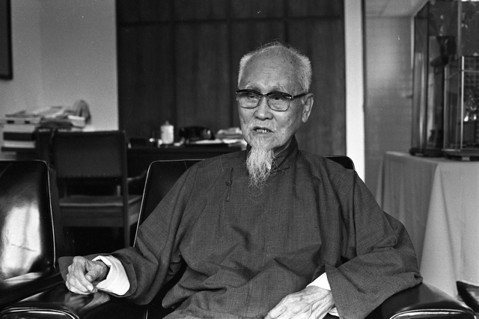從《王牌辯士》反思台灣辯士(下):形塑大眾文化的要角

▍上篇:
前面所說的辯士,比較像是政治演講的解說者,辯士的另一重意義,就是電影的解說角色。事實上,電影自日本引入台灣以來,便出現解說電影的辯士角色。不過,在統治者眼中,電影雖是受歡迎的娛樂,但幽暗的觀影空間也是可能的社會治安死角,尤其辯士們口若懸河,他們和影像有著同樣的誘惑力,因此必須積極管理。
1927年開始,台北州舉行了第一次的辯士資格考試,各州考試科目不盡相同,但不脫電影相關法規、作文與歷史地理基本常識。1935年8月的《台灣警察時報》列舉了基本常識的幾個考題:本居宣長、天津乃至法國首相姓名等,可見辯士應有一定的教育程度。

台灣辯士的第二重角色:形塑大眾文化
王雲峰、詹天馬是台灣最知名的辯士,然而,他們並不僅僅是能言善道的辯士,更參與到形塑大眾文化的行列當中。1920年代上海電影崛起,不少台灣人以跑單幫式的方式前去購片、租片,再回到台灣上映,1923年成立的永樂座尤其是放映的大本營。彼時上海電影深受台灣人歡迎,詹天馬也曾自組公司,購片在永樂座放映。
1932年初期,古倫美亞帶動台灣唱片業的興起,當時名盛一時的辯士詹天馬、王雲峰為電影《桃花泣血記》所做的同名歌曲,一時之間成為流行曲,歌詞即是對電影內容的簡介與詮釋。
《桃花泣血記》為台灣人的複合式觀影模式奠定基礎,上海電影加上台灣流行音樂的詮釋,再加上辯士的講解三者共構。除此之外,隨著1931年台灣放送協會的成立,台灣進入新的媒介時代,廣播電台裡也有介紹電影的節目,詹、王兩人也曾分別在廣播電台裡講解上海電影。從電影解說到流行音樂再到廣播電影,台灣辯士可說是「跨領域演出」。
值得一提的是,台灣人喜愛的上海電影有兩類:一是武俠片,《火燒紅蓮寺》是最受歡迎的武俠電影;二是階級差異的愛情或是親情倫理題材,《桃花泣血記》、《倡門賢母》等都是代表作品。
在台灣大眾文化的生產機制裡,前者有嘉義蘭記書局販售中國的武俠小說,《三六九小報》則有專欄以小說方式介紹武俠電影;後者不少都像《桃花泣血記》一樣成為流行歌曲,有趣的是,歌仔冊也有不少以此為題的作品。
上海電影在日治時期的台灣電影文化裡意味著什麼?日治時期51年裡,台灣人自己拍的電影不到十部,主因是電影人才與資源相對欠缺,另外,觀眾可能也較慣於前述上海電影的複合式觀影模式。1920年代上海電影發展鼎盛,1929年全球經濟大恐慌之際曾面臨泡沫危機,1930年代重新再起,批判城市現實的左翼電影是其中的重要類型。
台灣觀眾在眾多上海電影類型中,獨獨喜愛武俠與階級差異的愛情、親情題材。前者可能是對中國古代歷史以及行俠仗義的想像,後者則呼應彼時台灣青年所倡議的愛情自主。總而言之,這個自主選擇過程,代表了台灣人的文化偏好與趣味。

從銀幕內外豐富日治時期台灣電影史
1927年美國電影《爵士歌手》(The Jazz Singer)標示有聲電影時代來臨,四年之後日本的第一部有聲電影《夫人與老婆》(The Neighbor's Wife and Mine)也問世。此刻,與電影銀幕的聲音互相輝映的,是抵殖民運動的眾聲喧嘩。
隨著台灣社會進一步發展,文協原來的路線受到許多挑戰,蔣渭水退出文協、成立台灣民眾黨成立這一年,也正是《爵士歌手》上映前三個月。到了1930年代,政治社會團體的分裂是一條條複雜的線才能說明的圖像。
但另一方面,代表台灣城市流行文化的歌曲卻也在此刻綻放。政治、社會運動團體的眾聲喧嘩,與流行歌曲在台灣同時迴盪。
兩種辯士看似各自在不同舞台上登場,或透過影像播放講解現代生活,或講解電影,甚至參與塑造城市流行文化的塑造。不過,我們會發現兩者其實偶有空間的交集,台灣人經營的電影院有時候是公共空間,例如有時是文協的活動場所,最經典的莫過於1931年蔣渭水逝世的大眾葬,舉辦地點正是在大稻埕的永樂座。
蔣渭水大眾葬的紀錄片裡,短短兩三秒可以瞥見永樂座外觀的歐式風格,也可以看到永樂座裡各種政治、社會運動團體敬贈的花圈。因此,電影院也可以說是標示台灣人意識的場所。

小結
當世界電影史從無聲翻向有聲一頁時,台灣因為被殖民情境,使用台語的台灣辯士一直維繫觀眾與影像的中介,甚至到了戰後,辯士也都還存在。1952年出生的知名作家吳念真,小時候便在電影院聽辯士講解電影,甚至萌生辯士之夢。
台灣電影史研究裡,有兩個有待釐清的問題。辯士在台灣電影史當中長期存在是事實,不過,有聲電影問世之際,也是台灣新一代知識菁英湧現之際。1926年台灣總督府台北高等學校成立、1928年台北帝國大學成立,加上赴日求學的年輕知識菁英,他們的文化品味是否出現變化?對電影的選擇是西洋片與日本片優先,還是會喜愛上海電影?
此外,上海電影熱潮在台灣到底持續多久?是1937年盧溝橋事件爆發後終止,還是跟前述的邏輯相同,即使不談知識菁英,隨著殖民現代性的構築,會說日語的人口逐漸增加,他們的文化品味是否也出現變化?
總而言之,日治時期台灣電影的相關研究就像對辯士的討論一樣,不大可能只局限在電影裡的辯士,而是要從銀幕內外的視角切入,這段歷史才能有動態而豐富的呈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