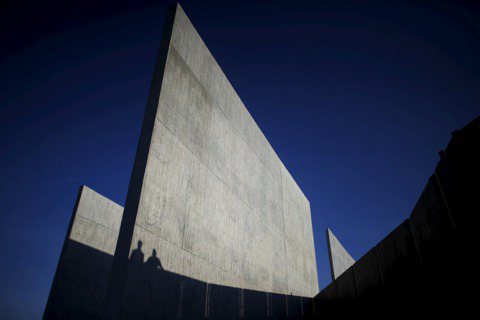接軌或脫軌——試爬梳後威權時期的司改脈絡

意外的借鏡
臺灣的法律體系,基本上屬於歐陸法系,而這套從歐洲學來、以德國法為主幹的法律體系,無論溯源至前清末年的變法運動,還是大日本帝國的明治維新,都起自當年的知識份子銳意西化、救亡圖存的企求。
在當年那些知識份子看來,傳統法律體系早就不合時宜,更淪為阻礙現代化的路障,必須修正,甚至全盤拋棄(臺語謂之kē-lō͘);而必須拋棄的,不只是傳統法系本身,就連它所以存立的價值、觀念、思想,也必須一併掃進歷史的垃圾桶。
由於這樣的法制背景,從德國留學歸國的法律人,在臺灣為數眾多,或許正是因為這樣,每當選民做出保守的決定時,威瑪共和以至於納粹政權的歷史,才會這麼常被抬出來;連帶地,兩次大戰之間的德國史上種種荒腔走板的現象,也為臺灣這令人哀愁的政治社會現實,提供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言外之意。
不同國家、不同時代的歷史之間的對比,當然不是網紅公知所說所寫的這麼理所當然;而且,在時序上,前清末年及日本明治維新繼受德國法的時候,第一次世界大戰還沒開打,威瑪共和連個影子都沒有;當時的德國首相還是俾斯麥,希特勒甚至還沒投胎轉世。
換句話說,近代德國史那些讓人掩卷興嘆的故事,其實是臺灣透過殖民母國而接觸德國法的很久之後才發生。法律繼受的母國,事後附上這麼多的「借鏡」,這不知道是歷史之神開的玩笑、送的禮物,還是祂所給予的殘酷教訓。
法律學德國、司改像東歐
同樣由於繼受德國法的歷史背景,在修法、立法乃至於司法改革的種種議題上,「向德國取經」成了通用的起手式。這項訴求固然不是完全沒有道理,希望臺灣的法治水準有一天能跟德國接軌,當然也是值得追求的夢想,只是,講到司法的處境與司法改革的脈絡,臺灣其實是跟波蘭、匈牙利之類的東歐國家比較接近的,因為同樣都有著對司法獨立磨刀霍霍的民粹政治。
今年6月24日,歐盟法院做出判決,宣告波蘭所謂的「司法改革」侵害司法獨立,進而違反歐盟條約。波蘭在2018年修法,將該國最高法院法官的退休年齡從70歲降到65歲,已屆退休年齡的法官,可以申請續任,續任與否應由總統決定。
這項法律施行時,最高法院的72個法官中,有27個已經年滿65歲,換句話說,按照這項法律,三分之一以上的最高法院法官,去留立刻就掌握在波蘭總統手中;而人盡皆知的是,決定了審判者,往往就決定了判決結果。
歐盟法院認定這項法律侵害司法獨立,進而違反歐盟條約,理由有二。首先,波蘭政府聲稱,這項法律的政策目的,是讓法官能夠適用跟其他職業的勞動者相同的退休條件,但一一檢驗其細節的結果是,這項法律並無法達成那個目的。
另一方面,波蘭總統在決定是否准予續任時,判斷的要件跟標準是什麼,法律沒有規定,也沒有要求總統必須給個理由;無法續任的法官,也不能聲明不服,更不能就此提起訴訟。這樣一來,續任與否,就完全聽憑總統的裁量,用白話講就是看總統高興,這顯然是侵害司法獨立的。
在前揭案件參加訴訟的匈牙利,在波蘭敗訴的判決出爐前不久,就宣布放棄了所謂的「平行法院計畫」。匈牙利原本計畫成立新的法院體系,專門審理選舉、稅務、貪瀆案件,而且,這個法院體系,將不受司法委員會的管轄,而是直屬司法部。
司法委員會設立的目的,原本就是要讓法院跟政治部門保持距離,以維護法官的獨立地位,但「平行法院」卻又繞過司法委員會,而由身為內閣部會的司法部直接管轄。這些審理選舉、稅務、貪瀆等等敏感案件的法官,能不能維持應有的獨立性,非但令人存疑,法院直屬於政治部門的設計,更有一口氣把一整批的法官給行政官化的危險。
反觀臺灣,職業司改家跟聰明司改學者們爭論檢察官該不該行政官化,吵了30年都沒有結果;監察委員想要法官改姓「黨」,還得透過個案干預,一件一件的伸手進來「調查」(他對媒體放話說要調查之後,是不是真的能立案,其實還很難說),比起匈牙利執政黨的頭人,臺灣的司改菁英根本就看不到車尾燈啊!

讓司改列車脫軌的「威權遺毒」想像
臺灣固然未曾有過波、匈兩國那樣的民粹政府,威權統治所造成對司法先天上的不信任,仍然會跟民粹政治結合,每當爭議案件與爭議裁判發生時,人民往往將裁判結果的不滿,跟威權時期的司法黑歷史連結,威權遺毒、恐龍、貪污的標籤,也就一個一個的貼上來。
無論這樣的連結是真實的還是想像的,一旦掛上這個連結,就很難再有真切的檢討了。對心存不滿的民眾、政客、名嘴來說,「威權遺毒」的標籤早就貼上去了,還有什麼好檢討的?對司法人員來說也一樣,「威權遺毒」的黑鍋都背定了,還有什麼好檢討的?
筆者當然認為,這個「威權遺毒」的想像泰半只是想像,這裡只需要從一點切入:解嚴已經30年了,你要說威權遺毒在司法體系中流竄至今,你必須假設,這30年來,法學院的教授在課堂上都不談民主法治的崇高理念、對威權統治時期的司法也毫無批判;你必須假設法學院的學生不知道當時的司法有多糟糕,就算知道了也是不假思索地全盤接受。
你還必須假設,即使法學院教給學生什麼反思批判的能力、帶學生認識威權司法的黑歷史,他們考上司法官後,司法官學院(原司法官訓練所)都能把它抹得一乾二淨(甚至如同某司改團體所寫的,在司法官訓練所吃了時任所長的林輝煌的口水,都會變成美麗島大審當時軍法官的形狀、判決裡都會「存有跟所長相同的基因」)。
最後你必須假設,這麼多坎都給它闖過去,在每一個現職法官身上業力引爆——這奇妙的邏輯,不就是第一版的普悠瑪號出軌事件調查報告嗎?
如果那場交通事故,你認為不該讓種種情況累積到最後,再由司機員一個人負起全責,你為什麼又會用這種邏輯,來看法學教育跟法曹的選拔培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