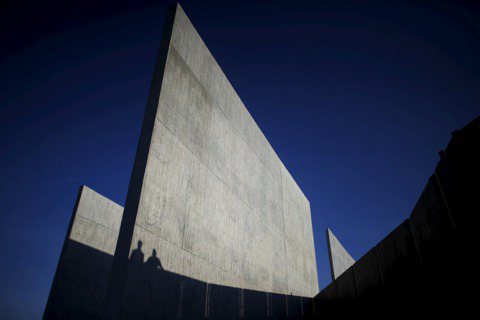時空錯置的黨國遺緒:廉價的吞球彈劾案,崩盤的民主法治

我出生的時候,還沒解嚴。至少到我國中之前,家裡支持黨外/民進黨的長輩,每次選舉被問到投給誰,都說不想講,其實是不敢講、不能講。我小時候還親眼看過買票,是樁腳拿著錢,在公寓裡挨家挨戶按電鈴,亮出鈔票說「這XXX候選人拜託」。他一開始是怎麼打開公寓大門的,就不得而知了。總之,這是我生長的年代。
某個小我一屆的學弟曾告訴我,他的碩士論文要偷帶一個註腳:「由於筆者並非生長在民主國家……」,諷刺民主自由得來不易,臺灣社會竟也不加珍惜的奇怪心態。我不知道他最後有沒有真的這樣寫,但碩士論文寫到最後,連我自己也想寫一個這樣的註腳了。只是想歸想,最後沒有真的寫下去。
會有這樣的感慨,是因為在撰寫碩士論文的過程中,稍微摸到法學界的黑歷史:《法學叢刊》曾有一期專刊,極盡諂媚的鼓吹修憲、支持老蔣不知道幾連任;《法律評論》每期翻開就有社論,為黨國發聲,毛邦初、吳國楨、槍殺劉自然的羅伯特・雷諾(Robert G. Reynolds)、雷震等人,都曾受到它的撻伐;《法令月刊》的「夏蟲語冰錄」專欄,一開始的作者是張知本,他是老蔣的文膽,雷震被捕的時候,他參與抹黑《自由中國》相關人等的宣傳工作。
年輕司法官的幸福與哀愁
法律人忘記了嗎?與其說忘記,不如說一開始就不曉得。我碩論初稿完成,報告給同門研究生聽的時候,指導教授的評論之一,就是「大家都忘記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有多重要了」。其實不是忘記,而是生活在時空彼端的我們,不太有機會能感受,當時曾經一度它是多麼「重要」。
現在的司法官,不曉得以前的司法多黑,這是幸也是不幸。現在的司法官群體,早就把關說、行賄、政治干預視為洪水猛獸,在這樣的時代廁身法曹,自然是幸福的。順道一提,我升任實任法官時,可是蔡英文總統發的任命令,我可以告訴我在荷蘭擔任訪問學人時認識的教授們:這是推動同性婚姻合法化的總統頒給我的。
不幸的是,在這樣的時代擔任司法官,還沒辦過一個案子、還沒寫過一件裁判、還沒開過一次庭,甚至還在受訓,就要背負黨國、威權的原罪,同時也貼滿了恐龍、奶嘴的標籤。總是有人不知道或不願意承認,時代已經不同了。
還有一些司法界的前輩,動不動就「現在的年輕司法官都不曉得以前怎樣怎樣」。欸學長你又不是大我幾歲,你的以前是多久以前?還是你的言外之意其實是,「你不曉得我們以前為司法付出多少」?
至於我們對外澄清、闢謠的舉動,這些司法前輩還要嘲諷「現在的年輕司法官就是太愛司法,受不了任何的批評」。欸我沒做的事情不要算到我頭上來,這不是做人做事最基本的道理嗎?難道人當了司法官,名譽榮譽人格都自動歸零,hông幹隨人嗎?
我跟江湖人稱司法唯一最後良心的法官前輩,就是這樣鬧翻的:某案件當事人謠傳我收了建商兩棟房子,這位前輩卻要我反省檢討。就沒有的事情有什麼好反省檢討的?你會叫被關超過30年、被刑求、被逼供、被冤枉判死的邱和順去反省檢討嗎?
話說回來,以前的司法多黑,黨國體制又是透過怎樣的手段來滲透、掌控、操縱司法,不要說現在的司法官不曉得,成天辱罵黨國遺緒的政客名嘴刁民們,恐怕也不是真的知道,而沒有真相、沒有事實,轉型正義就只能淪為騙人的玩意兒。
有鑑於此,2017年底,筆者有幸能與幾位志同道合的司法官夥伴共同舉辦「台灣司法史研習會」,我們邀請研究司法改革的學者,以及曾親身參與司法改革的法官、檢察官們,分享他們的心得與經驗。我們期許自己能夠做個有記憶的司法人,因為了解過去,才能告別過去。
時空錯置的「黨國遺緒」
監察委員高涌誠、蔡崇義違法濫權彈劾檢察官,引起司法官群體幾近於憤恨的反彈,全國律師公會聯合會與全台灣(除了台北律師公會以外的)律師公會也發表聲明,反對監察委員以政治因素介入干涉檢察權,監察委員陳師孟則指責反彈的司法官們為「黨國遺緒」。我所敬愛的林臻嫺法官投書媒體點評:
而今天,被監察院選擇性彈劾的年輕檢察官,以及在知道駭人聽聞的彈劾案時,會氣憤地自發性集體連署抗議,勇於向政治黑手說不的年輕司法官們……在民主自由的今天、政黨輪替的現在,竟仍會遭遇到應已是歷史塵埃的政治干預司法事件,會非常不可置信地悲憤莫名。
然而,這些只懂得司法獨立、卻不懂得忠黨愛國的年輕司法官們,可能更無法理解的是,為什麼會被一個爺爺是國民黨忠黨愛國的重要文膽,自己則是民進黨忠黨愛國的監察委員,扣上一頂「印證黨國遺緒在台灣司法體系的代代相傳、陰魂不散」的帽子,這無論如何,聽起來都讓人有種時光錯亂的不寒而慄感。
對我來說,「不可置信」之處未盡於此。在陳師孟擔任監察委員之前,我對他的印象,還停留在《外省人台灣心》一書中,那個有點笨拙、但非常溫暖的形象。
他被提名監察委員之後,對司法官群體濫開地圖砲的模樣,卻活像是不知今夕何夕的「老番顛」,不知道現在已經是2019年,更不知道這30年來,台灣的法學有多大的進展;這30年來,多少在解嚴、終止動員戡亂之後才接受法學教育、成為法律人、進而成為司法官的新血,已經注入司法體系。
要不是因為這些「不知道」,又如何能像開罐頭一樣地輕易端出「黨國遺緒」這種制式回應?
當「黨國遺緒」成為如此廉價的髒話,當這樣的髒話扣到我這個世代、我後面那些世代的司法官頭上,我忍不住想看一下自己任命令上蔡英文總統的印章,並且卑屈又無力地問道,曾經為了打倒黨國體制而犧牲身家性命的民主運動前輩、曾經為了追求司法獨立而提頭辦案,甚至丟官去職的司法前輩們,知道自己換來的是這樣的民主自由憲政法治,又將情何以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