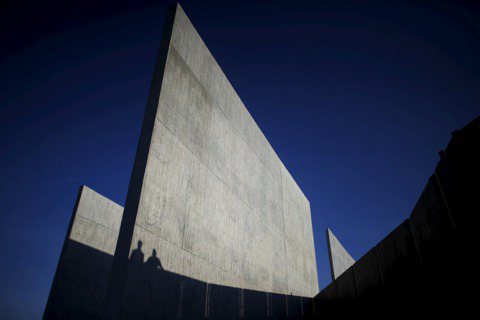血與文化權利:《原住民身分法》憲法法庭言詞辯論側記

千年傳統,國家標準
2022年1月17日,憲法法庭在《憲法訴訟法》施行、釋憲新制上路後,第一次進行言詞辯論程序,辯論的主題是《原住民身分法》若干條文的合憲性。這部法律主要規範原住民身分的認定,其中第1條第1項就開宗明義地規定:
為認定原住民身分,保障原住民權益,特制定本法。
《原住民身分法》的存在意味著,這個國家有一部法律,專門在規定原住民身分的認定及其得喪變更;換句話說,一個人是不是原住民,必須按國家制定的法律判斷。這無可避免地會引來尖銳的批判:誰是原住民,憑什麼是國家說了算?同樣的問題還有更尖銳的問法:誰是原住民,憑什麼是漢人國家說了算?
一旦我們把法律擺回它原來的位置,如此尖銳的提問,就會顯得脫離現實。國家之所以要認定誰是原住民,是因為這就是它分配權利或資源的標準,如果原住民身分的存在與否,是國家分配權利或資源的標準之一,國家就必須要決定,誰是、誰不是它所要保障的原住民。
如果原住民身分乘載著國家所授予的權利、給予的資源、課予的義務,如果原住民身分必然連結到某種利益(還有隨之而來的利益衝突),誰才是國家所謂的原住民,非得要有人說了算。在我們這樣的民主國家裡,任何人都可以批評國家所採行的標準,但批評「國家說了算」這件事,質問國家憑什麼說了算,其實沒有太大意義。
比加分更重要的事
講到原住民身分所帶來的利益,許多人第一個就想到考試加分,然而,從過去一年幾個重要的司法實務見解來看,這個議題涉及的層面,遠比考試加分的爭議還要深邃。
例如,原住民狩獵案(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803號解釋),涉及原住民持有自製獵槍及獵捕宰殺野生動物的權利,這項權利受到《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槍砲彈藥刀械許可及管理辦法》、《野生動物保育法》等法規的承認,而這號解釋所處理的問題是,既有的規範,是不是規定得不夠明確或不夠完整。
再如原住民保留地的借名登記案(最高法院大法庭108年度台上大字第1636號裁定),依《山坡地保育條例》及《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規定,國家劃定的原住民保留地,屬於私有土地者,所有權人必須是原住民,而在借名之島台灣,利用人頭的土地買賣到處都有,在山上也不例外,這號裁定要處理的問題就是,依法不得購買原住民保留地的非原住民(pài-láng,俗稱漢人),可不可以透過借名登記,利用原住民人頭買地。
無論是大法官還是最高法院,都明白地以傳統文化權利作為其立論基礎,如此一來,一個人可不可以說,我不拿槍、不打獵,就不覺得自己是個完整的人,取決於他是不是原住民;一個人能不能買受原住民保留地,或是透過借名登記支配原住民保留地,同樣取決於他是不是原住民。

想要文化,先問血統?
在1月17日的憲法法庭上,各方交火的標的,是《原住民身分法》第4條。依該條第2項規定,原住民與非原住民結婚所生子女,是否取得原住民身分,取決於從姓。舉例來說,如果某人的爸爸是福佬人,媽媽是布農族人,而他本人是姓爸爸的姓,他就不是國家所承認的原住民;他必須從母姓,才能取得原住民身分。
本項規定顯然預設,原住民要不全都擁有如同漢人的姓氏制度,要不就通通都改了漢姓。這項預設固然不盡合乎現實,有其窒礙難行之處,但弔詭的是,姓名具有表彰血緣、族裔與認同的功能,一旦拿掉了從姓的要件,一個人是不是原住民,就全然取決於血統,無關文化,也無關認同。
換句話說,一旦拿掉了從姓的要件,一個人將會只因為有原住民的血統,就成為國家承認的原住民;一旦拿掉了從姓的要件,原住民身分的構成,將會全然以血統為基礎,不是語言、不是文化、也不是生活方式,甚至可以說,將漢人的姓氏觀念套在原住民身分的判斷標準上,無疑是汙染原住民純淨的血。
一旦拿掉了從姓的要件,一個人將會只因為身上流著原住民的血統,就理所當然地享有原住民之文化權利;如此一來,一個人可不可以說,我不拿槍、不打獵,就不覺得自己是個完整的人,取決於他有沒有原住民的血統。
如此一來,一個人能不能買受原住民保留地,並且在土地上開民宿,取決於他有沒有原住民的血統。如果沒有,就連長年來為借名登記大開後門,如太平洋般寬廣、如銀河般遼闊的最高法院,都要對你緊閉門窗。血緣跟土地之間,果然存有某種,漢人無法參透的神秘連結。
從姓還是只有從姓
族群是個人所能享有的一種身分,這種身分具有社會、文化上的意涵,透過血緣跟這些意涵連結,不是絕對不行,只是這種做法很容易遭到質疑,這個族群的身分,除去血統純正,還剩下些什麼?為什麼一輩子拿著筆桿的讀書人,只因為有著原住民的血統,就能夠享有拿槍打獵的集體文化權利?
從這個角度來看《原住民身分法》,或許問題並不是在血緣之外設有從姓的要件,而是除了從姓,它沒有為其他表徵身分認同的符碼留下空間。至於這個「其他」會是什麼,又如何建構當代社會的原住民身分,就不是三言兩語講得清楚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