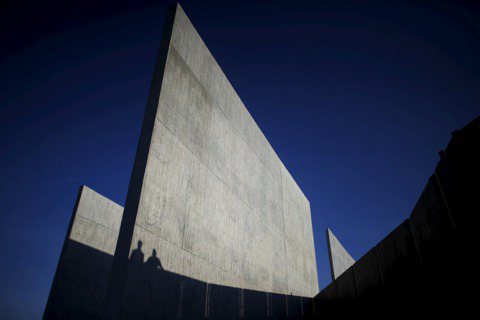立足於審判之外的法官倫理?從司法風紀案件談操守的悖論

上週一(18日),司法院與法務部針對司法高官涉嫌與富商不當來往的風紀案件,分別公布調查報告。調查報告的公布,原本是要給社會一個交代,卻反而招致更多的批評,而一如以往,隨著爭議的升高,各方的意見也變得繁多、紛雜。
法官的操守至關重要,這彷彿早就是自明之理,再也不需要更多的論述。不過,正如筆者在評論免費便當案的文章裡曾經指出的:
強調公眾對司法懷有極高的期待,或是引述「能夠成為法官,是一種特殊的榮譽,因此應該要有與這份榮譽相襯的舉止」之類名言錦句,都只是好聽而已,沒有實質意義。如此吹捧身為法官的殊榮,無法幫助我們理解,《法官倫理規範》到底要求或禁止什麼樣的行為。
同樣地,光是反覆強調法官的操守多麼至關重要,其實也無法幫助我們理解,我們到底能夠以操守之名,要求(以及非難)法官到什麼程度。
法官操守與獨立審判
廉潔的操守是所有公務人員共通的責任,儘管隨著《法官法》的施行,法官任用關係已另有定位,並且獨立於其他公務人員的任用關係之外,這樣的規定其實也間接確認,作為職業倫理上的要求,法官的操守,理當比其他公務人員受到更加嚴格的檢視。
職業倫理的規範,如果沒有根植於職業本身的考量,其正當性就很容易受到質疑,而法官倫理對於法官操守的要求,可以追溯到司法獨立的內在面向。在這個面向上,司法獨立意味著,法官跟承辦案件的勝敗結果沒有利害關係,法官個人的利害考量也就不會影響案件的勝敗結果。
讀者或許會說,所有的公務人員,在執行職務時,都不該受到個人利害的影響,不是只有法官。沒錯,但操守的要求在法官身上之所以尤其強烈,是因為司法的核心事務是審判,審判的對象是紛爭,而儘管大多數案件的裁判,都只是照本宣科、行禮如儀的日常瑣事,人們的目光卻多半投注於疑難案件。
疑難案件之所以疑難,或者因為沒有一翻兩瞪眼的明確事證,或者因為找不到對應於個案事實的法律規範,也可能是因為,特定個案引發的爭議,超出了立法者在立法當時的設想,適用既有規定的結果令人無法接受,法官因此面臨個案正義與裁判一致性的兩難。
台灣的法制背景讓情況更加艱難。我們在日治時期就開始繼受歐陸法系的現代法律制度,二戰之後,中華民國政府把清末以來繼受歐陸法律的事工,從中國整套搬來。台灣法制的基調,從很久以前就已經不是傳統中華法系那一套,但市井小民的法治觀念跟法律文化卻遠遠沒有跟上,由於制度與文化的落差,即使不是疑難案件,司法裁判也可能會引起輿論的猛烈抨擊。
由於諸般的現實,在許多案件,大多數人都能接受的判決結果或理由,並不存在,有些案件就是注定討罵,不管怎麼判,就是等著被罵,差別只在開罵的是哪一邊而已。
法官常常要作出有爭議的決定,而這些決定是對是錯,找不到客觀標準,不像數學算式一樣可以驗算,也不像酸鹼值一樣可以用石蕊試紙測試。遠的不說,太陽花學運衍生的諸多訴訟,這幾年來就一再上演雙方輪流高喊「司法已死」(或毋寧說輪流殺死司法)的戲碼。
如果我們無法要求,對於人民享有什麼權利,法官總是要有萬民擁戴的答案,至少我們能要求,法官必須認真對待權利。至少我們能要求,司法機關必須讓各方當事人透過公正的程序提出證據、呈現的訴求,再由作為中立第三人的法官,本於法的確信做成判斷,並且盡可能首尾一貫地說明,做成這項判斷的理由。
要維護這套機制,就必須確保法官作為中立第三人的地位;要確保法官作為中立第三人的地位,就必須杜絕不當的外力干預,防範不當的利益考量。前者有賴賦予法官相對應的身分保障,後者則衍生出對於操守的嚴格規範。
抓住結論、放掉前提?
鋪了這麼長的哏,終於要講到標題裡的悖論了。請容我再次提醒讀者,法官的操守之所以這麼重要,是職務性質使然,是因為我們的工作關係著人民的身家性命,更因為我們必須常常作出天生就無法服眾的決定。學者可以透過研究課題的選擇而避免涉足爭議,法官卻不能因為爭議的存在而拒絕裁判。
所謂的悖論就在於,儘管人民是以這麼嚴格的標準檢視著法官,儘管嚴格的操守要求背後有著這樣的前提預設,許多對於司法的批評,卻講得像是疑難案件並不存在、個案裁判引起的爭議也都只是假象,宛如法官必須判斷的一切問題,都會有簡單明瞭的答案,甚至裁判的對錯就像數學算式一樣可以驗算,像酸鹼值一樣可以用石蕊試紙測試。
過去幾年,政治人物論及司法改革時,言必稱社會期待或國民法律情感的行徑,就讓它更進一步地演化成了雙重悖論。第一重的悖論當然在於,抱持這種說法的政治人物們似乎認為,司法裁判的好壞對錯,必須遵循一個簡單明瞭的判斷標準,那就是社會期待或國民法律情感,至於法律,那是法學菁英傲慢的藉口,拜託靠邊站別擋路。
第二重的悖論在於,他們似乎也認為,社會期待或國民法律情感是昭然若揭、毫無爭議的判斷標準。然而,正如每個政治陣營都能毫不臉紅氣喘地自稱代表主流民意,對司法心存不滿的每個人,也都能安安穩穩地為自己披上社會期待或國民法律情感的外衣。
法官倫理的重建?
長期接受他人餽贈、供養的法官,已經一腳踩在法官倫理的紅線上,即使他未曾經手這個「他人」的案件,也是一樣,因為這樣的行為足以讓人懷疑,他們會不會在處理某些案件的時候,無視個案中的證據、事實及法律,卻讓個人的利害考量左右裁判。
然而,在法官依法裁判的責任之外,用個案中的證據、事實及法律以外的東西,要求或責難司法,卻也早就成了台灣的政治言說中不可或缺的一環。在論者高呼重建司法倫理的同時,如果不同時確立「法官應依法裁判,不多也不少」的前提,還繼續要求法官服膺社會期待或國民法律情感,就難保不會重演脫離現實的盲動戲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