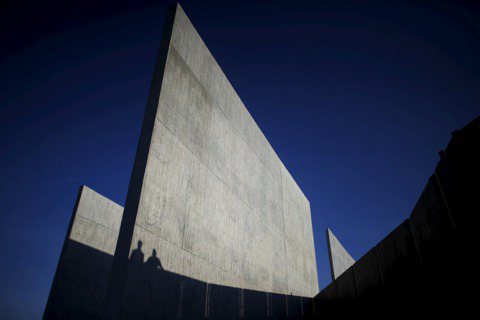在軍法判決尋求司法轉型正義,是否搞錯了什麼?

司法轉型正義的迷思
臺灣人對近代史有一些常見的迷思,例如,誤以為(身為日本殖民地的)臺灣曾在二戰時遭到日軍轟炸,分不清楚(訓政時期的)國民政府跟(戒嚴時期的)國民黨政府,最近還聽說,有些人所謂的「民國初年」,指的是二戰後的那幾年。
關於近代司法史,有個常見的迷思是,司法機關參與了戒嚴時期的白色恐怖案件。有些人因此將司法官視為「威權遺毒」的象徵,更有人拿著白色恐怖案件高呼,必須進行司法轉型正義。
事實上,按照《戒嚴法》第8條、《臺灣地區戒嚴時期軍法機關自行審判及交法院審判案件劃分辦法》等相關規定,「匪諜」、「叛亂」之類的白色恐怖案件,基本上是由軍法機關審判,不關司法的事。
「軍法」(軍事法院、軍事檢察署)跟「司法」(法院、檢察署)是不同的機關,有不同的組織、由不同的人員組成,適用不同的訴訟程序、審理不同的案件,光是名稱看起來就不一樣了!拿著「軍法案件」來批判「司法不公」、鼓吹「司法轉型正義」,根本就搞錯了對象。
當然,這並不表示,司法案件裡面沒有轉型正義的課題,只不過,它們跟白色恐怖案件往往沾不上邊,反而藏在看似稀鬆平常的刑案,甚至出現在行政訴訟或民事事件裡。
這個區分之所以重要,因為這麼基本的史實,本來就不該弄錯,而拿著軍法案件要司法負責,悖離轉型正義的意旨,更是完全起不了反省檢討、防治濫權的作用——就不是司法做的,你叫它反省檢討有什麼用?套用筆者三年半前就寫過的:
當你拿著重大政治案件,在悼念白色恐怖的受難者之餘,洋洋得意地細數你以為的司法不公時,我卻也聽到當年那些司法官僚在背地裡偷笑:「說什麼轉型正義,原來連我們辦過哪些案件,都搞不清楚啊!」
促轉會的混淆
兩個禮拜前的週日,史明歐里桑告別式的那一天,促轉會就犯了這樣的錯。它在臉書粉專分享了顏世鴻前輩的故事,一起手就是「平反司法不法」,擺明了把這個軍法案件算在司法的頭上。
或許是因為看到司法流言終結者的批評,促轉會也在幾天之後貼出回應。然而,促轉會的回應,並沒有真正的回答問題。
首先,促轉會引用促轉條例第6條第1項,認為就法條的字面意義來說,這項規定指稱的「司法不法」,本來就沒有軍法跟司法的區分。確實,筆者也同意,從字面意義就看得出,這項規定沒有區分軍法跟司法。但就促轉會面臨的質疑而言,這不是有效的回應。
促轉條例的這項規定,只是顯示立法者不曉得(或更可能是不在乎),軍法跟司法是不同的機關,而執法者理當比立法者更聰明,促轉會的回應卻把立法者的錯誤照單全收,跟它所標榜的「導正法治及人權教育,並促進社會和解」,恰恰是背道而馳的。
身負落實轉型正義重任的促轉會,應當比誰都還要清楚,臺灣社會普遍存在著軍法司法不分的刻板印象,卻仍照本宣科地引用法條,將軍事審判囫圇吞棗地蓋上「司法不法」的印記,結果就是悖離史實,加深司法承受的負面印象,製造另類的轉型不正義。
其次,促轉會也指出,促轉條例第6條第1項「特別提及國安法第9條,也可以看出立法者很明白地將司法不法的概念擴及於不法的軍事審判。」同樣地,這也不是有效的回應。
按《戒嚴法》第10條,白色恐怖的受難者,本來可以在解嚴後向普通法院尋求救濟,國安法第9條卻把救濟之門關起來,不准上訴、抗告,而大法官釋字第272號解釋更宣告它合憲。
正是基於這樣的背景,促轉條例第6條第1項才要特別規定,應重新調查威權統治時期的不當審判,且其調查「不適用國家安全法第9條規定」。
儘管如此,促轉會指向國安法第9條的作法,並不恰當,因為:
- 促轉條例第6條第1項將軍法與司法混為一談,這是立法者的錯誤,而促轉會這部分的回應,仍然是把立法者的錯誤照單全收。
- 《戒嚴法》第10條的救濟之門,國安法第9條把它關起來,而白色恐怖案件仍然是軍法判決,沒有因此變成司法判決。
- 國安法第9條是立法者三讀通過的法律,不是法院的裁判;受難者無從救濟,不是因為司法拒不受理,而是因為立法者禁止司法給予救濟。
- 聲稱作成釋字第272號的大法官也屬於「司法」機關,於事無補,因為這無法改變前面這些既定事實。
判決是軍法機關判的,不准向司法救濟是立法院三讀通過的,這樣也叫司法不法、這樣也是司法機關的責任,會不會太扯了一點?
再次,促轉會援引大法官釋字第436號、第624號解釋,聲稱:
軍事檢察及審判機關所行使之追訴、處罰權,亦屬國家刑罰權之一種,具司法權之性質。因此,並不是「軍法」案件就絕對不在「司法」不法的範圍內。
這項回應,如果是作為憲法上的論證,自然有其意義,但若作為史實的陳述,卻犯了時空倒錯的史學大忌,就像用中華民國民法上關於要約承諾、物權行為無因性、登記生效等等規定,解釋清代的土地買賣那樣的時空倒錯。
釋字第436號在1997年作成,釋字第624號則在2007年公布,都已經是民主轉型之後了,可想而見的是,這兩號解釋對軍事審判的理解,跟戒嚴時期的法規與實踐,有著天壤之別。
戒嚴時期的主流法學理論認為,軍事審判屬於統帥權,而不是司法權,1955年《軍法專刊》上的〈軍人犯軍法以外之罪由軍法審判有問題嗎?〉一文,標題就把這個觀點道盡了:軍事審判屬於統帥權,怎麼會有問題?
對於「軍法不是司法權」、「軍法屬於統帥權」的陳舊觀念,你大可以批評它們威權遺毒;而大法官之所以必須透過兩號解釋,一再強調軍事審判具有司法權之性質,也正是就是為了清除威權體制殘餘的錯誤觀念。
然而,轉型正義是面向歷史的工作,而促轉會似乎沒有意識到,釋字第436號、第624號所謂「軍事審判具有司法權的性質」,是法治國的憲法理論,不是威權統治的法律實踐。硬是套用這兩號解釋來說明當年的軍法,就免不了以今非古、扭曲史實的疑義。
最後,司法跟軍法明明是不同的機關,促轉會以「軍法具有司法權的性質」為由,將兩者混為一談的結果,也就連帶造成非常嚴重的邏輯謬誤。
軍事審判具有司法權的性質,但軍法判決仍然是軍事法院的責任,不能叫司法機關背黑鍋。否則,基於相同的理由,國安局不願意配合解密檔案,我就可以抨擊促轉會反對轉型正義,因為一樣「具有行政權的性質」啊!
小結
英國史學家E.H. Carr在《什麼是歷史?》(What is History?)——沒錯,《正義辯護人》曾提及其人其書——一書中指出,好的史家必須要對過去具有「想像的理解」,他不說「同情的理解」,因為「同情」太容易被誤認為「同意」。
本文之所以強調,要從威權統治的法規跟理論來看待當年的軍事審判,不是因為贊同那些規定或理論,也不是因為支持當年的法學者(以及其他社會科學研究者)為當年統治者提出的種種反動論述。不,它們錯得離譜。
然而,只有在我們試著想像的理解,當年的法學菁英如何地支持那些荒謬、愚蠢甚至可笑的理論,並在這樣的理解上看待當時的軍事審判,我們才能更明瞭,白色恐怖案件是怎麼製造出來的。
促轉會堅持軍法與司法不分的行徑,本身就已經夠匪夷所思了,它的混淆更是取消了歷史的這些面向。這恰好反映了司法改革一再落入的困境:無法面對並檢討司法第一線的實態,只是反覆確認民眾對司法的負面印象,不但沒有對症下藥,反而越是改革,司法就越沒有公信力。
白色恐怖案件是由軍法審判,司法有自己的轉型正義課題,不要拿軍法判決給司法潑糞,如果連這麼基本的史實都弄不清楚,我想當年那些司法官僚還是在背地裡偷笑:「說什麼轉型正義,原來連我們辦過哪些案件,都搞不清楚啊!」司法的轉型正義,豈不是更遙遙無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