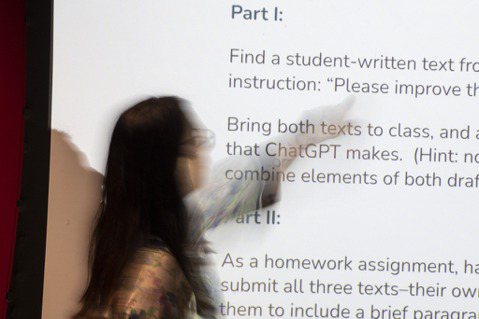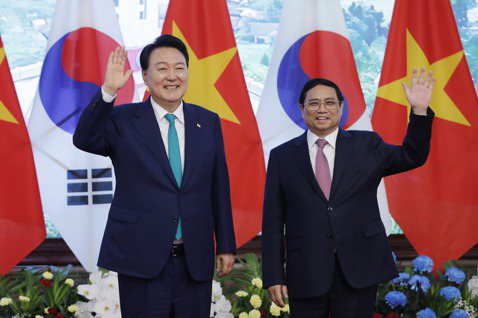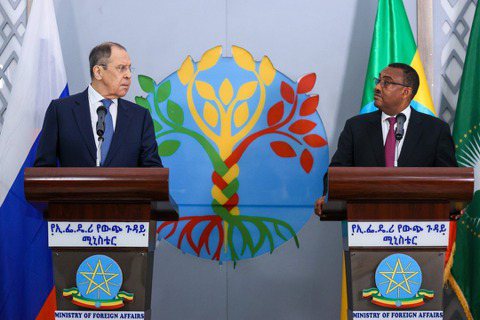後疫情大挑戰(四):瑞典錯了嗎?難以論斷的防疫戰略抉擇

當COVID-19蔓延為大流行,疫苗仍尚未問世前,大多數國家採取的共同策略主要是封鎖城市或居家隔離,作為打破病毒傳播鏈的措施。然而,位於北歐的瑞典採取了不同的方法,即透過最小干預——小學、餐廳、酒吧等場所仍然開放,並鼓勵公司自行決定員工是否在家工作,對抗疫情爆發。
當時的第三次勒夫文內閣(Löfven III Cabinet),委任國家流行病學家泰格內爾(Anders Tegnell)掌舵,以緩解病毒傳播速度為目標,也就是希望透過拉平感染曲線,避免過多人民染疫,拖垮醫療體系。在此前提下,瑞典政府拒絕執行WHO關於封鎖和隔離的指導方針,而是強調個人責任,才是防疫關鍵。
以低度管控換取群體免疫
這並不是說勒夫文內閣躺平不做事,而是視情況動態調整政策。像是2020年其他歐洲國家在3月中旬嚴格封鎖時,瑞典僅禁止超過五百人的公共集會,並在3月底禁止超過五十人的公共集會。對此,政府表示是為公民提供充分的自主權,因為COVID-19大流行是一場馬拉松,而不是短跑,實施嚴格措施的國家,其公民最終必定不會遵守。
部分瑞典的科學和醫學界人士一直呼籲採取更嚴厲的措施,因為自由放任方法的代價太高。自COVID-19大流行以來,瑞典的致死率與美國相近,政府也缺乏整體戰略、反應混亂,對弱勢族群造成顯著的損失。且即使政府否認,也有媒體披露政府是想藉由最小封鎖,達成群體免疫。

在COVID-19大流行期間,勒夫文內閣並未面臨強烈的政治攻擊,只有右翼民粹政黨瑞典民主黨提出零星批評。雖然瑞典國內染疫致死率偏高,但大多數政黨仍支持政府,這也反映了瑞典民眾的立場——犧牲弱勢、為中上階層打造一如往常的環境。有些學者因此抨擊瑞典由上至下過於保護自身形象,而不是著重於拯救生命或是以科學證據抗疫1。
如今回頭來看,瑞典染疫死亡人數約為兩萬出頭,死亡率為0.8%。相較於西方諸國,實施嚴格封鎖的澳大利亞為0.1%、紐西蘭為0.1%,實施相對嚴格封鎖的德國為0.5%、法國為0.4%,瑞典的表現不如預期;但對照實施部分封鎖的國家如英國為0.9%、美國為1.1%,瑞典似乎又差強人意。
西方雖然被簡單歸屬為一個文明,但各國文化、社會、政治、經濟條件都有差異。北歐五國生活方式較為相似,通常會進行比較。若對照斯堪地那維亞夥伴,挪威為0.3%、冰島為0.1%、芬蘭為0.5%、丹麥為0.2%,瑞典顯然落後,然而五國人口比例與密度懸殊,將致死率高低簡單歸因於封鎖與否也不見得公允。
「踩著屍體前進」的防疫成果?
更值得關注的,應是所謂的超額死亡(excess mortality),即是可直接或間接歸因於新冠疫情的死亡人數,像是在醫療系統超載下無法獲得常規醫療服務而死、或是因封鎖導致交通事故減少而使死亡率下降亦有可能。由於各國的計算方式、統計能力等因素不一,通常會低估新冠疫情影響,超額死亡較能客觀反映當地實情。
相較之下,澳大利亞與紐西蘭都呈現負數超額死亡,這表示雖然有人感染COVID-19喪生,但卻因為施行封鎖政策,而讓同時期死亡率下降。若不算經濟、社會等損失,對國家反倒是好事,凸顯福禍相倚的古訓。在北歐五國,只有冰島的超額死亡呈現負數,但冰島人口太少、難以類比,瑞典的表現與丹麥、芬蘭差不多,但輸給較為嚴格封鎖的挪威2。

同樣的,瑞典的超額死亡也比實施封鎖的法國、德國、英國、奧地利等都來得少。如果將封鎖視為對抗新冠疫情的最主要舉措,瑞典的案例可能代表其人民比一些國家較為健康、也可能是醫療設施較為充足,但更可能是驗證了瑞典政府的論點——部分西方國家的封鎖不如瑞典的自主抗疫有用。
瑞典仰賴人民自主抗疫之所以能得到效果,其實是公眾和政府之間的信任所致。一方面瑞典人民相信政府能保護他們,一方面政府給予人民充分資訊,有助於建立個人信心和自我效能感,增強人民對採取政府建議的預防措施的信念,並藉由改變自我行為以對抗疫情3。
據調查,有超過80%的瑞典人表示在COVID-19大流行期間調整了自己的行為,像是保持社交距離、避開人群以及在家工作等,移動數據也證實了瑞典人民的確減少了旅行,顯示大多數人民傾向遵守政府的防疫建議。之後各種病毒變體陸續出現,瑞典政府採取了一些較嚴格的限制,包括關閉所有非必要的公共服務等,致死率也隨之起伏。
然而,無論是死一個人、一萬個人或十萬個人,都是生命消逝,當作統計數字來評斷抗疫成績,不符合積極清零人士的道德觀。從這個角度來說,瑞典放棄封鎖,等於放棄國民生命,勒夫文內閣以瑞典人民當作群體免疫實驗,踩著屍體前進換取防疫成果,難道不必被嚴格究責嗎?
為此,挪威政府成立了獨立委員會,包含公衛、經濟、法律、社會等各方面專家,進行新冠疫情的對策審查。結論是瑞典政府的對策基本正確,但在第一波疫情期間應採取更果斷的行動,如限制公共集會來更有效的地控制病毒傳播。此外,由於長照護理的結構性缺陷等因素,瑞典政府在保護老年人和其他高風險族群的戰略可謂失敗。

誠實面對防疫政策的代價
進一步來看,在COVID-19大流行初期,由於醫療資源不足,瑞典政府考慮到80歲以上或身體質量指數(BMI)高於40的患者康復的可能性較小,因此對斯德哥爾摩地區醫院下令,不應讓這些族群進入重症監護室(ICU)。此外,許多療養院都沒有提供純氧設備,因此不少長照住民只能改為服用嗎啡來減輕痛苦,估計第一波疫情有7%長照居民病故。
再加上,瑞典的長照護理一直遭到忽視,像是醫療設備與人力稀缺、照護人員工作條件不佳等,雖然政府在2020年春季推出了幾項保護老年人的措施,但這些措施往往不足且太遲。種種醫療的不平等導致某些族群無法得到較好照護,且獲得公眾普遍接受。讓批評者抨擊瑞典似乎以社會達爾文主義(Social Darwinism)哲學,面對COVID-19大流行。
這讓人想起不久前,著名歷史學家弗爾森(Neil Ferguson)曾撰文表示,COVID-19大流行讓美國人成為心照不宣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者,而中國人則是被關進了全景監獄(Panopticon)。弗爾森這樣看待美國人,那麼對瑞典人應該更不會吝嗇使用此詞。瑞典人肯定不想進全景監獄,但大概也不願意被形容為社會達爾文主義者。
然而,到底什麼是社會達爾文主義,還適合應用在當代面對大流行嗎?當各國政府紛紛鬆綁疫情規定、試圖回歸正常生活時,所憑藉的理由不過就是疫苗打好打滿、病毒變體致死率降低等醫學證據,但醫學界普遍不認為COVID-19大流行已經結束、甚至仍舊視COVID-19為嚴重威脅。
如果將致死率當作結束COVID-19大流行的重大標準;或是將COVID-19疫情與流感相較,就此得出因COVID-19病歿者是可接受的死亡數字,足以承擔的風險,那麼和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差別又有多少?說到底,人類必須誠實面對自己的選擇,認定一切都盡人事後,只好聽天命,否則社會將難以繼續前進。
當然,雖然許多醫學界人士與知識份子恐怕不會贊同,但他們多半還是選擇服從規則並與之共生,一般人也只能在疲憊抗疫後轉向有利於己的科學證據。瑞典,或許只是提前為世人展示了不帶假面具的生活態度而已。

- Brusselaers, N., Steadson, D., Bjorklund, K. et al. 2022. Evaluation of science advice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in Sweden.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Communications(9).
- COVID-19 Excess Mortality Collaborators. 2022 Estimating excess mortality due to the COVID-19 pandemic: a systematic analysis of COVID-19-related mortality, 2020–21. The Lancet(399): p1441-1572.
- Hassan, M.S., Al Halbusi, H., Razali, A. et al. 2022. The Swedish gamble: trust in the government and self-efficacy in the battle to combat COVID-19. Curr Psychol(2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