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玉婷/難以辨識的傷痛:性侵、性騷擾受害者為什麼陷入沉默?

原編按:時值國際丹寧日(今年為4月26日),全球倡議性暴力防治、打破強暴迷思,多多益善以兩篇報導和一則圖文包,透過好幾位倖存者的心聲,釐清性暴力受害者經常不被理解的行為反應與創傷。
本篇為專題第一篇,呈現受害者在歷經性暴力的當下與之後,所面臨的漫長而混亂的釐清過程,再加上諸多原因導致求助困難、言行前後不一、容易被誤解。長期無法述說、獨自吞忍,更造成各種層面的影響。
本專題由現代婦女基金會部分支持,Right Plus多多益善獨立報導完成。
1992年,義大利發生一起性侵案,少女因為當時穿著緊身牛仔褲,最高法院認為他人很難強行脫下,應是少女自願配合脫褲。法官以此判定雙方屬於合意性行為,推翻先前判決,被告無罪釋放。
這樁判決引發輿論怒火,人們紛紛穿上牛仔褲抗議性侵與衣著無關,後續更有團體發起「國際丹寧日」(Denim Day)的全球活動,呼籲大眾在每年4月的最後一個週三穿戴丹寧服飾,為性暴力倖存者的權益發聲,打擊強暴文化。
今年的丹寧日是4月26日。長年推動婦幼人權的現代婦女基金會響應倡議行動,3月更進行「性暴力事件求助態度網路調查」,回收共876份有效問卷,其中293人曾遭遇性暴力。結果顯示,高達九成被害者不敢報警、四成從未向任何人提及被性侵或性騷擾的經歷。
不即時求助,甚至隱忍多年,除了導致受害者獨自承受痛苦,嚴重影響身心,加害者也因此迴避了責任,甚至可能重複施暴;即使日後鼓起勇氣開口,身邊的人,包括警察、司法等專業人士,還可能質疑受害者是否有某種程度的「自願」,形成二度傷害。

沒有同意,就是性侵(only YES means YES)
為什麼有這麼高比例的受害者錯過求助機會、陷入沉默,或被迫噤聲?其中一個原因是,倖存者首先要能辨認自己經歷了性暴力。但許多時候,當事人其實難以意識到自己受了傷。
「我花了很長的時間才有辦法說,那是性侵。」三年前,鍾昌芸(化名)被職場前輩脅迫發生性行為。她憶述:「剛開始我不太理解,人在遭受性侵時會有什麼反應?最初我有拒絕對方,只是後面沒有劇烈反抗,沒有大家想像的、被害人該有的正常反應。我覺得那好像只是普通的一夜情。」
「事後我心裡很不舒服,跟朋友聊到這件事,對方問我要不要去警局備案,我才意識到原來這也是性暴力的範疇。通報後遇到的社工也跟我說,我一開始有拒絕,就已經是代表拒絕了。」
「只是起初聽到性侵或強暴的字眼時,我還是覺得有點當機。會認為我只是沒有自願做那件事,雙方過程卻沒有發生嚴重的爭執或打鬥。後來我才明白,事發當時原來我並不是毫無反應,而是整個人變得僵直⋯⋯會有點抽離當下實際的感受。」
鍾昌芸回想,她的成長環境認識許多具備性平意識的同儕,過去她總認為自己遇到這些事,會很積極尋找解決方法,「但真的發生時,光要爬梳事件和辨識自己的狀態,其實很不容易。」
現代婦女基金會社工李姿瑩解釋,每一個性暴力事件的脈絡都不同,有時連當事人也不太確定「究竟發生了什麼事」,還在辨認的過程。「假設被毆打,那是一個很明確的事實;可是被侵犯的過程,會有一個互動的時間跟脈絡,裡面每個細節都可能讓當事人覺得,是不是我做了什麼或沒做什麼,才會發生侵犯。」

性暴力倖存者匿名社群「暖暖 Sunshine」創辦人湯淨,也整理她曾訪問收集的倖存者故事,歸納出難以辨別性暴力、進而不曾跟任何人求助的兩種情境。
第一是童年受到家內性侵。當事人的家庭環境往往相對較不重視孩子的身體界線,會擅自出現摸頭、拍抱等肢體接觸。有些孩子遭長輩性侵時年僅五、六歲,即使抱持疑問,卻礙於家長視而不見或當成惡作劇,甚至受迫於成年人的權勢,便不再提及。
第二是雙方曾有情感關係,像是朋友或情侶等,加害者可能利用性誘騙,透過鋪陳、預謀等控制手法,讓當事人在關係裡面深陷徬徨,無法釐清現況。包括自己是不是喜歡對方?彼此原本在曖昧或交往就不算性侵嗎?導致在事發當下,很難辨認自己是否真的遭遇性暴力。
針對第二種情境,現代婦女基金會總督導張妙如舉例,曾有倖存者被熟人脅迫侵害後,加害者不停安撫、關心她,使得那次經歷雖然讓她很不舒服,卻越來越混淆。
事發後的三年間,她無法好好說明自己的遭遇,只是每次回想起來總是認為「不對勁」跟「有點奇怪」。她曾向朋友傾訴,卻被敷衍回應,後來鼓起勇氣跟其他友人提起,才發現原來當天的狀況也屬於「性侵」的一種樣態,進而尋找相關單位諮詢。
「有些倖存者,因為無法替自己的經驗找到一個適合擺放的位置,不曉得該如何是好。我們可以協助他做整理跟定義,陪他慢慢釐清整件事。」張妙如提到的個案,如今生活狀態穩定許多,但細數從性暴力發生、向周圍朋友開口試探、尋找管道求助、進入司法程序等,仍花費足足約十年來處理、消化這些傷害,相當漫長。

求助的阻礙:自責羞恥、他人反應、輿論刻薄、加害者權勢
即使釐清了事件的本質,鼓起勇氣發聲的倖存者也未必能被承接。現代婦女基金會的調查顯示,逾五成性暴力倖存者認為過去的求助經驗不如預期。例如,親友會責備當事人沒有保護好自己、小題大作、未陪伴協助處理後續流程,或通報後專業人員的態度不佳等。
在職場案件中,有許多倖存者更會因為性暴力事件被調職。張妙如指出:「長官或主管認為自己在維護當事人的權益、讓員工能有更好的工作環境,對受害者來說卻像是種懲罰。」
發不出求救訊號更是常見的樣態,背後埋藏著無數困難和風險。鍾昌芸便指出,加害者在職場上握有權勢,使她擔心開口會影響職涯發展,加上事件難以啟齒,她很難逃脫不斷出現的自責感,所以當時不太想向工作單位回報。
「社會氛圍告訴我們,不要讓自己陷入會受傷害的環境,所以那時我覺得,讓自己處在孤男寡女的情境,錯的人是我。直到現在,我還是認為自己一定有做錯,是我沒有畫好界線。」她說。
事發隔年,鍾昌芸再度遇到職場性騷擾,這一次她氣憤提報工作單位,也試圖向好友傾訴,卻面臨挫折。「有朋友反問我,可是為什麼會發生?當下我心想,我怎麼知道為什麼?我也想知道為什麼。」
不僅如此,她曾聽其他倖存者和朋友訴說,卻換來「這沒什麼啊」的回應。說者也許無心,單純的一句話卻能對當事人造成很大的打擊。她無奈道:「不是所有人都有辦法幫助自己,也不是每個人都能理解這些肉眼難以看見的傷。」

另一名倖存者戴凱晴(化名),就學階段曾發生熟人性侵,但戴凱晴身邊的同學和朋友,都是經由加害人認識的,且加害人還向其他同學透露雙方「發生關係」。
「我沒有辦法信任其他人,因為我覺得,大家一定更相信他。」事件過後約一年多,戴凱晴都無法跟別人訴說自己的遭遇。期間她恐慌發作、頻繁失眠做噩夢,隨著身心狀態轉差,還曾短暫入住精神科急性病房。
回想當時難以訴說的掙扎,戴凱晴表示:「我擔心別人不相信我,也擔心我之後才說,給人的感覺會不會前後不一致?而且如果開口,對方沒有接住我的話,我能不能承受?我又能否承受對方的不能承受?於是我選擇都不要講。」
「我還是會跟加害者同組做報告,當朋友聊天。我沒有多想,就是想讓事件壓下去,認為所有的身心症狀都不是因為性侵,只是我的狀態不好而已,當時我只想要趕快畢業。」
直到戴凱晴出院後,她開始使用校內的諮商資源,幸好遇到她願意信任的心理師,能夠揭露自己的性創傷。然而這段時間,她得知有其他受害者出現,又讓她陷入另一段內疚。「我有很深很深的罪惡感,如果我早點求助,或許就不會發生這些了。」
戴凱晴當時不願多想的心理狀態,湯淨也有提到,指出許多倖存者不願回想,會發生「解離」的心理防衛機制。也就是一個人面臨龐大的心理衝擊或創傷時,可能會失憶或切斷內在的感受。
「對倖存者來說,遺忘是保護自己的方式。因為決定開口,就等於要跟全世界說我被性侵,打開回憶的鑰匙,當時的片段也會在腦袋裡不斷播放。」湯淨說:「也有倖存者會破壞跟加害者有關的所有物品,就是為了抹滅不好的記憶。」

超過七成加害者是熟人,背叛的恐懼蔓延人際
在如今的科技和討論氛圍下,人們上網能隨時找到關於性的相關議題資料,節目或戲劇以此為題進行討論及創作。近年臺灣也因應深偽技術(Deepfake)換臉、性私密影像外流等犯罪事件,將「數位性犯罪」納入《刑法》等四法,防止各種形式的性暴力。
「即使如此,『性』在社會裡面還是屬於比較隱晦的話題。」李姿瑩觀察,性的傷害通常很難被訴說,有些是難以啟齒,有些是不曉得如何開口,或不確定聆聽的對象會有什麼反應。
並且,性侵害事件高達七成是熟人犯案。根據衛福部去年(2022)的通報統計,案件最多發生在男女朋友之間(1770人),其次是前男女朋友(1156人)跟網友關係(1036人),陌生人反而是其中的少數。
也因此,性暴力對受害者來說,經常意謂著對親近之人「信任的毀滅」,連帶影響到其他的人際關係。「當事人的信任關係被背叛,成為他們難以開口的另一個原因。要講出來以前,往往不曉得眼前的人是否可以相信。」李姿瑩說。
透過各種情境,可以觀察到受害者選擇不求助,往往不是他們不願意,常是迫於環境的驅使無法把求救的話語說出口。長年下來,這些無法傾訴的傷口會全面性的影響倖存者的身心狀態,可能讓一個人變得害怕出門、難以跟他人保持良好的社交關係,甚至出現自傷或自殺等舉動。
目前,大學畢業的戴凱晴投入助人工作。基於過去所學,她已經比多數人更理解創傷樣態和支持資源,但在面對性暴力創傷時,她一樣深感痛苦和孤立無援,並懷抱跟許多倖存者相似的心聲——
我常常覺得很難過。對自己的自責,身心的折磨、別人的眼光⋯⋯
為什麼要承受一切的,都是倖存者?
(本文授權轉載自「Right Plus 多多益善」,原標題:〈「不知道那是性侵,只知道沒有自願」4成性暴力受害者獨自隱忍、從未求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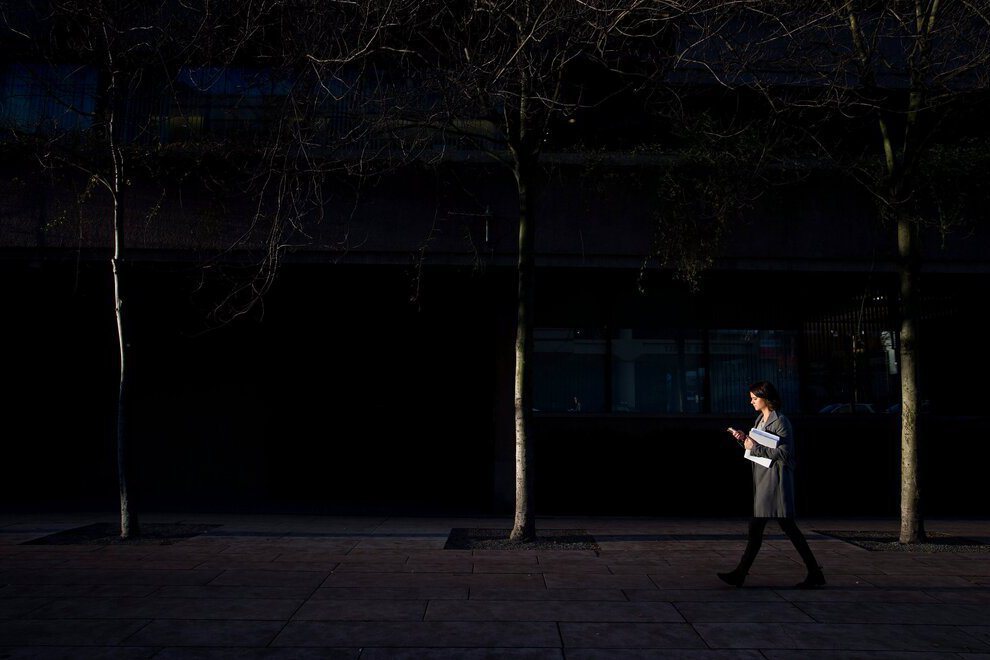
|延伸閱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