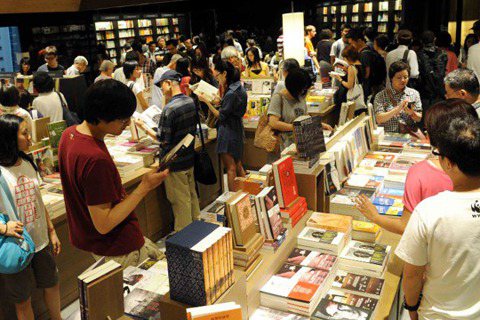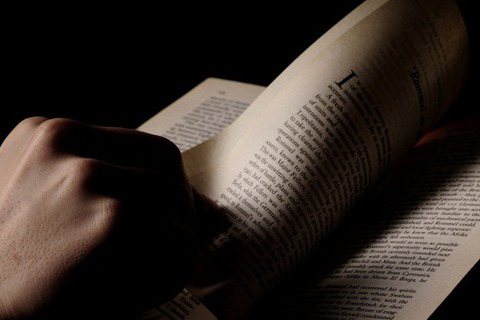「坐立難安」的《粽邪》:斷裂的敘事,生不了的同情

(有微雷,慎入)
要怎麼說故事,觀眾才會覺得精彩有趣?又要怎麼說故事,才能夠把一部還算好看的恐怖片變成無法錯過的經典?這或許是看完《粽邪》之後,我內心興起的疑問。
我私心是喜歡的(因為有夏于喬),但總有地方過不去。
先提提最喜歡的部分,美術很棒。無論是只出現不到一分鐘的辦公室桌面,蚵寮與角色家居擺設,都發散著強烈的「實用至上」的臺灣風格,看了很親切,相對容易投入編導想要傳達的氣氛。至於最後那一場法壇大戰的場景,雖然沒有《雙瞳》真仙觀那樣的壯麗(預算應該差很多),但一致的顏色設定和大量細碎的符咒與道旗使用,也呈現出了臺式美感。
在預算不高的狀況下,透過與故事相關的彰化外景(蚵田、校園、巷弄)搭配小而美的場景,算是非常精巧(畢竟國片預算往往捉襟見肘)。這部片如果成功讓人覺得毛毛的,有一大部分得歸功於美術。
至於演員,多數來看也是不錯的安排。無論是老戲精陳博正,或是與他搭配的外甥劉國劭,都是很棒的綠葉。孫可芳在兇案發生後產生了極端恐懼,從驚訝到害怕再到木然的演出層次精準,可以想像未來一定發光發熱。
那男女主角鄒承恩與夏于喬呢?只能說可惜了。

只有過去,沒有現在的角色刻畫
鄒承恩的台詞沒有安排好,在與劉國劭以外的角色對戲時,都很明顯會處於劣勢:觀眾都會意識到他在演戲。此外,鄒承恩所飾演的角色,在各個面向都是斷裂的,無論是為了追求點擊率而踏入命案現場的冷血工作狂,或是急切想結婚的愛人,或甚至是親切大哥哥,所有面向都沒有聚合成一個,各自發散無法集中。
角色斷裂的問題,同樣發生在夏于喬所飾演的書儀身上。
她的角色只有過去,沒有現在。
這也是《粽邪》敘事過程當中最嚴重的問題,片中採取雙線敘事,從過去與現在同時進行,套句劇中台詞,便是「找到線頭」,去找出一連串鬧鬼事件的源頭到底是什麼。但一再重複的過往場景與橋段,一方面讓人不耐,另一方面也削弱了詛咒為何生成的懸疑。
恐怖或驚悚電影中,最重要的便是「揭下面具的時刻」(unmasking moment),正如《十三號星期五第一集》和《驚聲尖叫》的兇手揭露(竟然是他!),《靈異入侵》中母親打開鬼娃恰基的電池插槽才發現是空的(沒有電,「它」為何會動!),或是《半夜鬼上床》最後的佛萊迪燒傷的原因(原來每個青少年的父母都參與了),或甚至最近的《厲陰宅》系列,無一不是讓鬼怪最後的「現身」帶來最高潮。

但在《粽邪》雙線進行之下,觀眾完全不需要推理,每個人都知道女鬼是誰,就連她想殺的目標清單都清清楚楚。少了懸念,就只是被動地接受訊息。如此一來,便很難感同身受,去理解、接受角色所發生的悲慘。令人百思不解的「為什麼這種事情會發生在我身上」的恐怖感自然大打折扣。
試想,如果《奪魂鋸第一集》在開場不到半小時,就開始進行了「那個人」的生命回顧,等到他最後現身的時候,你是否還會覺得毛骨悚然呢?
另外,也因為雙線敘事的進行,讓女主角失去了「現在」的戲分,這是最可惜之處。試問,夏于喬在「現在」這個時間線,除了當人肉快遞、對男友和夥伴生氣說死者是她同學不是賺錢工具、彈吉他跟男友告白過往、陪男友和夥伴去找同學,以及反覆不斷地睡覺、作夢被附身之外,有什麼其他的作為嗎?
如果書儀(夏于喬飾演)的同學許千禾(孫可芳飾演)在十年後,從我們看了都討厭的豔麗少女,搖身一變成了一個我們都覺得很慘的、埋沒在小裁縫工作室又得照顧中風母親,每天壓抑著憤怒與恐懼的黯淡女人,那書儀在這十年間變成了什麼樣的人?
上班族?但她上什麼班、工作性質是?她目前的夢想到底是什麼?她在工作上、生活上是否感受到哪些壓力?這些完全是個謎團。
一個只有過往、沒有現在的角色,很難讓人同情。

《粽邪》的坐立難安
這也是為什麼,我由衷佩服夏于喬,因為演技大爆發的緣故,無論是中邪時的肢體表現與神情,都準確地表現出陰氣森森的樣子,而飾演學生時代時一開始雖然尷尬(畢竟是熟面孔,觀眾能立刻意識到其實際年紀),但藉由原本就討喜的個人特質以及精湛演技,也變得很有說服力。
如果沒有優秀的演技,《粽邪》因為敘事帶來的不耐感,絕對會讓人「坐立難安」。
其實《粽邪》開場是好的,一個在大喜之日上吊的新娘,本身便是一個謎團(為什麼她要上吊?她到底是誰?),沿著那一條繩索出發(畢竟就是「送肉粽」不是嗎),更可以製造出許多懸疑氣氛(後續出現的白衣女鬼是不是那個新娘?為什麼她要挑這些受害者?是他們犯煞嗎?),然而卻因為太執著於訴說一個「霸凌」的「校園故事」,反而削弱了那一條「繩子」所能夠串起的故事內涵與生命的重量。
雖然無法成為恐怖片中的經典,撇開其敘事上的弱點,《粽邪》也有不少迷人可愛之處(尤其是夏于喬),各方面的安排都算是小巧到位,能夠在大螢幕上看見彰化沿海送肉粽的習俗,更是難得的觀影經驗。期待《粽邪》導演團隊可以繼續交出更棒的成績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