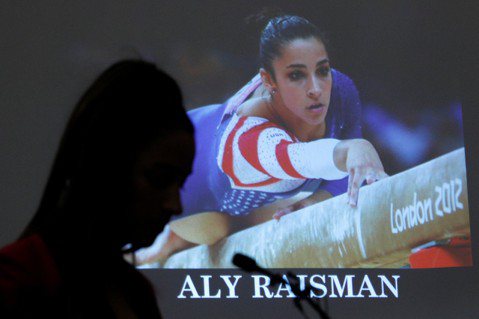我們離印度有多遠?——譴責性侵受害者的文化

自從兩年多前印度女大學生在公車上遭到性侵傷重身亡,台灣媒體就不時出現各種印度慘絕人寰的性侵案件,每次鄉民的回應都很一致,約末就是「印度,不意外」、「這個國家的男人都是禽獸」這樣的說法,好像那個世界離我們很遙遠,這樣的暴行對我們來說很陌生。是嗎?
當然不是。比如說,被稱為「台大宅王」的張彥文在大街上亂刀屠殺想分手的女友,當她身受重傷奄奄一息時,還當街遭受猥褻;或是黃姓現役軍人跑到前女友家殺死她母親,並性侵隨後返家的前女友後將其勒斃;當然也不要忘了,拒絕求愛慘遭姦殺焚屍的嘉南藥理科技大學女學生。
這些案例有一個共通點,就是案件發生時,痛罵殺手泯滅人性的人雖所在多有,也多的是鄉民指責受害者,說她們要不是跟其他男性友人過從甚密、要不就是接受男友金錢與勞務示好,根本就是「玩火自焚」,說她們不「潔身自好」,或太過愚蠢,相信「男女之間有純友誼」。
最大的不同,有人會說,是台灣的案件叫做「恐怖情人」,而不是印度那樣來自陌生人的攻擊,總之冤有頭債有主,雖然殺人不應該,但多半是女生也做了什麼讓男人受不了的事,才會引來殺身之禍。真的是這樣嗎?英國BBC剛推出的紀錄片《印度的女兒》(India’s Daughter),讓我們看見了,台灣社會裡譴責受害者的思維,與印度巴士性侵案揭露出來的性侵文化如出一轍。
印度的女兒
2012年12月16日晚上九點鐘,印度醫科女學生Jyoti Singh與一名男性朋友看完《少年 Pi的奇幻漂流》後準備搭公車回家,一輛公車在站牌停下來,表示有到他們想去的地方。司機賣給他們兩張票,他們坐下來聊天,突然燈暗了、前後車門碰一聲地關起來,一群早已躲在車上的男人走向他們,指責她為何這麼晚了還在外面遊蕩,然後就開始毆打他們,Jyoti被拖到車後座,慘遭六人輪暴,除此之外他們還用生鏽的鐵條刺入她的陰道,穿破子宮,甚至拉出部分的腸子。以為兩人已經死亡,暴徒將他們推出車外,還試圖倒車碾過他們。奄奄一息的兩人向路人求救,但沒有人願意停下來,直到一名腳踏車騎士停下來報警,人們開始聚集在他們身邊,每個人都想知道他們做了什麼事才會遭受這樣的厄運,卻少有人願意提供幫助。13天後,Jyoti傷重死亡。
這當然不是德里第一次發生這樣的案件。事實上德里早就被稱為是「性侵之都」,然而即便女性在街上受到性騷擾可謂家常便飯,也沒有女人覺得太陽西下後獨自外出是一件安全的事,但性侵報案率仍然非常地低。大多數女性覺得被性侵是一件極端羞恥的事情,更遑論整個過程中她們將飽受警察與司法單位的嘲弄與羞辱,提出告訴也會永遠地在她們身上留下印記,為她們結婚成家的機會投下陰影。
然而Jyoti Singh的死卻史無前例地喚起眾人的憤怒,因為她代表的是新的印度,一個正在崛起的經濟強權,一個努力擺脫傳統、邁向現代化的古老國家。她是新時代的女性,夢想著成為世界知名的腦神經醫學專家,拒絕相信女性不如男性。
雖然來自較低的種姓階級、家境亦十分清寒,她靠著意志力與驚人的毅力掙脫種種限制。換言之,她就是「新」印度的女兒,然而,她卻被那些不斷扯著印度後腿的貧窮、文盲、保守勢力與男性暴力殘忍地殺害了。她讓人們看見,新印度刻畫出來的新女性形象根本就是個脆弱的謊言,那些「舊」印度的兒子輕而易舉地戳破了這個泡沫,用鮮血與慘酷的暴力再度重申他們對女人的所有權。

印度的兒子
《印度的女兒》這部紀錄片中最具爭議性的,就是其中一位強暴犯Mukesh在接受訪談時,毫不羞恥地說:「一個巴掌拍不響,一個女孩晚上在街上亂走,被強暴了應該比男孩子負更多的責任。」「男孩與女孩本來就不是平等的,女孩應該待在家裡做家務,而不是晚上跑到舞廳鬼混。」「我們只是想給他們一個教訓。」「一個女人被強暴的時候最好不要抵抗,如果她乖乖地接受,他們 『完事後』 只會把她丟出車外,就只有男孩被打罷了。」「判處死刑,女孩們會面臨更大的危險 …… 以前他們(強暴犯)可能會想,放她們走吧,她們不會告訴任何人的,現在他們一定會在強暴後把女孩殺了。」
觸目驚心嗎?是的,但我覺得最可怕的是嫌犯兩位辯護律師的發言。辯護律師M. L. Sherma說:「一個淑女、女孩、女人,比寶石、鑽石都要珍貴,這都取決於你要把這寶石放在哪裡,如果把鑽石放在街上,就會被狗撿走,你沒有辦法阻止牠」,他指責受害者行為不檢:「那個女孩是跟一個不知名的男孩子出門約會,在我們的社會裡,我們從來不會容許女孩在晚上跟一個不知名的男孩出門」,另一個辯護律師A. P. Singh更說:「如果我的女兒或姊妹在婚前做出讓她們名節受損的事情,我會親自把她們帶到一個農舍,讓我的家人站在一旁觀看,潑她一身汽油,放火燒死她。」
性侵文化
這些話聽起來是不是有點耳熟?還記得張彥文被補之後還哭哭啼啼地說,如果女友能夠同意不分手的話,就不會被殺了;告白被拒絕,掐死學妹姦屍,「如果不拒絕就不會被殺了」,這跟「被強暴時乖乖接受就不會被打」的邏輯如出一轍,這些男人試圖以暴力控制女人的身體,認為不服從本身就構成傷害對方的理由。
當我們為印度駭人聽聞的性侵案件震驚不已,卻無視於台灣性侵案件發生的比例居高不下,在情侶、夫妻之間發生的性侵、暴力與謀殺,慘酷程度也不遑多讓。以台灣的情況來說,加害者多半以情侶、同學、親友等熟人居多,發生的場所也以受害者與加害者的住所為主。然而這樣的趨勢卻讓許多人反過來譴責受害者,認為是受害者「太大意」、「自找的」、「自己也很有問題吧」。
以最近姦屍焚屍案為例,由於受害者視加害人如兄長,與男友吵架後到兇嫌家中訴苦聊天,不幸被性侵殺害,竟有不少鄉民發言說「一個懂得潔身自愛的女性是不會做這種事的」、「在男性朋友家過夜就是不對……如果一個女生會想、會思考,就不會做出這種事」、「跟男友吵架、找別的男人訴苦,這不是婊子是什麼」。
讓我們來回顧一下印度巴士性侵案辯護律師的說詞:「男人跟女人之間的友誼,這在我們的社會中完全不可能存在。這樣的女人馬上讓男人想到性。」一個女人如果「愚蠢」到相信任何男人可以當朋友,遭逢不幸了當然是自己的錯了,因為她不「潔身自愛」,就像把自己丟到狗面前,怎麼能夠期望「狗」不要做出狗的行為呢?
女性主義裡有一個名詞叫做「性侵文化」(rape culture),也就是說當一個社會對性別與性抱持特定態度,導致強暴被合理化、正當化。比如說,人們批評受害者跑到兇嫌家中讓對方「有所期待」,因此被拒絕後惱羞成怒性侵殺害對方也是「可想而知」、可以「理解」的。這樣的說詞一方面將男性性慾毫無限制地合理化,另一方面又壓制女性的身體自主權,因為男人「就是這樣」(跟狗一樣),女人必須永遠活在自我搭設的身體牢籠裡,「潔身自愛」,才不會被「狗」吃了。

台灣的女兒
這些批評中,讓人印象深刻的則是,這些對受害者的檢討,有極大的比例來自年輕女性。這些女性認為自己非常地通達事理、非常地會「保護自己」,她們說「防人之心不可無」,尤其因為性侵案件多半發生在熟人之間,更要注意不要置自己於險境,要謹守「男女之間的界線」。
她們不瞭解的是,這整個性侵文化是一體的,因為這個社會羞辱被害人,正當化加害者的情慾,將女人的身體客體化,將之視為可以擁有的財產(因此分手才會造成如此強烈的損失感,不惜通過暴力強行討回),這樣的案件才會一再發生。
我們從「熟人強暴」中應該試圖去瞭解的是,為什麼很多台灣男性,在單獨與女性相處的時候,就會不由自主地情慾化對方。就如同那個印度律師說的,這些男性輕賤那些跨越性別藩籬、希望與男性建立友誼關係的女性,認為這樣的想法等同於「主動邀請」性侵行為。
換言之,這恰恰正是因為在性意識開始發展的時候,我們的文化對情慾的羞恥感,以及隨之的矢口不提,導致青年男女沒有辦法在一個正常而開放的環境中認識自己的身體、探索自己的慾望與情感。而謹守「男女之間的界線」,進而放任男性從A片裡認識虛假的女性情慾、客體化女性身體,並無限制地合理化這些扭曲的慾望(「男人就是男人」),同時又創造出壓制情慾、關閉自己身體、「潔身自愛」的「好女孩」與「愚蠢」、「不懂得自我保護」、「破麻」的「壞女孩」之二元對立,正是這些環節導致性侵文化的結構不斷輪迴重生、無法打破。
我們真的比印度好嗎?
當我們觀看印度的性侵新聞,深信台灣的情況比那邊好上許多,在某個程度上或許是如此,畢竟如果一對台灣男女晚上八點多被襲擊,大概沒有人會攻擊他們一同外出的行為本身敗德。
但我們也別忘了,所謂「恐怖情人」與這些「印度之子」的攻擊動機是類似的。出自同一種保守的傳統父權勢力,他們看見一個情感與身體自主的女性,意識到除了用暴力之外,他們沒有辦法控制對方,出自於這種挫折與無力感,他們用強暴來羞辱這些女性。同樣的,他們要傳達的訊息也是類似的:妳不可以比我自由,我不允許妳有自主的慾望、身體的自由。
我們也不要忘記了印度人回應該慘劇的方式是一波波地走上街頭,要求政府正視性暴力問題、鼓勵女性出面指控性侵、反對污名化受害者、呼籲加強性別平等教育;巴士性侵案發生後,性侵通報率已經大幅提升35%。
那我們又在做什麼呢?一次又一次,我們指責受害者,我們為加害者辯解,我們逃避社會為這些案件層出不窮該負起的責任,我們說這都是笨女孩與怪物的錯,所以我們相信我們是安全的,只要我們緊緊地綑綁起自己,在暗巷不斷倉皇回顧,永遠不得安寧。
我們真的比印度好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