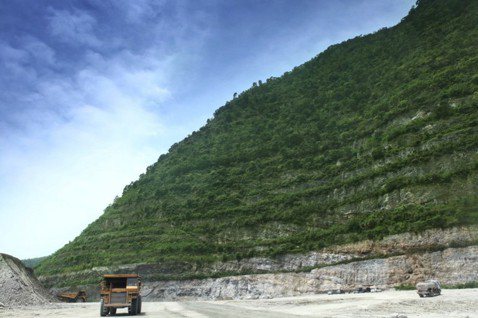管理不當動物放生行為還需要多少的法律設計與教育宣導?

4月27日早上十點在立法院紅樓101會議室,由民進黨立委林岱樺辦公室所召開的「野生動物保育法部分條文修正案釋放動物管理規範之公聽會」中,各界關心這個議題的環保團體、動保團體、保育團體、宗教團體、學者專家、主管單位、媒體與相關政黨代表齊聚一堂,試圖為這個棘手卻又迫切的議題找出共識與對策。
然而在整個會議的進行中,本人觀察到幾個問題,而這些問題似乎會成為橫亙在民間團體與主管單位之間的障礙,現行的相關法律設計與執行面也的確無法面面俱道地觸及合理的需求並管理衍生的問題。本人根據今日參與會議,以及離場後持續觀看立法院議場內直播影像的觀察,以下提出幾個在法律設計、教育宣導與單位間配合的議題,期望立法院經濟委員會、相關團體,與主管單位能夠加以留意,讓整件事情往正面積極的方向發展。
首先,如同我在先前的評論中已經提到,此次《野生動物保育法》修法的主要目的是在「降低相關主管機關權責之間的疊床架屋」以及「依據動物的保育等級區分罰則,以期降低動物被不當放生而死亡的風險」。而適用《野生動物保育法》而且還是宗教團體經常進行大量商業性放生的動物事實上並沒有那麼多。也就是說,宗教團體應該關切的不是《野保法》,而是涉及大量經濟動物釋放的《漁業法》、《動物保護法》、《畜牧法》與《水庫蓄水範圍使用管理辦法》甚至是《河川管理辦法》之間的配合。還有,是否能夠在經過溝通、學習與規劃的前提下合法、合理、合情地進行。
也就是說,任何把所有管制不當放生行為的問題推到《野生動物保育法》與其主管機關是不對的。雖然法律的設計未臻完美,但是在透過網路直播的會場中我們仍然可以聽到許多根植於誤解的發言與建議(或抗辯),而這些誤解多半基於偽科學,張冠李戴,一知半解的零碎知識,以及宗教自由與現代法治社會關係的錯誤想像。
因此要如何為這些沒有接受過《環境教育法》與「生態保育知識」洗禮的世代與團體進行教育與溝通,使他們能夠認同法律設計的目的是在協助正確的護生,而非錯誤的放死,則是相當艱難的挑戰。
為什麼宗教團體會對法律的設計產生誤解或困惑?在前文中我已經提到,不一樣的動物、不同的場合、不同的狀況,就會涉及完全不一樣的法規與罰則。因為對宗教團體來說是「一次法會」,但是對主管單位與其他團體來說,卻是「多重議題」。
我來舉幾個實務上會發生的例子讓大家了解:
◎狀況一
問:A寺廟打算在台中梧棲漁港放生200隻食蛇龜,結果導致陸生的烏龜通通在海裡淹死,這違反甚麼法?
答:《台中市放生保育自治條例》還有《野生動物保育法》。又因為食蛇龜為保育類動物,造成保育類動物大量死亡最高可判處250萬元的罰鍰。
◎狀況二
問:B寺廟打算在墾丁國家公園的龍鑾潭施放500斤的鯉魚,這樣違反甚麼法?
答:《國家公園法》。但因為鯉魚不被認為是野生動物,所以不違反《野保法》。鯉魚雖是人工飼養的經濟動物,卻又不受漁業署的《水產動物增殖放流限制及應遵行事項》所規範,除非在運輸與施放過程中造成大量死亡,就可能再違反《動物保護法》。
◎狀況三
問:C寺廟不忍屠宰場中的動物被殺害,所以花錢購買動物放置於私人經營的護生園區中,有沒有違法?
答:目前來說沒有。但如果經營管理不善,以至於動物產生疫病,產生噪音,與大量的排泄物。那麼或許《畜牧法》與《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就需要介入。
◎狀況四
問:D寺廟想在翡翠水庫放流香魚,有沒有違法?
答:有。雖然新北市並沒有自訂的放生管理條例,但是依據《水庫蓄水範圍使用管理辦法》,翡翠水庫早就公告不接受任何放生的申請,也就是任何在翡翠水庫自行施放魚苗的行為都是違法的。因為那是大台北地區的飲用水,身為水利管理單位,當然有權責來維護多數人的用水安全與品質。
◎狀況五
問:一個白目到水族館買了20隻來自南美洲的綠鬣蜥,放到嘉義的山區,結果那些外來物種就落地生根。這違反甚麼法?
答:《野生動物保育法》。雖然我國目前沒有管理外來入侵種的任何專法,但在非國家公園與非內政部所轄的溼地範圍中,野保法大概是一個最能管理這類行為的法律。
所以宗教放生真的是萬惡不赦的嗎?事實上並非如此。其實在媒體的關注與相關主管單位的積極努力之下,已經有為數不少的宗教團體開始與保育及動保團體合作,進行流浪動物的收容,還有野生動物的救傷。即始是涉及商業放生的動物種類也開始下降。然而社會大眾對這樣的走向就會完全滿意嗎?除了高喊宗教自由是人權以外,宗教團體抗拒管理的原因又是什麼?
一、知識的落差太大
在公聽會中,所有的與會代表聽到某些宗教團體宣稱「台灣之所以最近沒有嚴重的風災是因為他們大量放生使颱風改道」、「放生就是要讓熱帶性低氣壓還小的時候就培養它,和它搏感情」。如果沒有這樣現場直播的公聽會,社會大眾恐怕難以想像在2016年的今天,還能出現這般的言論,甚至以此荒唐的言論砰擊相關主管單位。
如果在封閉的水體(例如與外界河道不相通的人工池塘)中放養食藻性的魚類來控制水質其實是可行的,因為這不會有入侵種與散逸的問題。然而有宗教團體在未經翡翠水庫管理局的同意之下就密集施放大量魚類到翡翠水庫中,並聲稱水質之所以清澈是他們放生的功勞,這就顯得荒唐。這也就是說拿著一知半解的知識來誆稱己身行為對環境的貢獻,其實是一種狂妄。而且也違反了佛教與道教所尊崇的敬天惜物的精神。
但是如果相關單位打算辦研習會推廣友善環境與動物的護生行為,應該找誰當講師?是生態學者?還是宗教學者?對話的知識起點在那裏?是小學程度?還是國中?要幾堂課才能完成甚至驗收呢?
二、辭彙使用的落差與濫用
延續自上一個話題,相關單位努力推行了很久的政策與法令為何沒有深入到這些個人或團體?除了資訊傳遞的圈子完全不同之外,辭彙的使用恐怕就有很大的認知落差。
生態學者所認知的「理想生態環境」是儘可能排除人為干擾,讓大自然的水文、地質、森林演替、食物鏈等機制自然運作。然而部份宗教團體在缺乏這方面的知識時,他們概念中的「生態環境」變成是「人力應介入,只要有動物活著就是好環境」的想像。所以當一個宗教團體成立一個「XX生態協會」來彰顯自己關心生態環境時,你認為「他說的生態」和「你認知的生態」是同一碼子事嗎?
三、邏輯的錯落
有些發言者認為,「要不是他們在放生,河流,海洋中怎麼可能還有魚?魚都被人類吃光了」。然而增殖放流的前提事實上是「在棲地環境品質還有改善可能時,動物的族群規模過小而無法延續時」,有計畫的放流特定的魚苗才可能有助於漁業資源的恢復與生態系統的改善。但是就現行的大規模放生行為來看,許多放生活動的所在地並不適合動物的存活(例如將泥鰍放進深潭中),因此忽然放入大量的動物個體並沒有救到任何一隻動物,反而是放死,甚至排擠了原生物種的生存空間。
四、資訊傳遞的障礙
許多宗教團體認為,農委會根本沒有拿出任何「放生影響生態環境」的數據,所以他們不服這樣的法律約束。事實上從1985年左右,生態保育界就已經開始展開與宗教界的對話,相關的國內外科學研究不勝枚舉。雖然科學與宗教並非是完全對立與互斥的,然而就資訊傳播的體系與網絡來說,科學與宗教圈完全是兩個平行世界。就好比你不太可能沒事到基督教與天主教的論壇去大談演化論,或是執意在佛教與道教的社群中質問燒紙錢會不會影響陰間的金融秩序。
換句話說,宗教界可能根本不知道該使用什麼樣的關鍵字來搜尋這些資訊,而主管機關與學術界,可能也無法瞭解除了直接加入一個佛堂成為信眾以外,還有什麼其它的可能以「人家聽得懂的辭彙」進行溝通。正因為這樣的障礙,使得政府相關單位與保育團體總是無法理解:「做了這麼久的宣導卻沒有用處」,而宗教團體或許也覺得委曲,認為「政府的法令那麼多,又缺乏單一窗口的說明,誰會知道什麼動物能放不能放?」
五、法令的設計與執行仍有許多改善空間
以《野生動物保育法》來說,唯一有可能讓宗教團體參與放生的途徑有兩個。第一是野生動物的救傷,但這不能由未經訓練的團體與個人私自操作。因為野生動物相關知識遠比經濟動物來得複雜與精細,因此宗教團體可以做的是提供資金與土地的支援,還有釋放時以動物福利為最高考量的祈福儀式。
第二,則是被誘捕之農損鳥的釋放。在我的前一篇文章中已經提到,如果農漁民不忍野生鳥類掛網慘死,或遭毒殺,卻又不甘心努力化為烏有,除了改善養殖種植設施之外,大概就是會請獵人幫忙誘捕移除。但若宗教團體有意進入這個部份協助農損鳥類的「移開」,那麼《野保法》的設計就需要使之變得可行,卻需要排除金錢交易引發獵人刻意捕鳥的惡習,整個走向回頭路。這與積極護生的理念反而是背道而馳的。
就《漁業法》來說,雖然《水產動物增殖放流限制及應遵行事項》已經提供放生團體非常非常多的選擇,但因這個辦法只規範了海洋性物種,而沒有規範同為經濟動物放生大宗的淡水魚、蝦、蟹、斑龜與中華鱉。而這些動物都屬於漁業法中所認定的「水產養殖種苗名錄」中的成員。因此缺了對可施放淡水物種及其地點的規範,只仰賴水利署的《水庫蓄水範圍使用管理辦法》就會顯得相當不足。因為水利署的辦法中只規定「放生需要得到主管單位許可」,但沒有「可放流物種的清單與地點建議」。水庫的下方就是河川,然《河川管理辦法》卻未對放生行為進行任何規範與建議。
便有一位發言的法師建議「找兩條河流做比較,看看是有放生的河流比較好,還是沒有放生的河流比較好」。事實上台灣的所有溪流河川已經被各式各樣的放生與棄養活動搞到通通都有外來物種的境界,所以根本就沒有比較的可能,除非宗教團體能幫忙移除這些外來種,帶回自己的護生園區去好好養起來。
也就是說,淡水性經濟物種的放流需要漁業署與經濟部水利署的合作,才可能得到可行的管理方向。理想上來說,只有食藻性的部份養殖魚種可以被施放到封閉性的水體中,其它一律都不應該施放以免放死,甚至造成水質的優養化。
就《畜牧法》與《動保法》主管單位來說,最需要其專業協助之處在於護生園區(包含私人流浪動物收容所)的設置規範,如何能夠合乎環保、衛生、低噪音、合乎動物福利,並避免疫病產生的狀況。而這也是許多頗具規模的宗教放生團體近年著力最多的護生場域。然而動保法主管機關的行政能量幾乎已經被流浪動物議題所壓垮,因此還有多少力氣與專業能夠稍微投入這個議題,使護生園區的成立不會成為另一種災難,疫病叢生的場所,則是相當大的考驗。
如果這些相關法規與主管單位能夠一同合作,讓良善、合理的放生行為得以實施,一方面可以解決宗教團體的信仰出口,二方面也可能把本意良善的正念,在現代科學知識與環境教育的引導下步向正途。
但是當一切看來都還有希望的時候,我們不要忘了還是有可能半路殺出程咬金,讓漸漸聚焦的討論與默契再度被打破。如果有宗教團體要求政府拿納稅人的錢或釋出國有土地來養「他們想救的動物」,那麼社會大眾會同意嗎?此外,當嘴中所說的「隨喜放生」在實務上的操作變成「個人贖罪與功德換購」,而違反佛道思想的教誨時,宗教團體內部的自律機制又是什麼?這是生態保育團體,與政府主管單位在盡可能肯定宗教團體的善意時,而宗教團體也希望「擺脫污名」時,應該向全體國人交待的議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