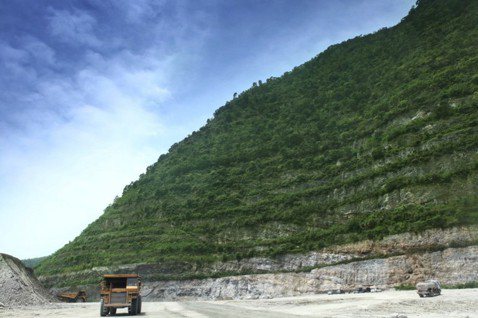在現行《野保法》框架下,管理野生動物釋放如何修法?

本人已經在先前的諸多評論中介紹與說明過「動物放生行為」的樣貌、涉及動物種類、場域、可能造成之正負衝擊、法律、與行政管理的複雜性。然而我並沒有提到在現況下(缺乏單一的外來生物防治法規與專責機構、事務與區域管理單位高度複雜、基層公務人員業務超載、生態保育預算年年縮減)的狀況下,《野生動物保育法》可以怎麼修才有可能把目前「不當動物釋放」的大洞給補一點點起來。
在談法律修訂的建議之前,我想我們應該要先談「理想上的動物釋放面貌」應該是什麼?如果我們希望動物的釋放符合生態保育、保障動物福利、防止外來物種入侵,與避免危害產業與人體安全,那麼理想上應該要符合以下條件:
- 被釋放物種不能是外來物種,更不能是入侵種;
- 釋放該物種不能影響當地的原生生態,包含植被、土壤、水質、同種或近似種遺傳結構、還有食物鏈;
- 釋放該物種的過程並未違反任何動物福利的基本要求,例如「免受飢餓、營養不良的自由」、「免於因環境而承受痛苦的自由」、「免受痛苦及傷病的自由」、「表達天性的自由」、「免受恐懼和壓力的自由」,甚至在某些狀況下還要考量「減量」、「取代」與「精緻化」;
- 釋放該物種後不能影響任何現行產業與設施。
然而我們現在談的是《野生動物保育法》,因此就需要根據此法的立法宗旨與職掌將上述條件修改如下:
- 被釋放物種不能是外來物種,更不能是入侵種之外,還要吻合「野生動物」之定義。因此經濟動物(包含陸生與水產)都不屬於此法管理範圍;
- 為了要與《動物保護法》的責任分工有所區隔,釋放野生動物應該要獲得主管單位的同意,以確保動物釋放作業的專業性,但是不需要特別把「動物福利」之類的字眼納入法規中;
- 至於釋放野生動物不能影響生態環境、產業與設施,則是一個常識,而且也不應該被違反。
當我們確立以上的修定條件以後,我們再來看看目前公認的,因為不當放生產生的入侵物種有哪些,是否適用《野生動物保育法》管理?

▎六大入侵物種是否適用野保法?
一、入侵性淡水魚:
在台灣的入侵物種之中,淡水魚類占了最大宗。在這些入侵性淡水魚類中,又以觀賞魚、食用經濟性魚類,再加上釣客刻意放流的本土與外來物種為多。
觀賞魚與實用經濟性魚類的主管單位顯然是農委會漁業署,而在農委會的內部分工協調中,在野生動物保育法架構下被定義為「一般類」的水產動物則被認為是漁業署的職掌,並劃歸《漁業法》管理。所以這部份就不是野生動物保育法處理的。但是當「保育類」魚類仍受到野保法的管理時,是否會有保育類魚類被不當放流呢?答案是有的。已經有研究者發現,原本只產於中部溪流的稀有保育類淡水魚,被刻意流放到南部溪流中。像這類的行為就仍然受野保法管制。
二、入侵性海水魚:
在台澎金馬地區是存在著一些外來入侵性的海水魚。例如有民眾刻意在小琉球放流澳洲的公子小丑魚,還有早年漁業單位引入美洲的紅鼓魚也已經在馬祖等地成為外來入侵種。而這個部分則應該是漁業法的管理範圍。
三、入侵性兩生類與爬蟲類:
兩生類與爬蟲類聽起來完全是野保法的管理範圍,然而因為漁業署主管的經濟水產動物中卻又有「斑龜」、「中華鱉」以及「虎皮蛙」等物種。因此有時候在部分物種的管理上就會有些重疊與模糊地帶。除了這些食用經濟物種外,目前所有的入侵性兩生類與爬蟲類,例如巴西龜、綠鬣蜥、綠水龍、沙氏變色蜥、花狹口蛙、斑腿樹蛙都被認為是野保法應該管理的。
四、入侵性鳥類:
由於過去輸入一般類禽鳥不需要經過審查,又加上禽流感所造成的恐慌,還有許多粗心飼主的放飛,因此台灣的入侵性鳥類物種數目幾乎是全球之冠。不當放生行為所涉及的鳥類則同時會有外來鳥類,與本土鳥類,而且種類繁多。
五、入侵性哺乳類:
目前在台灣還沒有太嚴重的入侵性哺乳類野生動物問題,但可能很快浮出檯面的會是浣熊這種破壞力強大的動物。
六、入侵性無脊椎動物:
最為人熟知的應該是福壽螺與非洲大蝸牛,還有為數不少的昆蟲,再加上蚯蚓。只要會破壞農作物的植食性無脊椎動物大體上都還能被《植物防疫檢疫法》所管理,但是類似外來蚯蚓,或是非植食性昆蟲(例如取食腐植土的鍬形蟲)這類的動物,在法令的適用上就有一些曖昧。

▎那違法行為呢?
由以上討論可得知,野保法應該可以管理保育類野生動物、野生鳥類、兩生類、爬蟲類、與哺乳類的釋放。但是目前的野保法能不能管住下列常見的違法行為?
第一,將馴化品系動物(domesticated animal)釋放到野外,並造成環境或人員的損害。例如黃金蟒是網紋蟒或緬甸蟒的馴化品系,早就不算是野生動物,而是人工繁殖寵物。如果非常大型的個體被刻意釋放到野外造成其他野生動物,甚至是嬰幼兒傷亡,應該要使用哪一個規範來處理?在世界主要先進各國的法規體系中,「危險動物」(包含寵物)的輸入、持有等規範都屬於「動物保護」法規的範疇。因此如果野保法無法規範非野生動物的釋放,我們的動保法有能力介入嗎?
第二,同時購買野生動物與非野生動物後釋放到野外。有些民眾會直接到寵物量販店或鳥店買了就放,然而其中可能同時混有漁業法主管的觀賞魚、野保法主管的野生外來爬蟲類、與動保法主管的寵物兔或寵物鼠。這個時候是不是只能以野保法處理爬蟲類的釋放,以動保法處理棄養,而漁業法則無法可法?三部法規與三個單位能夠同時介入嗎?
再來是若有民眾看見路邊小販兜售「民眾認知的野生動物」,民眾並不選擇直接通知地方政府農業、動保、或保育單位告發處理,反而花錢購買後釋放。這樣的行為反而助長獵捕與販賣行為,但若只罰購買者,而無法處罰非法獵捕與販售者是否造成「自認善心民眾」的被剝奪感?此類行為所造成的危害卻又因動物種類不同而有所差異。
舉例來說,若在路邊被兜售的是紅鳩或珠頸斑鳩之類的台灣原生野鳥,那麼購買後釋放至多會危害「動物福利」(若未經救傷因此死亡)。但若購買的是菲律賓椋鳥或泰國八哥這類的入侵性鳥類,或者是可能與原生物種雜交的中國畫眉與外來環頸雉,那危害的就是「生態環境」。然而一個小販同時兜售之動物的源頭差異極大,可能是野外捕獵,也可能是繁殖場批發,也可能來自同行調貨時,應該要如何以《野生動物保育法》來管制源頭?
第四,將在島內具有跼限地理分布範圍的野生動物釋放到原本並未分布的地區。例如常見的螢火蟲野放、蝴蝶野放、稀有保育類魚類野放,經常都未經過主管單位同意。而這樣的行為則會摧毀長期以來的天然生物分布格局,也屬於破壞自然生態的行為。
最後,則是刻意將外來野生動物釋放至合適生存地點造成入侵種問題。這樣的問題在台灣相當普遍,例如出現在高雄的大守宮、高冠變色龍、新北市的綠水龍、中南部的綠鬣蜥都是屬於這樣的案例。



當我們瞭解最常見的違法行為以後,再來看行政院版的修法建議,該建議對上述情事能有效管理嗎?
政院版對這個議題的修法重點在《野保法》第三十二條與其位於第四十六條的罰則,其原條文為:
野生動物經飼養者,非經主管機關之同意,不得釋放。前項野生動物之物種,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違反第三十二條第一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二十五萬元以下罰鍰;其致有破壞生態系之虞者,處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二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而建議修改後之條文為:
釋放經飼養之野生動物者,應經主管機關同意,始得為之。但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前項野生動物釋放之程序、種類、數量、區域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違反第三十二條第一項規定或依第三十二條第二項所定辦法有關野生動物釋放之程序、種類、數量、區域或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規定,釋放一般類野生動物者,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下罰鍰;其釋放保育類野生動物者,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二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違反第三十二條規定致釋放之野生動物大量死亡或有破壞生態系之虞者,處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二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這個修法建議也已經考量了「民眾捕捉侵入住家之野生動物(例如野鼠、蛇類等)而移置他處自然棲息環境之行為」,因此不適用此規定。
至於販賣動物供人放生者,政院版明確說明「應依第三十六條第二項規定(註:也就是「營利性野生動物飼養繁殖管理辦法」),先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許可,依法領得營業執照,方得為之,並應遵行同條第二項所定辦法。」
那我們就看看這個版本是否能管住上述行為:
- 釋放馴化品系的危險動物?事實上只要進入人工圈養的動物,無論是馴化品系或野生動物,都只有「動物福利」問題,理應受到《動物保護法》之管理,並應該依動保法進行飼主登記。然而目前動保單位只有能力進行貓狗登記,對非貓狗的寵物登記並沒有統一一致的作法(例如晶片管理)。而野保法目前僅對「需有個體管理」的野生動物進行晶片管理(例如保育類動物、需要進行配合華盛頓公約繁殖查場認證的動物)。所以如果以政院版來管理「經飼養的黃金蟒」,就會逾越野保法的範圍,但若不以野保法管理,那麼動保法中的寵物登記制就應該要跨出只處理貓狗的現況。
- 同時購買野生動物與非野生動物後釋放到野外?政院版很可能管不住這個行為,因為購買後釋放並不涉及「飼養」,因此既無法以野保法開罰,而釋放者也更不可能成為動保法中的「飼主」而造成「法律上的棄養」。
- 民眾不通知地方政府處理未經核可的野生動物販賣,反而花錢購買後釋放?就算不修法,這個行為也是可以被管理的。問題是中央政府從未公布過「應該被政府同意才能釋放的野生動物種類」清單。
- 在島內亂放原生物種?這個問題與前項類似,而造成這種問題的單位有時候甚至是某些生物的愛好者團體,或甚至是地方政府。
- 刻意釋放外來野生動物造成入侵種問題?政院版修法的原意是打算處理這樣的議題,但問題卡在「如何舉證」?

▎修法建議
本人在此建議政院版不需要執著於「經飼養」這三個字,因為加入「經飼養」有可能產生「飼主責任」的概念而與《動保法》的任務重疊。事實上不管有沒有被「飼養」,任何野生動物的釋放都應該要經過專業評估得以為之。
政院版最應該儘快提出的反而是「動物釋放之程序、種類、數量、區域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而這個辦法所著重的並非是「一長串的動物之清單」,而是明確將所有不應該在未經同意下釋放的野生動物類別,例如「保育類物種」、「紅皮書物種」、「優先防治來入侵種」,「部份具危險性圈養野生動物」整合起來,並說明每大類常見物種之鑑識要領、不當釋放之危害、應諮詢與通報的政府與民間機構。無論修法完成之前後,都應該要對民眾、NGO與地方政府加強常見外來入侵野生動物與通報流程之教育宣導。
除此之外,若「被販售之動物」為外來入侵種或人為雜交種而不應該再被釋放到自然環境時,那些動物應該要進入收容體系?那些動物可作為研究教育之用?那些動物應該要進行人道處理?而人道處理的準則可參照已根據《動物保護法》制定之辦法?或需要在《野生動物保育法》中制定,則攸關管理不當野生動物釋放是否能夠完整的關鍵。
至於第四十六條的罰則,坦白說,對於任何破壞生態環境且令其無法恢復的行為來說,還沒有要求當事者恢復原貌實在是太便宜了。假設我們知道當年是誰把綠鬣蜥放出去,造成近年南部的農業損失,耗費公帑辦理好幾個移除計畫還難以讓綠鬣蜥的數量下降,那麼只向他求償二百五十萬元簡直就是太便宜了。
林岱樺委員認為「主管單位不能不教而殺」,所以「初犯不罰,只要去上講習就好」,我認為這是非常不妥的。教育的確要全面性地往上開枝散葉,也要往下扎根。然而不當的動物放生所造成的環境破壞、動物痛苦與公共資源浪費則是長期的。因此我不建議在《野生動物保育法》中納入教育講習,因為我們已經有了來自教育體系的環境教育與生命教育,不需要再疊床架屋,為少數人造成的社會損失來浪費公帑。
整體來說,野保法無法要求「一般類野生動物」飼主進行登記,動保法連貓狗都做不來,是「難以舉證棄養與不當釋放」的現實因素。野保法的罰則未能要求當事人恢復環境原貌與動物健康,也會使得這類案件動輒被輕判以後,納稅人與主管機關仍要負擔這類不當行為所造成的後果。若能將野生動物釋放應遵循辦法,以及人道處理原則同時建立,那麼三十二條與四十六條的修法才不會白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