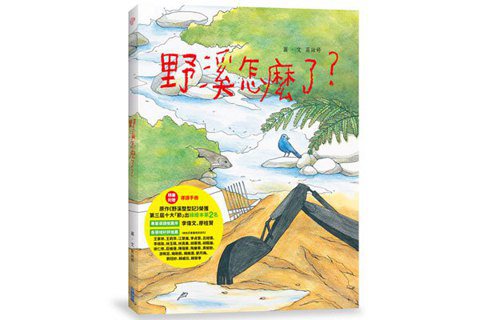國情不同?——永續城市,別說台灣不可能

先將時間回到2009年7月,《好城市》初出版之際。當時,即便許多朋友基於友情大力支持,卻對這本書的銷售不樂觀,不忘間接或直接告訴我:「你這本書陳義過高,可能很難賣」;也有人大致瀏覽之後就單刀直入說:「你講的這些在台灣不可能!」或許,這些朋友是幫我做「心理建設」,擔心出第一本書的我因期待而受到傷害,我謝謝他們的好意。
但是事實證明,《好城市》的表現未如那些朋友的悲觀預期,在書市慘淡的年代竟然還算「小暢銷」,顯然讀者願意閱讀、甚至接受書中所倡議的種種永續城市理念,以至於2017年的今天,《好城市》得以再版,經過一些改寫與資料更新,以新面貌再度呈現。
回首這些年,台灣的正面改變
這幾年來,我有許多機會受邀到各地演講,同時也在臉書上針對環境與社會議題做簡短評論,持續以不同的形式來推廣永續城市的理念與做法。這幾年來,即便認同相關理念的人越來越多,卻不乏向我潑冷水的人,不外乎認為:「你太過理想,這是不可能的」、「理想跟現實有差距」。但是,回首這些年來,在現實上台灣其實發生了不少正面的改變,有些改變快速到連我都感到驚奇。
例如,八年前當我在〈幾乎人人都有自行車的城市〉一文中介紹丹麥哥本哈根的公共自行車系統時,壓根兒沒想到,今天,台北市不但已經有了自己的公共自行車系統YouBike,而且非常成功,不但成為市區內重要的交通工具之一,甚至還擴張到了新北市、桃園市、新竹市、台中市、與彰化縣。不僅如此,台北市還建置了通勤用的自行車道系統,即便系統仍遠不若自行車天堂的荷蘭、丹麥、德國城市的完善,但已經讓香港羨慕不已。
又例如,當我在〈買在地、吃在地〉 一文中寫西雅圖的農夫市集時,豈會料到,在有心人士的努力推動之下,今天,農夫市集在台灣已經相當普遍,成為城市生活的一部分;在該文中,我提到本土產品對永續的重要性,時至今日,不管是為了什麼理由都好,台灣人越來越支持「台灣製」的產品,在亞洲其他城市包括我居住過的香港和新加坡,也可以看到一股復興「本地產製」 的潮流。

這些正面改變也發生在專業界
改變,也發生在專業界。例如,我在〈街道和雨水的故事:想像一個海綿城市〉(本版更名為〈從想像到實踐:打造一個海綿城市〉),提出「海綿城市」的概念,主張城市應該要模仿森林水文,能夠如海綿般地吸收雨水。萬萬沒有料到,今天,「海綿城市」已經成為中國大力推動的雨洪管理政策,其中央政府投入驚人的預算,在數十個城市試點打造相關設施;類似的,台灣政府也積極推動「低衝擊開發」(Low-Impact Development)相關設施。「海綿城市」、「低衝擊開發」等利用自然機制來處理雨水逕流的相關設施,雖然在台灣與中國的城市中仍未普及,但其觀念已經在實務界中被廣泛接受,嚴格上來說已不算是需要大力推銷的新觀念 。
又例如,我在〈還地於河,荷蘭與河流握手言和〉一文中所介紹的「還地於河」概念,今天,已是台灣水患治理領域中經常被提及的名詞。「還地於河」是我對荷蘭Room for the River(荷文 Ruimte voor de Rivier)政策的翻譯,2006年,我第一次將這個令我驚艷的政策介紹給台灣環保界的朋友;後來,從網路上發現有水利工程師乃至一般民眾認為「還地於河」這件事情簡直是駭人聽聞、不可思議。但也不過短短幾年間,「還地於河」就成為專業界越來越能夠接受的水患治理新思維。值得一提的是,「還地於河」開始有了異於荷蘭Room for the River政策的不同詮釋,例如,有人以「還地於河」來形容埋於地下管道的河川開蓋。我認為這是很好的發展,因為中文的「還地於河」強調「還」的動作,不必然要局限於荷蘭Room for the River政策的實際做法,台灣可以、也應該要發展出屬於我們自己的「還地於河」政策。
當然,以上所提種種現實上的改變,其相關細節還需要深入探討,以了解這些改變是否真的幫助我們往永續的道路邁進。此外,為了避免誤會,也要先澄清:舉出以上現實中的改變,絕非認定這些乃《好城市》所促成;以上種種改變是許多人共同倡議推動的結果。提出這些現實中的改變,是要強調:理想與現實沒有那麼遙遠,改變絕對是可能的!
頑強不改的主流價值觀——拚經濟
現實,當然遠非一片美好。今天,台灣在很多方面仍然落伍。例如,台灣的城市中仍然充滿汽機車,即便在有較完善捷運系統的台北市,道路仍是以汽車為大,行人次等,即便這幾年有些路段的人行道拓寬、擴大了步行空間,行人還是得吸大量汽機車排放的PM2.5。
又例如,台灣各地的河川仍然處於水深火熱之中,這幾年,當都市裡的河溪都被硬體工程「整治」殆盡之後,換成大量的山中野溪遭殃;既然醜陋的水泥工程已難以讓一般民眾接受,就漂綠,改以所謂的「生態工程」繼續破壞河溪生態。
最頑強不改的,是台灣的主流價值觀——拚經濟,而且我們仍然用最落伍的方式——犧牲環境和人道來拚經濟。城市發展,仍然過度重視硬體建設和土地開發。為建設而建設,造就了全台各地大量的蚊子館;為開發而開發、視土地和家為「房地產」、將農地變建地,造就了全台各地大量的空屋、假農舍和閒置建築用地,當然還有大量因為區段徵收而被迫離開家園的傷心人。不必要的開發破壞環境、浪費地球資源、傷害人權之外,令人最心痛的是,隨著永續城市規劃設計的相關概念愈來愈受到重視,近來許多極具爭議的開發計畫也被漂綠。
台北市政府這兩年來大力推動的社子島開發案正是一例,以「生態社子島」為名,堆砌大量永續規劃設計相關詞彙,包括「成長管理」、「緊密城市」、「綠色運具」、「生物廊道」、「物種DNA生態基地」、 「低衝擊開發」,甚至還有「還地於河」等等。許多概念誤植不說,開發一個環境敏感地帶、築以10公尺高堤、且很可能讓現有居民因負擔不起高漲的房價或租金而離開,這樣的計畫何「生態」之有?

看到西方先進案例,先不要說台灣不可能
即便現下的台灣仍有太多需要進步的地方,也絕不代表未來一片黯淡。台灣的現況提醒我們,我們還有更多工作要做。八年前,我以〈挑戰觀念,相信改變〉作序,今天,我仍堅定相信未來會有更多的正面改變會出現,而本書介紹的許多的新觀念以及國外案例,仍然應做為台灣努力的目標和參考。
然而,許多台灣人往往一看到來自所謂西方先進國家的案例,就馬上認定「台灣不可能」。這往往讓我感到無奈,因為如此的武斷不但無益、還有害。為何說是武斷?因為任何一件事絕不能只憑直覺或片面觀察就草率歸納、妄下結論。一個在其他國家成功推行的政策或運動,在台灣有沒有可能推動?要回答這個問題,得先分析促成該政策或運動的驅動力以及各項主客觀條件在台灣是否具備。如果沒有做任何一丁點的分析就斷言「台灣不可能」,無異於膝反射,不但沒有建設性,而且正是阻礙改變的原因之一。
太多根本不了解國外情況的台灣人,卻總是一口咬定好政策不可能在台灣推動,這種非理性的態度,是台灣人自己最需要先改變的地方。因為,若多數人一開始就否定了改變的可能性,當然難以造就改變。
改變,也需要耐心,不能輕言放棄。一直看不到的改變,也許下一秒鐘就會發生。歷史事件一再證明,人類社會絕大部分的改變不是線性進行,並非循序漸進,引爆改變的元素可能潛伏在社會中,不動聲色地累積能量,直到出現一個「催化劑」,當事情被催化到臨界點,就產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換句話說,即便今天未見任何動靜,不代表明天不會有劇烈的改變發生。
未來的可能性也難以就當下的主流價值觀,以及社會、經濟、環境等狀態來預測,畢竟今天的現實不等於明天的脈絡。以今天的現實來預測明天,等於是忽略了大環境本身會改變的可能性,是短視而非遠見。我之所以不怕倡議當下看似「陳義過高」、「太過理想」、「台灣不可能發生」的觀念和做法,是因為相信那是人類社會應該要走的路。很多人可能不知道,150年前,「公園」——讓公眾(而不只是權貴階級的皇室)可以享受的園林綠地——是一個被視為激進的概念;但現在,哪個現代城市沒有公園? 如果,我們不勇敢做夢,未來哪能發生改變?

城市不永續的結構性問題,該如何挑戰?
過去四年多,我在新加坡國立大學建築系以及香港中文大學城市研究課程都教授「永續城市」的必修課,談現代城市如何不永續、為何不永續、又如何邁向永續。永續課題作為大學的必修課,本身就是一個正向的重要改變,因為20多年前我在台灣讀大學時,並沒有這樣的必修課。2016年底,在香港中文大學的最後一堂課,一位學生提出了一個問題(她以英文提問,我翻譯如下):「上完這門課之後,我了解城市不永續是制度上、結構性的根本問題,那您可不可以教我們該如何去挑戰現有結構?」這個提問讓我非常欣慰,表示學生對永續課題已有深刻的理解;卻也讓我糾結,不知該如何回答。
「每個人在自己的崗位上盡好本分就好了」,這是過去面對關於大環境的問題時,我這一代的人被告知的「標準答案」,但是永續課題的答案卻恰如其反。「在自己的崗位上盡本分就好」只是「不要想太多、管太多」的包著糖衣的說法,只會強固現有不永續的結構。要促成結構性的改變不可能容易,得要有許多人積極跳脫那個狹隘定義「本分」的現有結構,得要有許人不顧一切、不計較名利得失、不畏異樣眼光,去做那些非主流的倡議甚至革命工作。我該鼓勵學生:「你必須要叛逆、必須起身革命」嗎?我該鼓勵他們走一條困難的路嗎?這是作為一個老師的糾結。
那麼,我自己怎麼挑戰現有結構呢?教育與研究,是我的主要工具,試圖間接促成改變,特別是透過在大學教書,我可以試圖影響很快就會成為社會中堅份子的大學生。即便不忍鼓動他們在經濟仍不穩定的時期叛逆,但我希望在他們心中種下革命的種子,盼他們未來衣食無缺時,這顆種子就會發芽茁壯。
相信改變,一起做夢
這幾年來,陸續有年輕學子告訴我,正因為讀了《好城市》,所以想要投身永續城市的相關領域。《好城市》是我在社會大眾中撒的種子,因為相信改變。
相信改變,不是因為過於天真浪漫,而是基於事實的理性預測。我相信,有緣分閱讀到《好城市》的讀者,不管是初版的舊雨或是再版的新知,心中多多少少都渴望看到社會的正向改變,因此,我邀請你們跟我一起做夢——做大夢。只要大家一起,我們就不怕倡議看來激進的理念,不怕冷水不斷澆頭,然後總有一天,某個催化劑會在我們意想不到的時候出現,改變的烈火就會猛然燒起。(本文摘自《好城市:綠設計,慢哲學,啟動未來城市整建計畫》)
《好城市:綠設計,慢哲學,啟動未來城市整建計畫》作者:廖桂賢出版社:野人文化出版日期:2017/1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