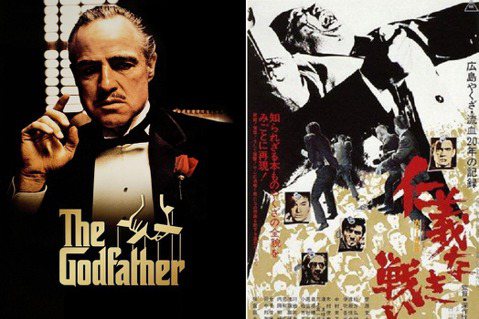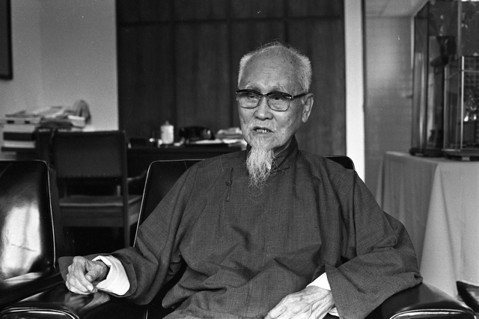《我這樣過了一生》,1980年代的外省族群記事——悼張毅導演

淡出影壇多年的導演張毅離世,他1980年代的相關作品也再一次為影迷所追念。
1982年,張毅與楊德昌、陶德辰、柯一正每人各拍一段落的《光陰的故事》,被視為「台灣新電影」的起點。台灣新電影也可以理解為「新台灣電影」,是新的台灣想像與表現美學。1970年代伴隨台灣的正當性危機,中影開始一連串的軍事宣傳電影,諸如《英烈千秋》(1976)、《梅花》(1976)等,但這類電影在1970、1980年代之交影響力式微。
戰後出生的年輕導演們開始從他們的視角反思台灣,其間有他們這一代的成長歷程、台灣的城鄉差異等。此外,也有從年輕一代的視角,反思上一代顛沛流離來到台灣的生命歷程,乃至身分認同的作品。台灣新電影力圖再現真實的社會軌跡,「寫實」也因此是台灣新電影的特色。從這個脈絡下來看,張毅的《我這樣過了一生》(1985)值得成為重新審視1980年代台灣社會景況的作品之一。
1980年代初期開始,外省族群(尤其是老兵)的處境成為電影題材;與之相較,《我這樣過了一生》以從中國來台灣的外省女性為主體,帶出來台灣勉力生存而後落地生根的生命經驗。除此之外,電影裡也以女主角一手打造的餐廳「霞飛之家」帶出台灣社會的轉型。這部作品獲得金馬獎最佳影片、最佳導演、最佳女主角與最佳改編劇本獎四大獎項,足見其在當時所獲得的肯定。


老兵故事的浮現
以外省族群為題材的電影早在1960年代就已出現,例如1963年李行執導的《街頭巷尾》。這部電影以外省底層為主角,強調環境雖然困難,但只要有志氣就能夠度過難關。電影最後還強調有一天要「回到大陸的家」。然而,20多年過去了,回家之夢早已因現實轉變為不可能之夢。當年跟著國民政府來台的軍人們,為數不少早已因年紀關係退役,而他們的處境如何?
1982年,外省退役老兵李師科戴著鴨舌帽,手上拿著手槍搶劫台北土地銀行古亭分行,一時之間震驚當時社會。1927年出生的李師科,22歲時跟著國民黨軍隊來台,32歲時因病退役,以開計程車維生。與其說他對社會懷有恨意,不如說是長期的思鄉以及生活不如意的累積。作家李敖當時也發表了〈為老兵李師科喊話〉的文章,其中提到李師科是被國家拋棄的老兵,而這個社會還有「千千萬萬的李師科在活著」。
李師科事件之後,1983年同時出現兩部以外省族群為題材的故事:台灣新電影系譜的作品《小畢的故事》,以及香港新藝城出品的《搭錯車》。陳坤厚執導的《小畢的故事》根據作家朱天文的同名小說改編。主角雖是小畢,但電影也帶出了父親「大畢」的背景——隨著國民政府來台,在中國曾有婚姻,但一身飄零在台灣,後來娶了曾是酒家女還未婚懷下小畢的妻子。大畢、小畢沒有血緣關係,卻因時代與社會因素陰錯陽差成為父子共同生活。
《搭錯車》雖是香港新藝城出品,不過幾乎全數是台灣班底拍攝。導演虞戡平以台北大安森林前身的違章建築為背景,孫越所飾演的外省老兵,正是住在那裡以撿破爛維生的社會底層,好心的他還收養棄嬰一路扶養,這個棄嬰日後成為知名歌星。電影裡,孫越是啞吧,象徵老兵在這個社會是無法出聲的。1984年李祐寧導演的《老莫的第二個春天》同樣是孫越主演老兵,是一部講述主角在中國曾有婚姻,因時代變化迎娶原住民的故事。
老兵故事的變化
1980年代是兩岸之間微妙的時空點。1980年代台灣老兵問題開始浮現之際,1978年年底中國確立改革開放路線,塵封30年的國門漸漸打開。而後,兩岸因國共戰爭分離的親人們輾轉開始聯繫,有的則是以香港為中介相互聯繫甚至見面。
原來的外省人故事開始有了一些新的變化,1985年王童執導的《陽春老爸》內容如名稱所示,父親一個人跟隨國民政府來台,而後與台灣女性成婚,名副其實的陽春老爸。電影聚焦兩代衝突,在台灣成家生小孩之後,小孩也慢慢成長,青春期間父子在眾多價值觀上有所衝突。直到某日父親輾轉得知人在中國的母親過世,嚎啕大哭,兒子見狀才知自己多麼不了解父親的過去。
虞戡平1988年的《海峽兩岸》是老兵故事的延伸,主題是在中國曾有婚姻的外省老兵,因時代因素在台也娶妻生子,隨著開放許多人以香港為中介見面,外省老兵再度由孫越演出,幾經聯繫安排,全家赴港與從中國而來的妻女見面。電影裡江霞所飾的台灣妻子,鮮活地演出了老公可能要回中國、不再回來的不確定感。
王童1989年的《香蕉天堂》門閂與李得勝兩人假冒左富貴與柳金元之名加入軍隊,而後隨著軍隊來到台灣。未料,兩人命運一路波折,柳金元被疑是共諜,面臨無情的審訊;門閂再改名生存,他以李麒麟之名考上公職生活漸趨穩定。多年之後,人們開始找尋失散多年的親友下落,門閂也接到李麒麟父親死訊的電話,時代下的流離,雖非真正的父親,門閂也放聲大哭。這一幕,應是1980年代外省族群流離題材當中讓人最深刻的。
勞苦女性一手打造的「霞飛之家」
張毅執導的《我這樣過了一生》根據蕭颯的小說《霞飛之家》改編,男女主角則是李立群與楊惠姍。值得一提的是,不少人或許聚焦導演、原著作家與女演員之間的感情關係,事實上,原著改編特別是1976年《聯合報》成立聯合報小說獎以來,得獎作品翻拍為電影者,在1980年代不在少數。
除了1980年蕭颯的《霞飛之家》,1983年李昂的《殺夫》1985年由曾壯祥導演改編為同名電影,1984年黃凡的《慈悲的滋味》1985年由蔡揚名導演改編為同名電影,1987年吳錦發的《春秋茶室》與王湘琦的《沒卵頭家》,也分別在1988年、1989年由徐進良導演、陳坤厚導演翻拍為同名電影。
《我這樣過了一生》以外省女性在台灣的生命經歷為故事,從中國來台的桂美,在家鄉曾有未婚夫,然而,時勢變動下隻身來台兩人分隔兩岸。在友人介紹下,桂美嫁給已育有三子的侯永年,未料,在飯店工作的侯永年嗜賭,生活無法安定,再加上又生了兩個小孩,生活無以為繼。桂美帶著兩個小孩赴日幫傭賺錢支撐家用,幾年之後,終於得以在台北仁愛路巷子裡開起「霞飛之家」餐廳。
霞飛之家的命名,因為桂美在中國鄉下長大,聽說有親戚住在上海霞飛路,繁華上海的印象就集中在「霞飛」兩字。店裡的招牌菜是牛肉燴飯、什錦炒飯、咖哩雞等。電影版與小說版的差異之一,在於小說裡桂美是赴美國幫傭,這段歷程也讓她學會巧克力派與蘋果派的作法,成為小店的招牌。無論是電影裡的到日本或是小說裡的到美國,都是到一個比台灣更先進的國度以勞力賺錢,這其實也是1960、1970年代台灣勞力密集、出口加工的經濟型態的縮影。
然而,安定的生活卻也是下一個波折的開始。桂美和丈夫侯永年是一組對照,丈夫嗜賭、愛面子,十足大男人主義,他是家裡的不定時炸彈,家庭安定之後嗜賭稍微收斂但卻又發生外遇;桂美則是傳統堅韌的女性,總是為家中大小事付諸心力。小說是1981年出版的,四年之後上映的電影,則因兩岸探親的社會話題加入了另一組命運的對照,當年留在中國的未婚夫也另有婚姻並育有兒女,雙方透過書信往來得知彼此近況。
電影的最終,是一生波折的桂美罹癌,霞飛之家何去何從。眾多兒女各有意見,原本要出國深造的正芳在無人願意接手下勇敢跳出。這一段電影詮釋得很精彩,這是正芳對母親的一生細緻觀察後的決定,不只是母女之情,還有一種同為女性的相互理解。


食物的隱喻
《我這樣過了一生》以外省女性為主體的敘事,放在電影與社會的脈絡下來看,迄今依舊在經典之林中有一席之地。即便我們在王童的《香蕉天堂》(1989)或是楊德昌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1991)裡看到不少外省女性的身影,但我們仍無法在影像裡看到她們的生命歷程。
此外,如果說《我這樣過了一生》再現了一個外省女性與家庭的故事,1984年萬仁執導的《油麻菜籽》正好足以為對照,這是本省夫婦的家庭故事。電影片名「油麻菜籽」取自台語俗諺「查某命油麻菜籽命」,也就是女性的生命歷程就隨婚姻飄到哪就長在哪。事實上,這也與《我這樣過了一生》裡桂美的流亡離散歷程相互呼應。
提及萬仁導演的作品,1983年的《蘋果的滋味》也有可與《我這樣過了一生》對照之處:同樣以食物為象徵,帶出不同面向的現代化表述。《蘋果的滋味》當中,蘋果就是美國的象徵,電影透過台灣底層百姓與駐台美軍官的一場車禍,帶出台灣人對美國「天堂」的想像,這自然是以反諷的手法,來反思戰後台灣「美國至上」的現代化歷程。《我這樣過了一生》則以霞飛之家原來的燴飯等中式餐飲轉型為西餐,象徵台北都會的轉型。整體來說,霞飛之家從中餐到西餐、從吃飽到講求品味,象徵了台灣社會的轉變。
《我這樣過了一生》講述了大時代下的流離故事,霞飛之家的味道平淡而堅實。導演離世,但作品永遠留下,讓我們得以重新回顧1980年代的時代刻痕。尤其社會是語言的居所,社會轉變了,有些語言也就跟著消逝,「外省人」的分類也慢慢消逝當中。《我這樣過了一生》除了是經典電影之一,也是台灣社會史的一道印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