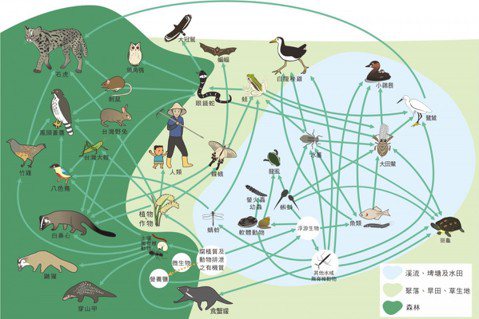黃重豪/「助魚好孕」:建設魚道、人工護送,北歐鮭魚復育之路

要人類與其他物種好好相處從來不是易事,以台灣來說,漁船在遠洋各處濫捕,經政府耗費4年整頓,好不容易在2019年才摘除歐盟給的黃牌警告;另外在河川生態上,堰壩林立形成十八銅人陣,政府雖闢建不少「魚道」方便通行,卻不諳各種魚類習性而多以失敗收場。
同樣靠水吃水的北歐何嘗不是如此?鮭魚是當地飲食文化基因,外國人若跟團到瑞典、芬蘭旅遊,大多都經歷過吃燻鮭魚、鮭魚湯喝到怕的經驗。而河流除了是鮭魚的家,更是發電來源,如芬蘭有330座水力電廠,佔總發電量達23%。於是在當地人嗜吃鮭魚、水力電廠開發的雙重夾擊下,波羅的海流域野生鮭魚的蹤跡已從100多條河川遽減到30條。
為了挽救這個頹勢,過去北歐人什麼都做了,闢建魚道,甚至拆掉舊水壩,卻都還是左支右絀。末了,最聰明的北歐人終於想出最笨拙的方法——用卡車載鮭魚越過水壩!
土法煉鋼,到底行不行得通呢?
河海「鮭」寶展現在地文化風采
之所以需要「保鑣」護送,是因為鮭魚是一種戀家的動物,一定要回到出生地(亦即河川上游)待產,才能安心的誕下下一代。
因而,牠們一生都忙著遷徙。出生在冰天雪地的河流發源地,長大成魚便開拔挺進下游,越過八千里路雲和月後,終於來到波瀾壯闊的大海。等到孕期一到,又得奮力上溯返回生命的原點,完成一生任務。
這種在河川、海洋之間折返跑的洄游魚類有好幾種,如鮭魚(salmon)、鱒魚(sea trout)、歐洲鰻鱺(eel)等,後兩者則是出生在海洋,洄游方向與鮭魚相反。
另還有「陸封型」洄游魚類,也就是其祖宗十八代在冰河期結束前來不及回到大海,就世世代代被困在內陸,像台灣的櫻花鉤吻鮭即屬之。雖然回不去海裡了,牠們也閒不下來,多在河川、湖泊間來回奔走。
不過跟櫻花鉤吻鮭不同的是,大西洋鮭魚體型較大、具高經濟價值,而且數個世紀以前就跟當地的文化緊緊綁在一起,比方北歐尋常人家大多有去河裡釣鮭魚的經驗。只是好景不常,這種庶民娛樂越來越奢侈,因為河裡漸不易尋得鮭魚芳蹤。
為了拯救產業及文化,歐盟已在波羅的海執行各種管制措施,如總量管制捕撈、分配捕撈額度、限制漁具種類等,固然有所成效,但大多數河川還是未恢復往日榮景。於是北歐人再為每一座水壩開闢魚道,只不過一系列五百障礙,仍給不了牠們一條安全回家的路。

設計不良,魚道仍是一條黃泉路
這條路到底有多遠呢?來看看瑞典的例子。
克拉爾河(Klarälven)起源於瑞典北方,流經挪威又回到瑞典,一路向南奔入維那恩湖(Vänern)。湖面積5,650平方公里,約為宜蘭、基隆、雙北、桃園加起來這麼大,是歐盟國家中最大的湖泊,9千年前冰河期結束便與大海永遠分離,形成溫和的棲地,也孕育了陸封型的大西洋鮭魚、棕鱒魚。
1600年代,是野生鮭、鱒魚捕獲量的歷史高峰,每年達5萬隻。到了1800年代初期降至3萬隻,此後小型水力發電站接連設立,用以供應伐木、金屬業用電,還將砍下的木材丟到河裡漂流運輸。至1800年代末,漁獲遽減到5千隻。
時間走到1900年代初,克拉爾河的大型水力發電站一座一座樹起,直到1964年第11座大壩落成,鮭魚的族群數量來到歷史新低,每年僅140隻。悲劇除了來自產業汙染、船舶干擾外,對鮭魚來說,長達280公里的返鄉路是備極艱辛的。
從維那恩湖出發,上溯25公里即會遇上1號發電站,這還只算熱身而已,接下來的挑戰是100公里內連續7座發電站,得一一攻克它,才能迎接150公里的康莊大道。最後,橫亙眼前的是9號發電站,耗盡剩餘力氣打敗這尊大魔王,家就真的不遠了——儘管正牌老家是在400公里之上的挪威,但已經永遠回不去了。
人類不忍其傷筋動骨,早從1907年起即設置秘密通道,幫助鮭魚暗度陳倉。但若魚道經常出現魚群,可一點都不是好事,這代表著塞車,也意味道路設計不良,有如「蜀道難,難於上青天」。這時魚兒可是焦急萬分的,等於完全暴露在掠食者的威脅中。
總算排隊通過了,千萬別以為魚兒能在水壩攔出的一片好風光裡喘息歇腳,此刻牠們已經奄奄一息,甚或迷失方向。而廣闊平靜的水面下其實天敵四伏,每多駐足一分鐘,就多一分被獵殺的機會。
實際上,魚道仍可能是一條黃泉路。

宅配免運費,笨方法反具經濟效益
至於那些平安返抵家鄉,卻被路程延誤懷孕黃金時機的,則是另一種遺憾。對此,瑞典又想出一帖妙方:1970年代起嘗試人工養殖鮭魚,等到母魚生產後,把魚苗載至1號發電站的下游放流,讓牠們在河、湖裡自由成長。
等到新生代2至3歲了,開始動身上溯,人類早已在離湖25公里遠的1號水壩前佈下天羅地網,等到魚群大軍一到,就一網打盡,整批送往養殖場孵育,生出的下一代再一次放流,如此反覆循環。
但是問題又來了,這些從人為襁褓復育出來的鮭魚適應力明顯較低,甚至無法與天敵、野生同類競爭生存。北歐人至此終於體認,老天爺的問題還是要老天爺來解決,生命的週期依然要生命自己來完成,不能任由自視上帝的人類橫加干涉。
不過北歐人也並非全無概念。時光回溯至1930年代,瑞典早已試行「誘捕與載運」(Trap and Transportation),也就是在河川下游的第一座水壩前設下陷阱,待鮭、鱒入彀後,打包丟上卡車,載往上游放生,「助魚好孕」。到1970年代人工復育啟動後,則將「綁架」來的魚群,一半送往養殖場,一半送回產卵地,人為與自然雙管齊下。
這看似傻呼呼的「宅配到府」一試80年,鮭、鱒數量到了2007年已經回升到2,300隻。而且野生族群的比例,從1997年的5%,增加到2008年的30%至50%。
北歐人護送鮭魚的方式,就像龍門鏢局一趟一趟押鏢金銀財寶一樣小心翼翼,難道不會所費不貲嗎?芬蘭就以伊河(Iijoki)研究發現,當河川只有一座水壩時,單純採用魚道是便宜有效的方式;一旦有兩座以上,魚道的興建及維護成本將超過保育效益,此時,直接用卡車運輸更具有經濟優勢。

圓滿生命週期只差一個角
芬蘭的研究同時指出,各地的主客觀條件不同,無法一概而論,因而每一條河都需要監測及調查更多基礎數據,才能作為分析基礎。此番結論也映照出,瑞典千算萬算,卻忽略一件事:鮭魚上得去、下不來。
鮭魚媽媽11月產完卵即會開始下遷,最遲隔年3月會全面撤退,孩子們長至2到3歲亦追隨母親腳步啟程下撤,此刻卻是河水量最少的季節,還須硬著頭皮穿過電廠渦輪,接受血滴子的考驗;或順著溢洪道落體,如同挑戰大怒神。
保守估計,克拉爾河的鮭魚下遷通過1座水壩的折損率約6%,通過8座就飆升到76%。另外如埃姆河(Emån),僅僅15%的鮭魚成功游向海裡。目前,瑞典只有少數河川如斯內克河(Snake)、哥倫比亞河(Columbia),同時具備協助上溯及下遷的機制,但效益仍未完整衡量。
北歐人挖空心思幫洄游魚類連結圓滿的生命週期,但這圓現在還缺了一角,且尚未找到有效方法。不管怎樣,站在動物角度設想,以生命週期為方針發想行動方案,大膽嘗試、勇於實踐,正是北歐人展現出來的智慧與靈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