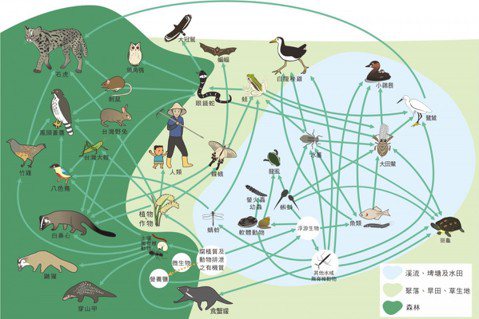侯延卿/【植物園方舟計畫】烏來杜鵑:植物牽起的跨海情誼

「生物多樣性」是全人類必須共同面對的課題,植物提供我們呼吸的空氣、食物、衣料、藥材、建材等,甚至具有維持環境安全與氣候穩定的功能,卻仍有許多人沒有意識到,生物多樣性是我們保命的基礎。
本系列專題將介紹被列入「國家植物園方舟計畫」的保育物種,帶領讀者認識這些「曾經與你我共存在同一片土地上」的珍稀植物,希冀透過情感上的關注,召喚全民支持與加入拯救瀕危物種的行列。
清溪倒照映山紅
台灣有15、16種原生杜鵑,其中11種是台灣特有種。杜鵑不僅是台北市的市花,也是舊台北縣的縣花,在大台北地區幾乎隨處可見,有如尋常百姓。但是,不知有多少人分得出不同品種的杜鵑花呢?
烏來杜鵑,算不上是明星植物,比起其他杜鵑也沒有特別亮眼,怎麼看都沒有那種會讓人為之瘋狂的特質,在生物學或分類學上也沒有崇高的地位,究竟有多少人會在乎它的存在?
筆者也是前往林試所拜訪博士後研究員蔡思薇後,才知道烏來杜鵑蘊藏了一段關於兩個男人的情誼——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那一年,植物學家威理森(Ernest Henry Wilson,1876-1930)來到台灣,遇見了金平亮三,兩人在彼此的人生中留下深刻記憶。當我了解這段近代烏來杜鵑的歷史後,這個植物在我眼中有了完全不同的光彩。

來自英國的威理森
威理森誕生於英國奇平坎普頓(Chipden Campden),他從小就熱愛植物,16歲開始在一家苗圃當學徒,學得一點經驗之後,白天在伯明翰植物園打工,晚上到伯明翰技術學校上課,並在求學時期獲得了女王植物學獎。21歲時,他進入邱園(Kew,英國皇家植物園)工作,並以一份有關松柏植物的論文而獲得了胡克獎(Hooker Prize,Hooker是英國皇家植物園首任園長)。
他原本考慮當植物學老師,但因緣際會被邱園推薦給國際苗圃商維奇公司(Veitch Nurseries,19世紀歐洲最大的家族經營苗圃),為他們去中國採集珙桐(又稱鴿子樹、手帕樹)。
1899年,威理森展開中國西部的壯遊,為維奇公司採集到數百種珍奇植物。他因此在植物界聲名大噪,1906年被美國哈佛大學的阿諾德植物園(Arnold Arboretum)挖角,派往中國、日本、韓國、澳洲、紐西蘭、印度、非洲等地尋找新物種,最高紀錄曾在四個月內為阿諾德植物園引進2,000個新物種。
他旅遊中國時,為方便與不識英語的中國人溝通,製作了類似名片功能的字條,上面寫的中文名字便是「威理森」。
1918年1月22日,威理森抵達臺灣。

來自日本的金平亮三
1895年,日本人在台灣展開殖民統治,於台灣總督府下置「殖產局林務課」,經營台灣林業。到了1910年代後期,日本對台灣植物已有比較充分的研究。
蔡思薇解釋,那個時代是台灣的植物大量被發現、被記錄的時代。發現一種植物需要很大的知識量,植物的名字背後是一個知識累積、浩瀚的世界,例如植物的學名都是以拉丁文來命名,因此研究植物分類的人都要學拉丁文之外,還要放眼全世界去比對他們所發現的植物,因此必須先了解其他國家有哪些植物;發表新物種之前,必須知道有沒有其他人比你更早確認這個植物的名字,以上條件要在一個具備很多知識的環境裡才有辦法做到,例如要有許多書籍、圖錄,要有圖書館(以前沒有網路),還要有人能看懂這些資訊,而這些資源不是一朝一夕就會突然出現的。
如果「植物學者」必須是受過系統訓練、有相當教育程度,且具備某些資格的人才足以勝任,那麼亞洲國家恐怕要到19世紀中、後期才有符合條件的「植物學者」出現。當時的台灣便在日本統治之下,出現了一些認識台灣植物的日籍植物學者。
因為環境的影響,相同的植物在不同地區會產生差異(例如葉子大小),日本屬於溫帶,生態環境和台灣不同,所以這些從日本來的植物學者,必須經過一段時間的調適,才比較了解在台灣要如何進行生態調查。
金平亮三(Ryozo Kanehira,1882-1948)是當時來台的日本植物學者之一,他出生於日本岡山,1907年自東京農科大學林學科畢業,隨即赴歐美遊學,1909年來台灣任職於殖產局下的林業部門;1911年林業試驗場成立後,由他兼任主事,1913年成為專任主事,數年後升任林業試驗場場長;1921年升任臺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林業部首任部長;1928年赴九州帝國大學農學部擔任教授,並於二次大戰時期赴印尼擔任日本佔領下的茂物植物園(Bogor Botanical Gardens)臘葉及圖書館館長。
1918年威理森來到台灣時,負責接待他的金平亮三已是林業試驗場主管,但與威理森這樣一個訓練有素、經驗豐富的植物學家相較,日本的植物學者仍處於學習階段。金平亮三曾多次提到他從威理森那裡學來的技巧,例如在野外大量記錄植物的方法、採集植物的技巧、如何使用獵槍採集高聳入雲的植物,還有如何使用巧力採集完整的毬果。當時,日本和台灣的植物學技巧都還在起步中。
威理森造訪亞洲多次,不過他對台灣的了解不足,所以需要當地對植物學有認識並可以溝通的人來導覽——這個人就是金平亮三。起初兩人的互動是科學家之間的交流,但是當他們開始攀登台灣的高山,友誼就往生死之交那一端靠近了。

兩位植物學者的交會
威理森來台灣兩次,分別在1918年的1月和10月,每次都停留兩三個月。走訪台灣山林,即使有人幫忙扛行李,威理森仍然必須自己跋山涉水、攀登危崖、鑽箭竹叢、忍受蚊蟲叮咬、淋大雨挨冰雹、躲避原住民的獵人頭行動……,台灣的山區地形險峻,是體力、耐力與修養的試煉。
他走遍大屯山、新高山(玉山)、雪山、合歡山、阿里山、打狗(高雄)、壽山、阿猴(屏東市)、卑南、花蓮、太魯閣、蘇澳、奇萊山、太平山、宜蘭、烏來等地,由北到南、由西到東,金平亮三陪伴威理森行遍台灣,幫他打點入山許可、組織武裝警察護衛、雇用熟悉山路的揹夫……,即使已經獲得官方全面協助,第二次來台的探查行程對威理森而言,仍有許多感到挫敗的時刻,他曾沮喪地說:「沒有比這更糟糕的冒險了。」
1918年10月底,威理森與金平亮三一起爬玉山。達成攻頂玉山的目標之後,威理森感嘆:「前往莫里遜山(玉山)的路根本沒有路。」「臺灣的山勢陡峭到我無法想像……」
然而,無論旅程多麼艱辛困頓,威理森仍時時對金平亮三讚不絕口:「金平英文很好,是個充滿活力、熱心且善意的人。」當時金平亮三的下屬佐佐木舜一與島田彌市,也輪流陪同威理森爬山採集植物,但佐佐木舜一與島田彌市在威理森心目中只是「能幹的採集者」,威理森念念不忘的人只有金平亮三。他寫給阿諾德植物園的書信和報告中,屢次提及金平亮三,甚至建議阿諾德植物園與金平亮三保持聯繫。

發現烏來杜鵑
威理森在1921年發表烏來杜鵑的文獻中記載,1918年4月1日他在烏來地區一間派出所的庭院中首次見到烏來杜鵑,他認為可能是一個新種,於是帶回阿諾德植物園研究。
當時的觀賞花卉沒有現在這麼多種,所以很多人會把附近山邊或溪邊漂亮的花木採回自家庭園種植,烏來那間派出所的烏來杜鵑就是從附近採集而來的。當時的烏來包括北勢溪及周邊山區,烏來杜鵑生長在北勢溪的溪邊岩石上,是岩生型的杜鵑,分佈極為侷限。雖然不知道烏來杜鵑在烏來生長了多少年,也不知道多少植物學者與杜鵑愛好者曾經在它身旁逗留,但當時都沒有人發現它是一個新種。
威理森發表烏來杜鵑時,用金平亮三的姓氏「Kanehira」當種小名,所以烏來杜鵑的學名Rhododendron kanehirai如果譯成中文應是「金平杜鵑」。威理森以金平亮三這個陪他遊覽台灣深山、曾經患難相扶的人來為烏來杜鵑命名,具有特別的紀念意義。蔡思薇說,發表的植物學家有種小名的命名裁量權,但大部分都不會用自己的名字(因為自己的名字會出現在發表者的論文中),一般會用植物的特徵,例如紅花白花、葉子大小或長梗短梗。
當然也有很多發表者以人名來為植物命名,所以台灣很多植物的種小名都是人名(多半是與植物有關的人名),其中以金平亮三命名的植物有數十種,有些是他採集的,也有許多是別人發現但以他為名。

再會老友、重訪烏來杜鵑
1926年3月,時任總督府林業部部長的金平亮三,啟程至歐洲、南北美洲,直至1927年6月返臺。這種長途旅行,搭船一趟要耗時三個月,當然要順道探訪老朋友,於是金平亮三從紐約一上岸便奔赴麻薩諸塞州,拜訪將近十年不見的威理森。
1928年,金平亮三即將離開台灣返回日本,他寄了一張自己與烏來杜鵑在天然棲地合影的照片給威理森。蔡思薇推測,因為1918年威理森來台灣時看到的烏來杜鵑是種在派出所的院子裡,金平亮三想讓威理森看看野生烏來杜鵑生長的環境,於是在烏來杜鵑開花時前往北勢溪,坐在溪邊的烏來杜鵑花叢中,拍下一張若有所思的照片。
這張照片不是隨手拍的,而是經過計畫,算準花開時間,帶著攝影師前往拍攝。這張照片現在保存於美國哈佛大學阿諾德植物園圖書館,然而隨照片一起寄給威理森的信件卻不知流落何方,也不知是否仍被留存?蔡思薇檢視所有能找到的文獻,甚至飛往美國阿諾德植物園查閱威理森的書信與相關記錄,雖知道兩人有通信,可惜找不到往返的信件。
1930年,威理森因車禍逝世,得年54歲。金平在遙遠的日本,為此撰寫追悼文,感傷威理森過世的太早。

一次滅絕,一個教訓
蔡思薇把烏來杜鵑的故事分為前後兩個階段。前半部是兩個植物學家相識的故事,後半部則是野外滅絕之後的復育。
由於烏來杜鵑是平地種杜鵑,要見到並不難,所以在它滅絕之前,人們從來沒有意識到它會消失。1984年,因翡翠水庫興建進行初期蓄水而淹沒整個烏來杜鵑的棲地,使這個物種被列為「原生地消失的野外滅絕」(EW),幸好山區有些人家裡也種了烏來杜鵑,經比對確定種類無誤,才得以復育。
烏來杜鵑的消失,其實是象徵台灣在7、80年代對於環境的不重視,蓋水庫之前沒想到要做比較深入的生態調查,而即使當時植物學家應該已經知道烏來杜鵑的生育地很侷限,但也沒有維護保存的聲浪。只能說這是時代的觀念,當時的台灣以經濟開發為主,等水庫完工,水淹上來,才發現有物種不見了。
烏來杜鵑的案例警惕我們,過去犯了一個錯誤,現在我們要從滅絕的命運中搶救生態環境,並將這個教訓謹記在心,希望以後不會再發生。並不是每種植物都可以滅絕了再栽培成功,有時候沒有就沒有了。

一趟旅程,一場機緣
研究植物歷史的蔡思薇認為,某個植物的發表時常與某一次的冒險有關,某個人走了某條路才因此遇見某個植物,或某個植物學者跟了某個探險隊才發現一個新物種,所以植物的學名常常蘊藏了一個故事、一趟旅程或一場機緣。
威理森當年採集的烏來杜鵑標本,仍留存在哈佛大學標本館內;台灣的烏來杜鵑則正在野外滅絕後的復育路上,等待完成另一個階段的故事。目前在台北植物園、翡翠水庫等地都有烏來杜鵑扦插復育的植株,新北市政府農業局則嘗試培育實生苗(直接從種子長出來的叫「實生苗」)。其中,台北植物園除了肩負方舟植物的保種任務外,也是過去金平亮三工作的地方,因此格外珍惜這個種名內含一段歷史的烏來杜鵑。
植物也有跌宕起伏的命運,但有時候,生命中就是會出現意想不到的貴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