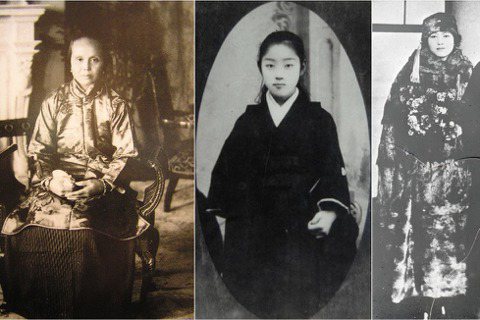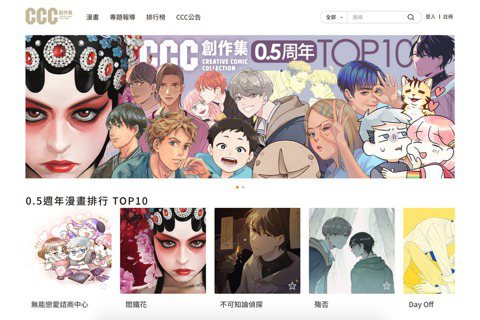奇蹟背後沒有光:被黨犧牲的數億農民工,與他們處身的《低端中國》

1949年的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本身就是近代史上的神奇事件。與傳統馬克斯主義理論相悖的是,中國共產黨的成功,並非依靠有組織有思想的都市產業工人,而是動員了廣大而分散的鄉村農民,最後成功擊敗國民黨這個「資產階級政權」。
早在1927年,毛澤東前往湖南貧困鄉間考察,他當時得出了一條結論:
誰贏得了農民,誰就贏得了中國。
這條戰略果然正確抓住「革命情勢」,第二次國共戰爭把國民黨打得一敗塗地。
不只是「革命建國」得益於農民,所謂「中國經濟奇蹟」背後,農村更是首要功臣。文革結束、極左派倒台,鄧小平在1978年宣佈改革開放,允許財產私有、外商進駐,廣東也「先行一步」成立特區,測驗資本經濟能否在中國施行。
當時百廢待舉的赤貧中國,唯一能夠吸引歐美資本的利基,就在於便宜到不可思議的「農村勞動力」——此後數十年,一貧如洗的內陸農民,大量湧入沿海都市及其週邊加工出口廠區,並創造了連續三十年10%的經濟成長率、還有數兆美元的外匯存底。
只不過,這幾年中國經濟出現疲軟趨勢,多年來的一胎化政策導致人口紅利用盡、對土地與自然的無節制開發也到了盡頭。四十年來打造「中國奇蹟」的最大功臣——出身鄉村的無數「農民工」——他們即將與這個巨大極權國度一同陷入某種「中國陷阱」。

剝削與鎮壓:農民工的「沿海中國」
在一個混合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怪異政體內,領導所欣欣樂道的總體「發展」,很可能來自於底層人民的慷慨「犧牲」。
美籍資深經濟記者羅谷(Dexter Roberts)的新書《低端中國:黨、土地、農民工,與中國即將到來的經濟危機》,就提供了一扇洞見全貌的窗口——從「農民工」這個廣大群體,來窺見官方絕口不提的「另一半中國」,還有資本主義中國模式的可能將來。
羅谷長年派駐中國,曾任《商業週刊》與《彭博商業週刊》社長。不過,他對紙醉金迷、捲入全球經濟的北京高端金融沒有工作以外的興趣,羅谷頻繁往返中國各地,長期追蹤訪調各地民工。
改革開放以來,大批的農村青年男女,遷移至珠江三角洲為首的沿海城市。他們在建築毫無章法、擁擠悶熱的加工製造區裡,以每小時不到20塊錢人民幣、一日上班14小時的代價,從事單調重複勞動,還要承受廠方各種剋扣條款。2010年,深圳富士康廠區陸續有14名員工不堪非人待遇跳樓自殺,那或許是農民工唯一可以自由表達的「最後抗議」。
若問誰該為此負責?全球知名大廠如諾基亞、蘋果、Coach、Calvin Klein都貪圖中國那無比便宜的勞動力。當然北京方面更加難辭其咎,在官方的默許或者有意助長下,巨型跨國企業盡可能壓低工資、福利與人權條件,讓數億工人的生活僅堪餬口,同時也擠壓出天文數字般的企業利潤與國家稅收。《低端中國》轉述了郭台銘某次失言,他認為安置鴻海旗下廣大員工有如「管理一百萬個動物,頭痛得要死」——郭董甚至懶得「把你們當人看」,員工不過牲畜。
在一個共產黨統治的國度,資本剝削卻沒有受到任何節制,這不能不說是歷史的諷刺。

「赤腳律師」到「三和大神」
除了寬鬆而且很少執行的勞動法規以外,「國家」還高高舉起「看得見的手」,去恫嚇那些不肯乖乖服從命運的工人。進入二十一世紀後,農民工開始爭取稍稍有點尊嚴的勞動條件,還有為了他們奔走的「赤腳律師」(指接受過中等教育、懂得基本法律知識、為農民服務的基層法律工作者)因應而生(本書引用民間統計,指出每年都有破千起勞工抗議)。
不過中國深知提升勞動條件也意味著減損發展優勢,為了穩定投資環境、也為了讓外資企業「安心」,中國政府嚴厲地打擊方興未艾的大小勞工運動。曖昧的「擾亂公共秩序」是最常見的罪名,還有一些法律外的「喝茶」、「度假」待遇(公安突然把異議者帶走軟禁數日),或者以虛構的嫖妓罪名抓捕抗議分子,對特別勇敢的領頭羊進行人格謀殺(香港民主運動中也用過這招)。
與進入中國做深度報導的所有同行一樣,《低端中國》多次描寫了外國記者的典型恐懼——每當羅谷依照受訪者指示,走入那些隱密的蜿蜒長巷,準備前往會面地點的時候,最讓這位「美國人」感到害怕的,就是身邊那些面無表情的路人突然表明自己的便衣身分。這種壓力更讓無數中國老百姓,看見帶著紙筆相機的外國人就退避三舍。
中國這種強勢維穩的作法,在某種層面上可以說「成效卓著」。如果你也是農民工階層,在這樣的處境下可有未來?雖然無數人被這種擔憂深深困擾,不過,現實讓他們慢慢學會收起憤怒,學會在嚴苛勞動條件與毫無希望的未來之下就地「躺平」。
近年來在中國廣受各方關注的「三和大神」現象(工作一日、遊玩三日的年輕民工),就表明了這一當代趨勢。對於那些持續進入沿海地區的年輕農民工來說,日薪不到100元人民幣的勞動條件,逼迫他們放棄掙扎,不再儲蓄、不再尋找穩定工作,手上有錢就流連於網咖,手上無錢就露宿街頭,然後明天再去人力仲介那裡等待一份單日結算的臨時工作。

蕭條與老化:農民工的「內陸中國」
對於離鄉背井多年的農民工來說,除了在沿海大城的艱困勞動,他們仍深情牽記著遙遠的親愛家鄉。儘管,整年只有春節假期夠長,讓遊子可以回家一次(中國幅員極廣,想想看貴州到天津的距離)。
當羅谷走訪內陸城鎮,他注意到,那些在「建設西部」口號下搭建的富麗旅遊中心、商業中心,許多都塵封廢棄,無人使用——誰會使用呢?畢竟農村地方只留下農民工的老年父母、幼年子女。
這便是所謂「空巢村」現象。在國際媒體前頻頻自誇「精準脫貧」的中國,目前有全國五分之一、為數6,000萬的出外農民工子女,是所謂「留守兒童」,在鄉村中由祖父母撫養長大。孩子們思念父母、少有人管教,最直接的後果有二:一是缺乏親情與照顧,造成了嚴重的兒少心理健康危機;二是出於同樣理由,鄉村兒童有著嚴重學習障礙。
在學歷與階級流動高度正相關的中國,全國統一的「高考」制度,更加劇了升學機會上的不平等,城市與鄉村的高中畢業率的差距,已經達到七倍以上。這意味著,留守兒童長大後很可能走上父母親成為廉價勞動力的老路,或者更慘,因為中國產業結構正在轉變,未來不再需要如此大量的低技術勞工。
與此相應的是,佔全國五分之三,超過8,000萬的老年人,也都居住在內陸的蕭條農村。多數鄉村老人的經濟狀況在貧窮線以下,還有極高的憂鬱症與自殺比率,同時因為世代差距,他們並不真正知道應該如何跟兒女們留下的孫輩相處,這對老幼雙方都是一種折磨。習近平上臺後,以政治改革為名加強中央集權,北京從省政府拿走更多稅收,地方因此無力改善老人與兒童緊迫需要的教育與醫療,使得城鄉差距雪上加霜。
這些被遺棄在農村的老人小孩,還有快速惡化的城鄉差距,都與中國「戶口制度」密切相關。學界普遍認為,戶口制度帶來雙重剝削:惡劣的異鄉勞動是第一層,在異鄉無法享有正常公共福祉則是第二層。
由於中國人民沒有完整的遷徙自由,雖然允許農民工前往遠方大城市工作,但他們的醫療、教育和社福等基本需求,依舊綁定於故鄉戶籍,即使在大城市工作三十年,要轉移戶口仍有非常嚴苛、基本上是不可能達成的經濟門檻須要跨過。這最終造成了,廣大農民工在工作地點無法享有基本公民權利,就只能把家中長幼留在故鄉(沒有城市戶籍老人無法就醫、孩子無法上學)。

振興鄉村的兩種辦法
中國當局並非不知道上述問題的嚴重性,他們有兩個振興鄉村的「辦法」。其一是,加速內陸基礎建設、鼓勵外商投資、鼓勵農民工回鄉。在這個「西部大開發」政策下,不少「空巢村」變成從事網路物流的「淘寶村」、國內旅遊中心紛紛成立、也有一些重點產業因為官方優惠自願轉移內陸。不過羅谷實地去拜訪了幾位中年「返鄉農民工」,他們都對政府的宣傳持保留態度,比如那條允諾多年的高速公路,遲遲沒有動工跡象。
另一個方法可能更為直接粗暴。國家強制性低價徵收農村土地,再變更地目,賣給開發商蓋起住商大樓或工業園區。除了官商都能在此過程中獲利,還能夠「強迫鄉村城市化」。不過這種模式在近年造成激烈反彈,每年都有自焚抗議或是人命衝突。真相是,假如農民拒絕搬遷,還會有不知哪來的流氓上門,砸爛家具門窗,打斷抗拒者的胳膊雙腿。
農民工的暗淡前景
在這個數千年來民變頻頻發生的古老國度,出身農村的人,在歷史與在當代都是次等公民。《低端中國》細膩地展現了「農民工」這種複合身分的兩難。身為偏鄙內陸的「農民」,他們的戶口被限制、父母孩子被留在家鄉、土地被國家強迫徵收;而作為進入繁華城市的「工人」,他們必須忍耐惡劣勞動環境、領取微薄薪資、任何維權主張都被打壓。
本書更進一步指出,隨著產業自動化、機器化的趨勢,以及都市人口政策的緊縮,農民工最終會被逐出傳統的加工製造園區。也許沿海大都市還是會收容這些漂泊的人——比如方興未艾的電商經濟、外送平台還有三級服務業,目前都需求大量人力來滿足富裕的都會白領階級——不過,羅谷提醒我們,這些新型態工作機會,更缺乏足夠的法律規範,也因而同樣不安全、高工時、缺乏基本勞權與職災保障,很可能只是換了名目的血汗勞動。
《低端中國》從長期深入的基層訪調出發,也有建立在經濟學與社會學上的犀利視野,精通中文的作者甚至能夠回顧中國歷史裡,中央政府與地方農民的長久矛盾。而羅谷本人多年的中國居住經驗,更與民工家族或維權人士發展出誠懇友誼,這又幫助了他在帶領讀者看見結構問題的同時,筆下又充滿了人情與故事的溫度。
回到「國家」的盤算,農民工問題有兩個互相衝突的面向。曾經,他們是中國快速發展的無名功臣;但如今,他們已是中國經濟轉型的「沉重負擔」。官方在「國家利益」的大旗下會怎麼權衡——是要繼續軟硬兼施,對龐大農村人口進行沒有節制的勞動力榨取?或者是「不可避免地」剝削或遺棄他們的同時,稍稍推出保護政策,避免相應的社會動盪?

中國模式的「中國主義」
令人難過的是,農民工的困境其實遠遠不只繫於國家政策,還包括保守中間階層對他們的敵意與漠視——農民工的存在,很大程度「保障」了都市白領的經濟利益,因為便宜的服務業與製造業確實提升了城市生活品質,但排擠農民工的現行戶口制度,又讓這些「外鄉人」無法分享繁華都市內的各種公共資源。
也許,所有中國人都心知肚明,在中國共產黨主導的私有制經濟裡,無論我們稱呼那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或者「中國特色資本主義」,其真正的本質都是立足於寡頭統治的「國家主義」,或乾脆說,「中國式威權主義」。這恐怕才是中國經濟奇蹟背後最大的秘密——國家機器決定勞動型態、決定利潤分配、決定產業藍圖。換句話說,國家很清楚超額勞動的農民工正是經濟快速發展的必要代價。
在疫情與貿易戰夾攻下,當前中國政府面對越來越明顯的衰退,當然有自己的如意算盤——中國需要從世界「工廠」轉變為世界「市場」,如果農民工能夠提升為中產階級,那麼龐大內需就足以成為經濟增長的動能。但是《低端中國》指出,這個十四億人口的國家,除了六億以上國民依舊陷於勞動貧窮,平均人力素質也長久低落,短期內難以真正轉型。
對於「中國工人能否成為中國經濟的核心驅動者?」這個問題,本書顯然不抱樂觀。但是不管是社會的、經濟的所有當代中國問題,或許還是得回到這個國家最根本的政治體質:如果沒有徹底的民主改革,底層農民工在今日無比迫切的生存困境,將永遠也沒有機會,進入保守自私的公眾視野與專制僵硬的決策中樞,遑論任何實質改變了。